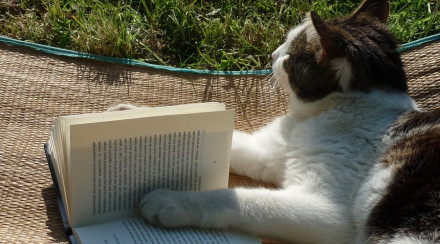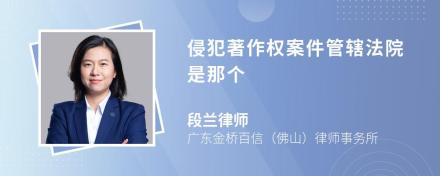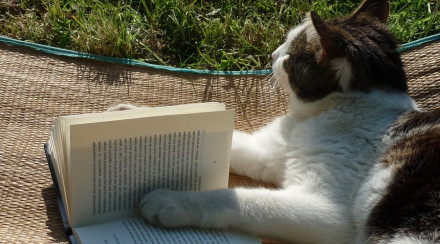正文:
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张承志。
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在线”是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互联)设立的在线网站。1998年4月,世纪互联成立“灵波小组”,为“北京在线”做栏目。尔后,世纪互联在未取得原告作家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张承志许可的情况下,下载了在网络上传播的六名原告分别创作的《坚硬的稀粥》、《漫长的路》、《白罂粟》、《预约死亡》、《一地鸡毛》、《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等文学作品,并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上网用户只要通过拨号上网方式进入世纪互联的网址:http://WWW.bol.com.cn主页,点击其页面中“小说一族”,进入
“书香远飘”页面,然后在该页面中点击“当代中国”页面,再点击具体作者的作品名称,用户即可浏览或下载该作者的作品。
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张承志6位作家得知以上事实后,分别向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位原告诉称:世纪互联作为提供互联网络服务的服务商,未经许可,以营利目的使用原告的作品,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承担诉讼费、调查费等合理费用。
世纪互联答辩称:互联网络服务是一种新兴行业,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在网络上传输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信息,具有便捷、低价等优势,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授权,是否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等问题无法可循。现公司已关闭“北京在线”的“小说一族”栏目,停止使用原告的作品。关于精神损失赔偿,法律没有规定,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审判】
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合并审理认为:著作权人对其创作的作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享有专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非依法律规定,未经著作权人的授权,公开使用他人的作品,即构成对作者著作权的侵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对作品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并不能否认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其中,数字化作品是将文字、数值、图像等表现形式的作品,通过计算机转换成机器识别的二进制编码数字的作品,这种转换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并没有形成新的作品,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在网络环境中数字化表现的作品依然享有著作权。被告从互联网上将原告的作品下载到其计算机系统内存储,并通过WWW服务器将原告的作品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的行为,是对原告作品的传播使用。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决定其作品是否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使用。被告未经许可将原告的作品在网上传播,侵害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第(五)项、第(八)项的规定,于1999年9月18日作出判决: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世纪互联停止使用6名原告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坚硬的稀粥》、《漫长的路》、《白罂粟》、《预约死亡》、《一地鸡毛》、《黑骏马》和《北方的河》。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世纪互联在其网站主页上分别向六名原告公开致歉,致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世纪互联向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张承志分别赔偿经济损失1680元、720元、1140元、5760元、4200元、13080元。
四、驳回六名原告要求世纪互联赔偿各自精神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世纪互联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法律问题,应当通过著作权法的修正或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和规范,使各方面有法可循。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一审法院就将文学作品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延伸、扩展到网上传输,认定对已有网络资源的利用,即转载已公开发表过的数字化文学作品,亦应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就是侵权,这是对法律的扩大化解释。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列举的是传统作品的使用方式,不包括在国际互联网上使用作品。同时,国际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使上诉人对网友传输来的信息难以控制。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被上诉人王蒙等六人答辩同意一审判决,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享有专有使用权。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明确网络上作品的使用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对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不进行规范。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也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使用者应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所列举的作品使用方式,是指传统作品的使用方式,不包括国际互联网使用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世纪互联作为网络内容提供服务商(ICP),对其在网站上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内容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应负有注意义务。本案涉及的被上诉人的作品是在
“小说一族”栏目中使用的,该栏目的内容是经上诉人委托“灵波小组”选择、整理而确定的。这些作品虽为他人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传递到世纪互联的网站上,但上诉人从技术上完全有能力控制是否将该作品上载到其互联网上。上诉人认为其对网上传递的信息难以控制,主观上无过错的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第四十五条第(五)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12月17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信息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民法院受理了一批涉及网络的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著作权纠纷案件。这类案件如何适用法律,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都规定得不具体,这给人民法院审判此类纠纷带来了困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遇到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数字化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在网络环境下,表现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编码形式的思想表达形式,即数字化作品能否适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这是本案的关键所在。从著作权保护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都会给著作权保护带来巨大的冲击,必然引起作品的表现形式、传播手段、使用方式的变化,使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得到扩张。但这些变化并不影响适用著作权法对作品进行保护。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根据这一定义,只要具备“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这两个实质要件,即可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而对于作品的存在形式及载体并无任何要求。实际上,作品的数字化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的文字、数值、图像、声音等表现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以运用数字信息的存储技术进行存储,并根据需要把这些被转换成数字编码形式的信息还原的一种技术。因此,作品的数字化过程,并不是创作作品的过程,将文字等表现形式的作品转换成机器识别的二进制编码的数字编码形式,并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并不产生新的作品。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的区别仅在于作品存在形式和载体的不同,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会因数字化而有丝毫改变,也不会因数字化而丧失“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因此,根据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数字化的网络信息,如具备作品实质要件,也应认定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能否确认将数字化作品进行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作品的网络传输行为,是指将作品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自选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作品的行为。网络传输不同于以往对作品的传统使用方式,而是一种新的作品使用方式。一般来讲,对于作品的每一种使用方式,著作权法中都会相应地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对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作了列举性规定,其中并不包括网络传输。这就使本案在适用法律时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能否将网络传输确认为一种新的作品使用方式,并进而确认著作权人享有网络传输权,这正是本案备受关注的原因。
1996年制定的《WIPO版权条约》第8条规定了公众传播权,即作者有权或有权授权他人将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我国已在该条约上签字,但尚未批准生效。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五条关于作品使用方式和侵权行为种类的规定中,虽未明确包括网络传输行为,但也并未绝对排除新出现的使用方式和侵权种类。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受理本案的一、二审法院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对作品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产生影响。作品在网络上进行传播,虽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播放等使用方式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公众了解作品的内容。使用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使用和传播的控制权利。因此,一、二审法院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第四十五条第(五)项判决被告侵权成立,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
从本案被告的答辩理由和上诉理由来看,其认为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授权和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属无法可循的问题;其作为信息网络经营者转载已公开发表过的数字化文学作品,是对已有网络资源的利用,似为是高新技术发展下其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作品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不应当延伸、扩展到网上传输领域。从此角度提出问题,似乎是在提醒人们注意,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无法适用现行著作权法处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更重于对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对此应当如何认识和回答呢?
首先,对著作权的保护,在绝大多数场合是对其中使用权即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使用权的保护。正是使用权的行使,作者创作的作品才得以进入社会,实现其社会价值和财产价值,并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同时,作品作为一种智力成果,其智力劳动价值与他人劳动价值、社会劳动价值的交换形式,就是作品的使用。而使用权的内涵,就是著作权人对使用的控制权。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以列举某些具体的使用方式的方法来表达了“使用权”的概念,即使用权是“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这里列举的一些使用方式,确实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常见的使用方式。但该规定在列举后加了一个“等”字,就非常明确地表明其列举是不穷尽的列举??包括对已有的和将来可能有的。这种立法技术表明,列举不加“等”字即为穷尽列举,穷尽列明的法律意义即是该法律规定仅在列明的事项范围内适用,不能超出列明的事项范围作扩大解释;列举后又加“等”字为不穷尽列举,其法律意义即是该法律规定对与列明的事项同类的未能列明的事项同样适用,这正是法律规范高度概括性和预见性的精巧所在。将这种不穷尽列举法律规范适用于同类事项,并不是对法律的扩大化解释,仅仅是对列举事项的进一步补充,是该法律规范本来就应当涵盖的事项。故此,对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项关于使用权概念的规定改变一种说法,应更能反映使用权的法律内涵,即著作权中的使用权,是著作权人以现在已有的和将来可能有的使用方式,自行使用作品或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因而,只要将本案涉及的网络上传输作品方式认定为是一种新型的使用作品的方式,本案的处理就非是“无法可循”的问题,而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循。
其次,网络上传输作品在性质上与出版商通过印刷的方式获得作品复制品后向社会发行,来满足公众的需求没有什么不同,即都可界定为是一种“发行”的使用方式。所不同的是,网络经营者或服务商取代了出版商,计算机信息输入、存储、传输、读取技术取代了印刷、发行,作品的数字编码存在形式和计算机信息还原形式取代了作品传统的某种有形载体直观表现的复制品形式。这些不同,只不过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作品表现形式和传播形式上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不同于传统使用方式的新的使用方式。根据著作权之使用权的涵义,上网使用作品的权利当然属著作权人的使用权控制的范围,得由其自行或许可他人以这种方式使用其作品,他人不经许可而将著作权人之作品上网使用,即构成侵犯著作权之使用权的行为。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网络传输技术使公众可以简单到通过“点击”而便捷、低廉地获得信息,并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因此,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的社会利用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它对信息权利人对信息专有权的控制和实现信息的交换价值带来无可估量的冲击。如作品上网使用可以不经其著作权人许可,则可能使著作权人的市场份额丧失殆尽,极大地损害其获得报酬的利益。如此,就更应当为著作权人提供有力的、有效的法律保护。
第三,被告所说的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应当解释出可以对抗著作权或应优于著作权获得保护。因为,网络经营者或者说服务商将他人作品上网向公众提供,首先面对的是作品著作权人是否许可的法律问题,网络经营者在此时仅是著作权法律关系的义务人,负有依法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其以该种使用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义务;如果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还负有依法向著作权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和不得侵犯著作权人其他著作权利的义务。网络经营者只要不履行其中任何一项义务,都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根本不可能用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来对抗。
当然,网络经营者在取得许可或依法可不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中,对自己赋于作品的传播形式应当享有权利。这种权利如同传统的出版商对其赋予作品的版式、装帧设计以及许可合同约定的排他专有出版权一样,可为其对抗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第三人的专有权。但对其这种权利的保护不能影响对作品著作权人著作权的保护,两种权利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法律问题。
第四,被告提出的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特别是转载已公开发表过的数字化文学作品,是否应经作品著作权人同意,及是否要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问题,一方面涉及立法政策考虑问题,即为鼓励和扶持新兴行业,国家是否要采取与已有法律规定不同的优惠政策,这应是立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任何人可随意解释的问题。在立法上未有新的规定之前,法院也无权突破已有法律规定另作解释。另一方面涉及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问题,即可否将网络经营者等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一样对待,对他人已发表过的作品上网传播,也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这实际上也是立法上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企业法人商业性使用作品,应当经著作权人许可,并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在著作权法上是难能改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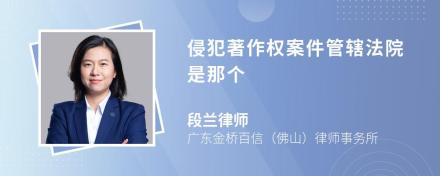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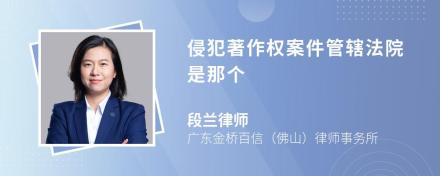


 01:07
人已看
01:07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