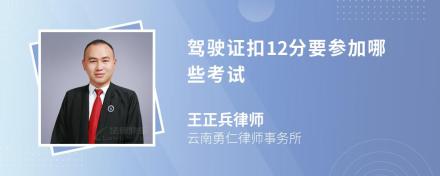[摘 要] 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也由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文化整合势在必行。法律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法学又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法学教育最有可能完成文化整合的使命。但我国已有的法律基础课程,由于设置的缺陷,并不能完成这一使命。通过对其改革而完成这一使命是必要的。
[关键词] 法学;教育;文化整合
近年来,关于法学教育的目的、方法等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在法学专业教育的范围内进行的。而笔者试从另一角度,即文化的角度,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的“两课”课程之一的《法律基础教程》的现状和应有功能展开论述,并探讨这一课程的目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整合的社会基础
在谈“文化整合”之前,对“文化”一词作一些研讨是必要的。
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ber)和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合著的《文化———有关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列举了西方学术界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定义160余种,其中尚不包括中国、苏联、东欧各国有关的种种“文化”定义。由此可见,“给文化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有争议的确切定义,这是多年来中外所有研究者的愿望。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1](P2)
在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词语。从广义上说,“文化”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古埃及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此处的“文化”不仅包括古埃及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也包括基于这些认识而产生的活动成果,如埃及金字塔、壁画等。在英文中,culture与“文化”相对应,指植物的栽培、树木的种植等,由此引申出教育、修养、人类能力的发展、礼貌、知识、情操、风尚等意义。这就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一词所具有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尽管“文化”一词的含义繁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强调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1](P3)给“文化”下一个定义确实很难,但我们可以描述它的外延,以揭示其内涵。“文化”包括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体的人与宇宙、社会的关系态度。“文化”也可指人类有意识的创造的物质成果。
那么,“文化整合”中的“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整合”即调整,统合,使之符合一定目的之意。显然,“物质成果”是已然的物化存在,不可能删改、调整,能删改、调整的只能是观念形态的文化,即指对个体的人与宇宙、社会的关系的态度及作为其基础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它的出发点是:人是什么?怎样的人才符合人的本性、“天道”?怎样的社会———人的复杂关系的群体———才是健康的?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文化整合”已成为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以致有人说,“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书生对它投入这么多的精力”。[2](P2)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的两个基础。
第一,尽管“文化整合”一词在最近一二十年才频频使用,但它概括的社会现象早在19世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时就已出现,当时国人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展成为更深层次的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同时,更为彻底的革命派的共和观念也在滋长,并在20世纪中,另一种性质的近代意义的国家形式又形成。算起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侵蚀”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这是一项庞大的文化运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并不曾理智地有效地进行文化的统计、清理、统合、移植。尽管很多精英分子在某些方面,如“统计”或“清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整个文化工程的统计、清理、统合、移植不是某些学究们独自能完成的。它不仅是一项理论工程,也是一项实践工程,而且是一项全社会的工程。所以,没有全社会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我们的社会不曾系统地做过这件事。[page]
不妨拿一件我们时常会碰到的事情来看。在法院,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上级要来人检查该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总动员。于是法院每天抽调部分干警,在院领导的带领下,跟其他相关人员一道上街清除污七八糟的广告,驱逐乞丐、小贩。除这些事情外,上级机关还常常布置如抽调法官去扶贫、支教、搞社教、抓计划生育、催公粮之类的任务。
中国的官僚、老百姓为什么会觉得如此职责不分的事情属正常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已习惯于“父母官”这一词对国家机关的概括。“父母官”意味着官员们像父母一样对不能自主的子女的“关怀”,“父母官”也意味着无微不至的“关心”。传统的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官儿。但在现代观念中,这却是极其荒谬的事情。首先,在现代观念中,平等意味着人格自主、独立,而不是像一个未成年人一样被父母“关怀”。其次,在现代社会中,官员们的职务行为不应是出于“爱”或“关心”,而应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另外,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意味着无所不至的干涉,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是不能容忍的。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行政长官就是一切,这确实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市委市府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挥自己辖区内的一切机构。有人说英国的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行政长官也有类似的通天术。于是现实中行政肆意干预司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部门一个附属机构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也是导致腐败和司法功能瘫痪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同样激烈,如主体意识的淡薄、不适应淘汰机制等都是其表现。
由此可见,文化整合已成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需要对文化进行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同时,对人们的观念、意识产生剧烈的冲击。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地增强,主体观念也在滋长,“君子言义不言利”的观念正在改变,传统文化中的“礼”正被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则所代替。从这一角度来说,目前的文化整合也具有自发需要的社会基础。
二、法学教育应是文化整合的前沿阵地
文化无非是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习惯等价值的体系。法律本身是一些规范,而这些规范是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所支配的。尽管法律不是文化的全部,但法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主干部分,构成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行为规范及价值取向。可以说法律直接体现了文化,运载了文化,法律可以使文化在一定的民族扎根,成为该民族的是非善恶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只是文化的外衣、存在形式,各民族无不把统治者倡导的主流价值确立为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由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人们对很多的价值观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他们相约尊重彼此的自由,即追求各自的价值的自由,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法律的发达。所以,把现代文化定义为“法治文化”,从某一角度来说是恰当的。既然文化与法密切相关,文化常常仰赖法的昭示,那么文化的整合同样离不开法这一形式的参与,而且法学应是最好的参与形式,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这除了由于法学与文化密切相关外,更是由于法学另一个特点———它是实践性极强、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触手可碰的学科,法学上的问题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也是对文化的概括,但它们都不具有法律那么强的实践性,成为每天碰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用现代法律理念去塑造我们的国民个性时,它具有极具体的针对性———针对日常生活,或经济行为,或政治态度。这一工程的完成将导致整个民族的意识体系的变化,而不是与实践相脱节的抽象的说教。[page]
由于法学与文化的“亲戚”关系,通过法学教育而重塑国民个性、民族文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与中国一样同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早已实践着这一工程。日本的法学教育截然不同于美国。美国的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律师,培养其法律执业能力。“美国的法学院主要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各种技术性训练,为此,案例教学法被广泛采用,这使得学生得以马上进入职业训练实质性阶段……”。[3](P699)在美国,学生学习法律的结果基本上就是选择律师职业,这一教育模式可称为职业教育。而日本的法学教育却不这么简单。根据其教学内容和方法,其法学教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类似于中国的本科、研究生的学院式教育,另一阶段是“司法研修所”的培训,而这二者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在日本,获得法学学士后,要想从事法律职业,必须通过严格的司法考试,这一考试的通过率约为2%-3%.[3](P700)通过司法考试后即可进入司法研修所学习,学习期间为两年。两年期满后还有一次严格的考试,这一阶段的考试大约只有10%的通过率,通过者获得担任法官的资格,其他人则可以做律师或检察官。日本的两个阶段的法学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是截然不同的。第一阶段是对法的基本原理、内容的学习。这一阶段属文化的层面,旨在促成国民对法的恰当的理解,培养其对法律的感情以形成法治的社会土壤,这一阶段的教育可称为“素质教育”。在第二个阶段,即“司法研修所”的培训,这一阶段的目的、方法截然不同于前一阶段,而与美国的法学教育有颇多相似之处,即通过法律实务问题的分析训练,培养学生的职业思维习惯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以及职业道德等,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职业教育”。从统计数据来看,在日本,具有法学学士学位而不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比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多得多,他们大多在政府、公司的管理部门。根据1985年对日本统治集团的一项调查,高级官僚中毕业于法科的占压倒性多数,达67.3%.[3](P703)为什么日本的法学教育不同于美国而分为“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阶段?并且保留大量受了法律教育的人在政府管理部门?事实上,日本那些大量的具有法学学士学位而在政府或其他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对日本法治的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受了现代法的精神的熏陶,并把这些精神带入国家、社会的管理中。他们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管理对象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的管理对象不得不基于这些价值取向而预测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些价值观也就成为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这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的变迁———由传统的儒家的价值取向转向法治的价值取向。
为什么美国的法学教育没有“素质教育”一环?关于这一点,理由很简单。因为日本所体现的“素质教育”塑造的内容就是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基因为日本本土所缺,于是要进行“文化补课”。但法治却是在欧洲本土萌芽壮大的,自古希腊时代就有法治的传统,后来又较早地发育了法治文化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后来,法治文化随着欧洲在北美的移民也扩散到了美国,甚至获得了更深更广的发展。所以,法治意识是欧美的根本性文化,而勿需人为的移植、栽培。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晚于日本也落后于日本。因为中国更长期更全面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支配,而儒家文化常常与法治文化相异、甚至相反。所以,日本的法学教育的实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要做的文化整合工作也比日本更艰巨、更广泛。
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的价值取舍、思维方式。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是在后天环境中耳濡目染、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不能有意识地去改变它。而用异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去替换已有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就叫做“文化移植”,其整个清理、统合的系统工程就叫“文化整合”。人类发展到现在,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形成的因素除了家庭及社会环境外,更为重要的莫过于教育。当然,教育只是一种手段。我们既可以通过这一手段以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武装国民的大脑,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以法治文化而为之。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化过程的理性工程。经挑选,人们把符合社会进步的意识“填入”人类的大脑,从而促进人类的进步。[page]
尽管影响人的意识的因素不胜枚举,但只有教育才可能是理性地、系统地针对全民族的每一分子而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教育最应成为文化整合的前沿阵地。文化整合的前沿阵地决不是某些知识分子的书屋———它们只是文化整合工程的设计室或指挥部。只有教育才可能使整个民族在各方面实现文化的系统移植或变迁。在这里,一方面,旧文化的行为模式、成因、其反人性的一面被批判;另一方面,新文化产生的历史哲学基础、行为模式被阐释并成为国民可“操作”的思维武器。
三、作为高等教育公共课程的《法律基础教程》
在中国,法学教育既有法律专业的教育,又有作为公共课程的法律常识的教育。笔者认为除了应对法律专业的学生进行现代法的精神熏陶外,更应充分利用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广泛地实践文化整合这一工程,即把《法律基础教程》的教学作为文化整合的广阔的前沿阵地。
然而,目前这一课程的设置并不令人满意。从教材的内容结构上来看,由于它覆盖了包括法理、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整个法律体系的主要制度,课程设置的目的似乎与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对臣民的要求相同,即知法、守法。循规蹈矩即为良民,否则为刁民。但是,仅凭《法律基础教程》一门课就希望公民知法,这似太强人所难了。事实上,即使一个受了四年法学专业教育的本科生,如果没有为律师资格之类的“行业准入”资格证而进行系统的复习的话,他们也不可能真正熟练掌握、运用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难怪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学完了法律基础之后只记得有民法、刑法等名词,至于其具体制度则又原物归还给了老师。更要引起重视的是这一课程的目标定位没有使学生获得对法的全新的认识,形成对法的亲切感。
笔者认为,正如前文所言,进行全民族的文化整合势在必行,而公共课《法律基础教程》的教学作为阵地是恰当的。但这门课程应作如下调整:
第一,关于本课程的目的。改变法仅仅是随心所欲的工具的价值定位,使国民从法是义务的堆积向法是自由的保障的全新认识。从而形成法对其有用、使其受益的对法的亲近感,并获得现代文化、现代价值观体验,增强其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免疫力。
第二,关于本课程的内容。在设计本课程的内容时应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即一方面揭示传统文化中的重礼轻法与法治文化中的法律至上的相悖之处,此为“破”;另一方面,介绍法治文化的主体构架,此为“立”。在教材内容的编写上应体现这一思想。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应为本课程的重要内容:
1、法的概念、特征、产生条件。此外重点介绍法与道德的关系,这是基于传统文化中礼法不分的原因;另外还有法与政党的政策的关系,这是基于中国只有一个执政党的原因。
2、法治的现代内容。其内容因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但最基本的有七、八项。这些内容在传统文化中是缺乏“基因”的,如法律至上、良法之治、程序正当、司法最终、司法独立、权力制约等。每一项内容应作为一节,安排不少于两个课时的时间。
3、各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这一部分内容设置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中华法系向来是“诸法合体”的,对部门法的介绍可促进国民对现代法律体系的了解;二是发端于西方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不一致。这一内容的设置既增加了国民对具体制度的理解,使其成为可“操作”的思维武器,又能加深国民对法的精神的把握。
第三,关于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本课程应大量采用案例教学法,既可使用日常的被人忽略的小事或政府行为,又可使用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等。用案例展现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行为模式,分析其中的缺陷及其产生的根源,同时阐明现代法治文化的构成、行为模式。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对糟粕文化的免疫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个体对传统文化只有模糊的理性认识,对法治文化的行为模式又知之不多,由于传统文化已成为其潜意识的一部分,那么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中作出行为模式的选择时,他只能选择传统的行为模式。这正是我们目前教育的缺陷。[page]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赵云芬 阳继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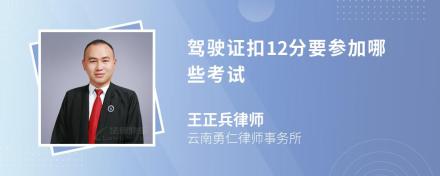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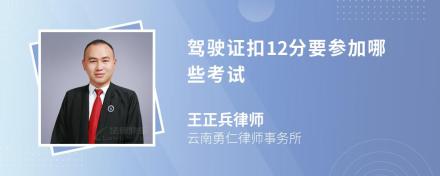


 01:30
人已看
01:30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