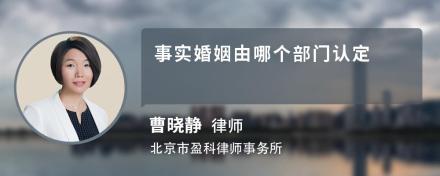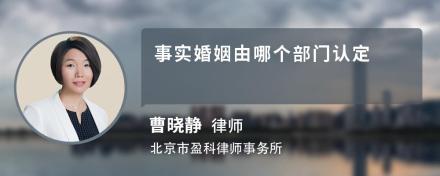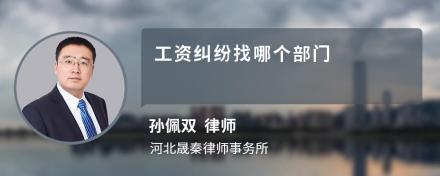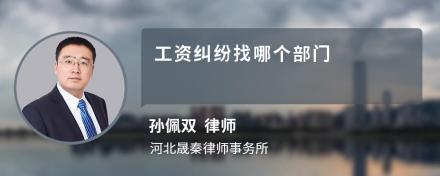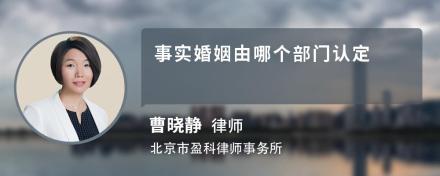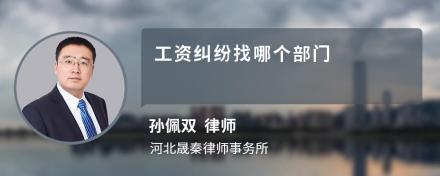立宪政府政治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定是关于地方政府的设计。——(美)斯蒂芬·L·埃尔金:《新宪政论》
在西方国家,过去二十多年来,许多理论被应用于地方政府或地方治理的研究。分析这些理论,对于深化地方制度研究、指导地方治理实践和了解地方政府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一、地方政府理论
对地方权力进行研究一直是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但真正以地方政府权力结构为研究中心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
根据地方政府理论论述问题的侧重点,地方政府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地方政府理论,主要审视了地方政府在广泛的地方政治制度框架内的运行方式,且主要研究在欧美的大城市的情形。这类理论起源于美国的政治学传统。以美国的F.亨特(Floyd Hunter)对亚特兰大市的研究和罗伯特A.达尔(R.A.Dahl)对纽黑文市的研究为先导,这类理论试图对日益影响地方政治过程的经济利益给予关注,另一方面,也试图说明地方政府结构变化和全球化对地方政治过程的影响。
另一类地方政府理论,主要是讨论地方政府与其他政府间的关系。这类理论主要以英国的经验为依据,且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方式给予特别的关注,其主要兴趣在于,地方政府多大程度上有不受中央政府控制而实行自治。但近年来,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扩大到其他方面,特别是欧盟政策过程的作用、新的大区机构和单一职能地方政府等的研究。[1]
概括而言,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
(一)多元论(pluralism)
多元论是国家机构主要理论的渊源之一,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为将政治学从狭隘的宪法假设中解脱出来作出了贡献。
多元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达尔。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该书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地方政府三个最主要的政策问题——城市重建、公共教育政策和政治任命——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他发现,当时有各种团体、个人参与了这三个方面的决策,政治权力很分散,每个个人或团体都拥有各种资源,有其在特定专属领域的影响力,但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足以垄断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例如,工商业团体对城市重建较有发言权,但是对教育的影响较小。政治决策总是倾向于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经过“在多元民主中领导人与公民间形成的关系复杂的共生和变化过程”而产生。据此,他指出,纽黑文市的地方政治是以“分散的非对称性”(dispersed unequalities)为主要特征的多元性政治。
邓里维(Dunleavy)和汉普敦(Hampton)等多元论者认为,地方政治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政治决策过程只有在大多数居民达成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主要包括:(1)竞争性政治团体向选民提出方案以获得制定政治制度的权力;(2)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制约与平衡为主要特征,以预防任何个别团体进行绝对的控制;(3 )政治制度对广大代表不同政治见解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公开的(这些利益集团因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具有合法性);(4 )政治事务由独立的提供各种政治见解并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审查的媒体进行分析和讨论。
多元论者假设,地方决策制度具有复杂的特征,但它是公开和透明的,能够回应大多数人的意愿;多元论者还假设,地方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法律资格将大多数居民的意志转化为政策措施。多元论者受到政治学者和和社会学家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多元主义。新多元主义认为,在政策决策过程中,若要充分表述意见、充分参与、影响决策,乃至顺利执行,相关的民间团体、政府部门、学者与专家,应形成一个有高度共识、凝聚力的网络。[page]
(二)精英论(elite theory)
有关地方政府的另一种学说是精英论。这一理论认为,政治控制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社会名流手中,地方重大的政治方案通常是由这些精英起决定作用,而地方各级官员予以配合来实现少数人的意志。实际上,精英论的提出在时间上要早于达尔提出的多元论。
亨特是精英论的代表。他曾以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决策层的层级和权力运行的过程,并于1953年出版了《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一书。亨特认为,地方权力通常由不超过40人的集团行使,其中实业界的利益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他通过调查得到了一个中选率最高的12人名单,他发现这12人是40 人权力精英的核心。他得出结论:少数实业界代表对决策后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决策集团中,经济利益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多元论者的批评,还认为它只关注政府的正式决策过程,忽略了非政府领袖、社会精英的影响。P.巴赫拉兹(Bachratz)和M.巴拉兹( Baratz)1970 年在《权力与贫穷》这本书中,对多元论者提出了两方面的批评,并指出:(1)达尔没有认真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且其选择纽黑文的政策领域是武断的;(2)达尔研究的是得到权力集团允许的提案,他根本无法研究那些尚在构想或酝酿阶段就已被社会权力结构否决驳回的提案,而获得允许的提案,也许更可能是不能真正影响资源分配和既定权力结构的琐碎小事。
精英论者与多元论者的交锋专注于美国地方政府的研究,长期以来,对英国地方政府研究产生的影响不大。邓里维认为,这主要源于英国地方政府研究者的保守主义倾向。
时至今日,地方政府研究中的精英论与多元论的争论仍在继续。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Marxism)
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地方政府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支新的学派,并迅速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设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但关于国家的作用,除了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现代国家的行为机关不过是全部资产那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之外,马克思所述不多,也许这是造成后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解不一的原因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家履行着对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至关重要的两种主要的职能:一是国家提供市场不能供给、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十分重要的广泛的一般必要条件,包括法律制度、交通运输设施和为确保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所必要的教育培训制度;二是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调节阶级矛盾。西方学者并将国家这两种职能概括为国家的“资本积累职能”和“维护职能”。
由于对国家与统治阶级关系程度的理解的不同,存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流派:工具主义流派和结构主义流派。前者重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主张,认为国家纯粹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后者则认为,尽管国家维护资本主义的普遍、长远的利益,但资产阶级内部结构中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要求国家机构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协调阶级矛盾。另外,结构主义者还认为,国家不仅是统治阶级结构中不同派别利益冲突的裁判人,同时要对付劳动人民的反抗,因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中心舞台。
这些不同流派反映到地方国家方面,也有不同的主张。有的赞成马克思主义,有的不赞成。工具主义者科克本(Cockburn)提出,地方政府不过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旨在维护资本主义在地方再生产的条件;结构主义者卡斯特尔斯(Castells),将地方国家机关看作是组织“集体消费”如卫生、教育、住宅和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认为它具有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缓和社会矛盾的双重作用。[page]
对上述地方国家的“资本积累职能”和“维护职能”的观点,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能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方政府改革现象,如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大大减少,并未危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或社会秩序的平衡;也不能用地方国家机构提供集体消费或社会消费福利的观点,来解释地方政府将原先提供的住宅服务签约外包;他们认为不能由市场提供的有些地方服务也私有化了。另外,上述理论也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进行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一方面,地方议会抵制中央政府改革,不符合地方政府是国家机构的分支的观点;另一方面,不能认为中央政府采取严厉方式对付地方政府,是对当地劳动人民反抗的一种反应。
二、地方治理理论
近几十年来,西方各国地方政府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和发展,如欧盟地方自治章程的签署、法国的地方分权、英国的权力下放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给地方政府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的地方政府理论不能完全适应需要。如英国中央政府将过去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一些服务交由联合委员会或联合机构等准政府机构、私人公司或民间自愿组织管理,地方政府对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能减少,地方政府由原来的公共服务的惟一或主要的提供者,变成地方上各种准政府机构、私人公司或民间自愿组织等复杂网络的策略指导者。所以,在地方政府制度中,除了“地方政府”的概念外,“地方治理”的概念也越来越为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所接受。[3]
“治理”常被一般地认为是普遍的统治过程;特别是指在统治过程中,非政府行动者和政府的关系。
1997年,杰索普认为,“治理”越来越流行地被视为社会关系合作的所有形式的概括用法,或是涉及非市场力量或正式阶层的合作形式。“治理”的普遍性定义应该是:“组织间关系的自我组织”。
1998年,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已经提出了五种主要的观点。这五种观点分别是:(1)治理是指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的复杂体系;(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4]
“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与“地方政府统治”(local 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不同。
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与“政府统治”一样,“治理”作为一种政治过程,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治理”与“政府统治”至少有两个区别:(1)“治理”与“政府统治”的最基本的或是本质性的区别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一定是政府机关,而“政府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2)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 “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5]
概括而言,有关地方治理的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实力-依赖关系论(power-dependence in central –local relations)
实力-依赖关系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罗兹(Rhodes)。实力-依赖关系论试图对英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理论阐释,被作为地方治理的理论之一。[page]
实力-依赖关系论假定,中央与地方都有办法对付另一方及其他组织。但这里的办法是指宪法、法律、组织、财政以外的各种对策,如政治、信息、执行任务等方面的对策。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试图调动其所掌握的资源使其影响最大化,并将对对方的依赖降到最小,但没有一方能够完全掌握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宪法、法律、组织、财政、政治、信息资源。因此,尽管有个别的政府可能按科层结构组织外,大多数的政府组织都是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资源交换是相互依赖的结果。
罗兹试图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特别指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加强,对社会政治的治理,已由一个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互动系统所主导,它既非市场,也非国家,但与以上两者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个互动系统就是“政策网络”。政策网络依政策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鉴于政策网络具有相互重合的特征,罗兹将英国的政府制度说成是“变异政体”。
罗兹认为,权力可能会在某些集合体中集中,但国家的变异结构产生了相互依赖,其潜在的权力并不能总是被动员。这种分析模式暗示,中央政府受到比过去更复杂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在内部,中央受到自身部门化和协调其他组织能力的限制;在外部,中央要依赖其他组织实施其政策。因此,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对其他组织发号施令,或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下级政府。为取得政策目标,中央政府必须通过广泛的政策网络起作用,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作用,否则将不可避免产生政策混乱。
实力-依赖关系论受到了诸如理论不够宏观、政策网络封闭性、中央与地方合作关系不明确等批评,但经验和实施结果,证明着这种理论原则的意义和政策网络的价值。例如,罗兹应用这一理论原则,审视了英国自1979年至1995年地方政府的发展变化,指出其中的政策失误和后果,并认为中央政府未参考政策网络是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
(二)政权论(regime theory)
美国学者斯通(Stone)1989年从他在美国亚特兰大所作的研究中,提出“都市政权”的概念。斯通指出:“都市政权是一种非正式但相对稳定的、易于获得体制内资源的集合体,这一资源使之在决策中保持持久的作用”。“政权论”的观念较倾向于新多元论,强调了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并注意到成长机器(growth machine)未能关注的其他冲突和妥协的政治过程。
与美国城市政治学的传统一样,“政权论”也关注权力问题,但与“多元论”和“精英论”不同,斯通将对于都市政治辩论的设问由[谁统治?]转向[如何统治?].“政权论”认为地方政治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征,要受相互依赖关系而非简单的、科层权力关系的制约。地方政治制度呈现出控制的分散性,都市权力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间,被分解成复杂的关系网络,都市政府的回应常常造成政策的偏离和意外的后果。因此,关键的问题是,都市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进行合作以取得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政权论”者更关注都市政府和非政府的行动者在复杂情况下有效进行地方治理是如何结盟的,而不太关注由谁控制这些结盟。斯通认为,权力的概念应该是 “power to”而非“power over”;同时承认权力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商业利益通常在都市地方政治制度中所占据的优越地位,但都市的政治家和公众并非是无权的。不仅都市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而且它们还承担着保护广大公众利益的角色。尽管都市政府不具有控制地方经济的能力或充当竞争社会组织仲裁者的地位,但它“更有可能成为社会资源的动员者和协调者”。
“政权论”强调应改变都市政府角色,以适应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转变。斯通认为,政府和非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有助于建立对领域广泛的活动的直接和有力的控制”。为了实行有效治理,地方政治家应承认都市地方政府独立行动是有限的:“都市政府应将自己的职能与各种非政府的职能结合起来”。尽管这里含蓄着都市政府并非事事要听从居民意愿且政策选择也不一定非要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意思,但地方政府毕竟是民意机关。因此,“政权论”暗含了地方民主与政策效率的交替使用。[page]
“政权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与成长机器之类的概念不同,“政权论”提出存在不同的“政权”模式。斯托克认为,“政权论”的实质就是政策选择的模式,公共政策由三个要素决定:(1)一个治理联盟的组成;(2)治理联盟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本质;(3)成员带入治理联盟內的资源。因此,治理联盟并非在社会和经济的真空中运作,而是回应不同时空脉络下社会经济环境的问题和变化。斯通将“政权”分为维护型政权、重建型政权、中产阶级累进型政权和下层阶级机会扩张型政权四种模式,并认为资源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既然“政权”是可行的,“政权”就必须能够动员为满足政策议程所需要的资源。
斯通提出的 “政权论”主要是针对美国地方治理的情形。为了保持在横跨各个个案研究时“政权”概念的解释力,英国学者道廷(Dowding)1999年在应用政权概念研究英国伦敦六个自治市后,提出“政权”的八点特征。尽管道廷认为,将“政权论”应用于所有地方是错误的,但也强调“政权论”的几点优点,尤其是,“政权论”方法很好地说明地方联盟采取的不同形式,而且解释了与地方政党控制以外因素有关的差别。
尽管“政权论”能够描述发生在美国一些城市的问题,但不足以解释权力分配的动因。因此,与罗兹提出的权力-依赖关系论一样,“政权论”也面临着批评,被认为“充其量是描述了一种模型或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理论”。另外,也有人认为,斯通对亚特兰大市的政治分析,过分强调了“政权”的地方性特征,没有看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
(三)调节论(regulation theory)
由于“政权论”比较关注城市发展的经济层面,并采取地方性的取向,忽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地方政治与外来力量的连结,而受到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的讨论中将“调节论”带入城市政治的范畴,引入社会调节的观点,试图找到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
调节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是一个矛盾冲突的过程,必须要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调节机制,即所谓的社会调解机制(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才能支持资本积累的再生产。
1989年斯托克首次将“调节论”应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研究。斯托克总结出地方政府在英国二十世纪当中所扮演的三种角色,并认为每一种角色都与资本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关:(1)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地方政府主要是提供和管理基础设施,为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2)在战后进入福特主义时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履行诸如供气、供电和供水、住房和教育等社会福利的职能,地方政府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的工具;(3)70年代,开始从福特主义转型进入后福特主义时期,地方政府角色也随之转换,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服务的签外包、在民选的地方议会控制之外设立地方准政府公共机构、私人部门对地方政府影响增大等;同样,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化,如出现了更分散的公共服务消费方式、以消费者为本的服务理念增强等,也改变着地方政府的传统角色。此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使用了更灵活的劳动管理方法,弱化了等级结构,并引进了新公共管理技术等。
1994年鲍勃·杰索普论述了后福特主义下国家的角色转变,认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形式的转变,其实可以用从“凯恩斯福利国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 KWS)到“熊彼得工作福利国家”(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SWS)的转变来分析。他认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终将被“熊彼得工作福利国家”所取代,并提出国家要重新考虑在不同地理层面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问题,特别是认为中央政府可以上移职能(给欧盟跨国机构),也可以下移职能(给新的和已有的地方和地区机构)。
1995年迈耶(Mayer)认为,在过去二十年来,都市政治有许多改变,这些改变似乎跨地域地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表现在:(1)地方政治在发展战略了中扮演重要角色;(2)在经济发展的支持下,地方政府的动员性增强,且伴随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附属品;(3)地方政治行为的范畴扩张,并涉及大批地方政府以及一系列私人部门和准公共行政部门的行动者。这些都市政治的改变,其实就暗含了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都市治理形式的转变。[page]
调节论中,后又发展出都市“政权论”与“调节论”的结合。如劳拉(Lauria)在1997年和1999年,认为都市政治的研究取向,应结合新都市政治理论和调节论,产生一个重构的都市“政权论”,并认为都市政权是社会调节模式的一部分。
葛德文(Goodwin)和潘特(Painter)1997年提出,将“调节论”引入“政权论”前,应先从方法论的取向检视社会调节模式的观点。认为应将社会模式看作是一个过程,且调节过程与社会实践是在时空中互为组成的,所以有天然在地理和历史上不均等的特性。
注释:
[1] Hugh Atkinson and Stuart Wilks-Heeg, Local Government from Thatcher to Blair ( London: Polity Pres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pp34-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3]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4] Gerry Stoker,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55, March 1998.
[5]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载《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任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