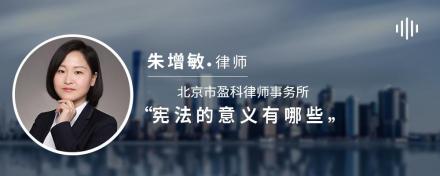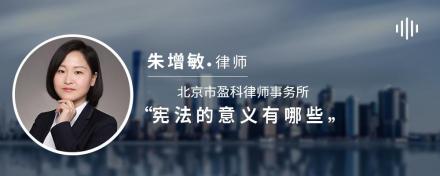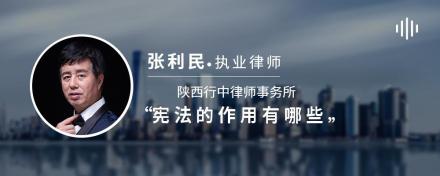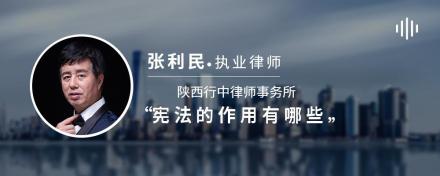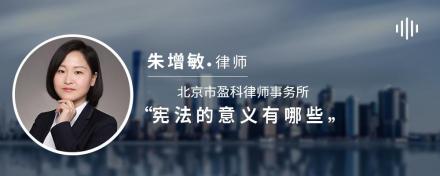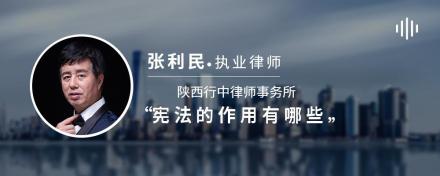引言2003年5月3日,是《日本国宪法》实施56周年的日子 .现在再回过头来端详这部曾以其树立的彻底的和平原则而享誉世界的宪法,是否青山依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岁月流逝,和平宪法尽管在形式上未变一词一句,但是实质上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和平宪法已经名存实亡。《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性从有到无,不是某一条宪法修正案造成的,也不是某些国会议员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政治、法律、思想根源。而作为《日本国宪法》三大基石之一的“和平”原则的消失必将对日本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下面仅就与《日本国宪法》和平性的消失有关的和平性的体现、和平性消失的方式以及原因、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这对深入了解战后日本政治、唤起国民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高度警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日本国宪法》和平性的体现
《日本国宪法》被誉为和平宪法,顾名思义,是因为该宪法强烈、充分地表达了日本希望和平的愿望与决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日本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渴求。
《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性集中表现在它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日本国宪法》第二章“放弃战争”仅有一个条文即第九条。该宪法没有将第九条放在补则等别的章中,而是将其单独列出作为一章,放在第三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之前,这首先从形式上表明了该条的重要性。在内容上,可以看到该条分为两款,为: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该条表达了两项基本意图:(一)放弃任何战争;(二)废除军备。并且在时间上是“永远”,即不是当时的暂时措施,而是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1].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九条前款并没有区别战争的性质,它在规定禁止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战争的同时,并没有允许为了自卫的战争,因为日本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都是打着自卫的旗号进行的,声称“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日本是为了自卫而打仗”[2].1931年日本发布的宣战诏书中就极力强调日本开战的理由是“奋起自卫”。并且,退一步说,自卫战争说到底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所以,应该把第九条规定的放弃战争理解为放弃所有意义上的战争,而不是有所区别,这样才是符合立法原意的。为了完全有效地放弃战争,最重要的是废除军备。因为如果没有军备,即使想进行战争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款进一步规定“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该款中的“战争”一词历来也是争议颇多的,争论的焦点是它是否包括自卫战争。根据系统解释的方法,由于后款与前款紧密相连,该“战争”也应解释为一切战争。因此为了自卫而保持战争力量也是禁止的。
很多人认为《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性仅仅体现在第九条,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性还体现在其序言中。
也许有人认为不应该将序言与第九条等量齐观,因为宪法序言的效力还有待商榷。关于宪法序言理论界存在“无效力说”和“有效力说”之争,有的学者通过对部分效力说的批判,结合以上两种学说,还提出了“模糊效力说”。我认为序言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理应具有宪法一样的法律效力,各国的宪法实践也承认了这点[3].宪法序言是有效力的,它的效力形式因其内容的多样性而呈现出多样性(这反映了立宪者对宪法效力的多元化需求)。譬如说,宪法序言中的目的性内容对宪法的修改、解释有着指导作用;史论性内容体现了序言的确认作用,它使宪法确认的史实和结论成为法律上免证的事实。《日本国宪法》的序言是原则性内容,它具有以下效力:(一)指导宪法解释,控制宪法解释的随意性;(二)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三)弥补宪法漏洞。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相提并论。[page]
《日本国宪法》的序言体现了在整部宪法中一以贯之的“民主、人权、和平”三大原则,定下了整部宪法的基调。该宪法在序言中庄严宣告:“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全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日本国民期望永久和平,深怀支配人类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生存与安全。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持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除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狭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地位。我们确认 ,世界各国国民同等享有在和平中生存并免除恐怖与贫乏的权利。”陈辞之慷慨激越,半个多世纪后仍掷地有声。其确立的彻底的和平原则,表现出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珍视,更道出了亿万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的心声。
序言与第九条遥相呼应,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根据第九条的规定,日本将不像过去那样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平素准备战争力量,一旦出现国际争端通过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加以解决,而是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样一来,日本靠什么保持其安全和生存呢?对于这个问题,序言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生存与安全。”关于这点,在日本很早以前就有“所谓他国的善意等,在今天国际社会的现实中,一旦发生国际争端时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尤其在日本独立后,又有这种意见:“如果独立国只想通过信赖其他国民的善意保持自己的安全和生存,既不妥当又不负责任”。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原子能时代,只靠本国武力保持本国的安全和生存是不可能的。原子武器及其他现代武器有可能带来特大规模的毁坏,甚至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如果不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和信义,那么怎样做才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呢?《日本国宪法》的序言及第九条的规定为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向世界的永久和平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受其影响,《禁止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限制战争、控制军备的多边条约相继签订。这些条约在内容上与《日本国宪法》异曲同工,都是为了人类的总体利益,国家放弃了一部分主权(因为为了自卫而保持战争力量、行使交战权是国家主权的应有之意。);在精神上,则反映了日本人民及其他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的价值观,放弃战争、废除军备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日本国宪法》确立彻底的和平原则,这在实践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引领了世界潮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精神已灰飞烟灭,但是它曾经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如果说《日本国宪法》的和平性仅体现在序言和第二章,那么未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该宪法的每一章、每一条都闪现着和平的光辉。以上都是从正面论述《日本国宪法》和平性的表现,我们不妨按照比较法的方法,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再从反面挖掘其和平性。现仅就第一、三章试做简要分析。
《日本国宪法》的第一章为天皇。该章否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的以天皇为中心、主权属于天皇的国家政治体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从而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天皇处于虚位状态,是虚位元首,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只具有礼仪性和象征意义。考察世界各国的宪法,不管国家元首是享有广泛实权,还是仅为一虚位,一国的元首通常都拥有对外宣布战争等程序上的职权[4].如我国宪法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等权力。而法国、美国等总统制国家的元首则具有实体上的权力。法国总统是军队的统帅 ,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美国总统是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应召为合众国服现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而天皇不仅没有涉及战争、军队的实体性权力,连与此有关的程序性权力也没有。[page]
《日本国宪法》的第三章为国民的权利与义务。该章的条文达31条,是该宪法中条文数量最多的一章,但是却没有规定国民服兵役的义务,甚至连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也没有规定。
在现行宪法中确立和平原则的国家除日本外,还有德国、意大利。但是为何《日本国宪法》以其和平性享誉全球,而德国、意大利宪法却默默无闻呢?
原因很简单,德国、意大利放弃的只是侵略战争 ,而日本用根本法的形式表明放弃的是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5],确立的是彻底的和平原则。现以德国宪法为例作简单比较。德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导致扰乱各国之间的和平关系,特别是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以及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作的行为是违宪的。它们被定为应受惩处的犯法行为。除获得联邦政府的许可外,不得制造、运送或贩卖作战用武器。”与此同时,宪法赋予了联邦总统任免军官和军士的权力,联邦国防部的武装部队指挥权,联邦关于国防的立法权、建立武装部队的权力等等。其关于战争、军队的正面条款之多与《日本国宪法》相应条款的缺位相比判若云泥,一般的和平原则与彻底的和平原则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彻底的和平原则在世界宪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难怪麦克阿瑟1952年5月在美国联邦议会上院发表演讲时说,在这部宪法中如果说有感动日本国民的感情的地方,那么正是这个原则[6].也正是由于其确立了彻底的和平原则,《日本国宪法》被世人称为和平宪法。
二、《日本国宪法》和平性的消失
56年前《日本国宪法》以其确立的彻底的和平原则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里程碑,谁又能想到其和平精神只犹如昙花一现,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向政治大国的迈进,和平宪法已经是明日黄花,杳不可寻。《日本国宪法》的蜕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和平宪法从实至名归到名不副实再到名存实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辈学者都是分阶段论述其蜕变的过程,我现在试从其蜕变的方式进行探讨。《日本国宪法》的和平原则是通过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宪法解释、宪法判例、条约、法律五种方式被篡改、架空的。
(一)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
这是日本被占领时期对宪法进行实质修改的主要方式。根据《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宣言》)的规定从1945年8月28日到1952年4月27日日本一直处于盟军的占领之下。《波茨坦宣言》规定:“投降后天皇及其日本政府的权限,将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这样一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就成为占领时期日本的最高权力者[7].他的命令对占领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唯盟军最高司令官马首是瞻。
1950年7月8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写信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由7.5万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海上保安厅人员8000名。吉田接令后,立即着手组建工作,于8月招募了第一批队员。所谓“警察预备队”(即后来的自卫队),实际上是一支由美军提供装备并受美军军官指挥的正规军[8].从此,日本结束了战后五年没有军队的历史,开始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这与宪法中日本不拥有武装力量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
(二)宪法解释
吉田内阁于1952年11月25日公布“有关战争力量的统一见解”,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第2、3、5、8条,即:2.“战争力量”,是指具备能够完成现代战争程度的装备和编制而言。3.“战争力量”的标准,必须以该国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环境具体判断。5.“战争力量”,是指人的和物的组织起来的综合力量。因此,仅仅武器本身虽然是构成战争力量的因素,但不是“战争力量” 本身。武器制造工厂当然也是同样。8.保安队和警备队不相当于“战争力量”。[page]
在实践过程中以上统一见解会产生使日本实际战争力量不断加强的恶果。首先,什么是能够完成现代战争的装备和编制意义不明确,“战争力量”的标准是一个变量,日本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解释;其次,为保安队和警备队增加人数、更新武器找到了借口,打着“保安队”和“警备队”的旗号,日本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发展军事力量;最后,为日本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大量制造武器开了绿灯。
鸠山内阁于1955年3月29日公布了有关宪法的统一解释。该解释表达了这样的认识:第九条第1款禁止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第2 款禁止的战争力量也是为完成这一目的的战争力量;宪法并没有放弃为了自卫的交战权。
比较吉田时期和鸠山时期的宪法解释,我们发现前者是补充解释,是为了弥补第九条中“战争力量”过于抽象的缺陷将其具体化所作的解释,后者是限缩解释,将战争解释为侵略战争。这是从解释的方法上进行划分,但是从解释的合宪性考察,这两个解释都是违宪解释。因为宪法解释必须以宪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而上述解释是与《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那么该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民主、人权、和平三原则。因为《日本国宪法》就是以这三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这三原则的具体化、系统化。
从法理上来讲,一切成文宪法都是根据一定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因而其解释必须在不否定其基本原则的范围内进行。当宪法赖以存在的原则本身被否定时,从逻辑上为宪法所不容许。对宪法的一些条款进行解释是必要的,但前提是不能与宪法的原则相违背。如果违背了宪法原则,那就超越了解释权的界限。和平原则是《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上述解释都是与该原则相背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宪法解释的实质都是以“解释宪法”的伎俩,篡改和平宪法。
(三)宪法判例
宪法判例是法院可以援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依据的具有宪法效力的判决。从《日本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上级法院决定中的结论对下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所做出的决定具有拘束力”可以看出在日本判例是一种法律渊源。
突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判例主要是1959年12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就是著名的“砂川事件”判决。 “砂川事件”是这样的:1957年7月,当东京都当局为扩建位于砂川镇的美军机场进行测量时,遭遇反对派的抗议示威,部分抗议者推倒了机场的栅栏并闯入机场,其中7人被警察当局逮捕,并以违反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制定的《刑事特别法》为由被起诉。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依据国家行为(acts of state)理论回避了对《刑事特别法》和《日美安全条约》的合宪性审查,而是在判决中指出:《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放弃战争,禁止保有武装力量,并没有否定日本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所固有的自卫权,作为国家固有权利的行使,日本为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障国家的存立,当然可以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日本国宪法》并没有禁止我国为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向外国寻求安全保障,驻留在日本的外国军队不应该理解为“战争力量”[9].该判决除将《日本国宪法》所放弃的战争限缩解释为侵略战争外,还认可了日本向外寻求战争力量的行为。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实际上默认了《日美安全条约》的合宪性。为了使日本摆脱宪法的羁绊,日本最高法院可谓用心良苦。
(四)条约
日本最高法院在对“砂川事件”做出的判决中认定对国家存立有着重要影响的高度政治性的条约是否违宪的审查,司法机关要受到政府和议会的制约。这使政府和议会的立场具有了权威性。 而日本政府认为与国家安危相关的条约有高于宪法的效力,其他条约的效力则低于宪法,但高于一般法律。就这样条约都以“与国家安危相关”为名堂而皇之地摆脱了宪法的控制。[page]
1. 1951年《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
这两个条约准许日本逐渐增强其自卫力量,日本成为美军基地,被纳入美国在远东的集体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战略体系,日本置于了美国的保护之下。
2. 1960年《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