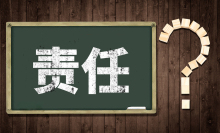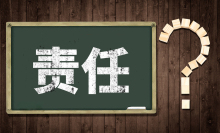在德国,处理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问题的侵权制度称为“危险责任”。德国是高危险民事责任的故乡,现代意义上的高危险民事责任发端于德国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企业法》,该法第25条规定:“铁路公司运输的人及物,或因转运之事故对别的人及物造成损害,应负赔偿责任,容易致人损害的企业虽企业主毫无过失,亦不得以无过失为免除赔偿的理由。”《普鲁士铁路企业法》这一条关于铁路交通事故的规定拉开了现代高危险民事责任的序幕,在为侵权行为法开辟新的领域、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到来了危机,它标志着侵权行为法甚至整个私法社会化历程的开始。
一、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概念
德国立法对危险责任的概念并未做出明确界定,因此在对危险责任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上,各学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是指“某特定企业物品或装置的所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问其有无过失,对于此特定企业、物品或装置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所负担的责任。”1而《德国民商法导论》的作者认为,“当一个人承担损害赔偿,仅仅是因为导致损害发生的某种特定的危险活动处于其控制之下时”,始称危险责任。2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拉伦茨则认为,危险责任是指“对物或者企业的危险所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绝对责任。”3
危险责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危险责任,即从语言意义上而言,是指因危险事故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狭义上的危险责任,即从私法角度而言,是指对因危险活动事故而发生的的民事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而在狭义的危险责任中,即在因危险活动致人损害的情形下,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有合同关系的,如受害人是加害人的雇员;另一种是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受害者是无辜的第三人。基于此,危险责任又可以分为“合同上的危险责任”和“合同外的危险责任。”上述各学者虽然在对危险责任的理解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但在对危险责任本质的认识上却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危险责任是以无过错责任为基础的责任类型,指的均为“合同外的危险责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是指危险活动的从事者对因危险活动事故导致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中加害人不存在过失不能成为其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法中还有一个与危险责任非常相似的概念,即危险归责,依德国著名学者拉伦兹的观点,危险归责包含以下三个类型:第一是危险责任;第二是在权利状态尚未终局确定前,一方面允许某人从事强制执行或为保全请求权的行为,但其他方面又在一定条件下使其负担因此所生的危险;第三是指为他人利益而从事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事务。由此可见,危险责任与危险归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危险责任只是危险归责中较为重要的一类。在德国,危险责任是与传统过错责任相对称的责任类型,二者同时构成德国侵权责任法的双轨体系。4
二、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
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损害的发生是由于危险物或危险作业所致,那么危险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危险作业的作业人即应对损害负赔偿责任,不问其对于损害的发生是否存有过失,这一思想与传统侵权行为法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过错责任相反。危险责任不是对不法行为所负的责任。危险责任的本旨不是在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行为的制裁,而是在于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强调的是分配正义。德国法上危险责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危险来源说。没有航空器或汽车的发明,就绝对不会有航空事故和汽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电力和核能的发现、利用,也决不会发生电力致人损害和核能泄露、爆炸事故。因为危险企业、物品或装置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制造了危险来源,因此应对由于危险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危险不一定会引发事故,但损害的发生仍有很大的可能。
其次,危险控制说。从事危险活动的人、危险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最能控制这些危险,因此,由这些人承担由于危险引起的损害可以有效防止、或者减少损害的发生,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再次,利益说。利益说是支撑危险责任最为有力的理论依据。该说认为,危险活动的从事者,危险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之所以对由于其危险性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他们在从事危险活动、持有或拥有危险物的过程种获得了利益,并且是由于其为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将危险带给了广大民众,而且这种利益往往是由于行业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化身。享受利益,承担在追逐利益过程中的损害风险,这合乎情理与法理。
最后,损害分散说。该说认为,让从事危险活动或持有、拥有危险物的人承担危险责任的原因在于这些人最便于将因危险活动而造成的损害通过商品的价格机制而予以转移。5
而我国台湾学者曾世雄教授则认为,德国法上危险责任得以确立、发展的原因除上述理由外,还有出于举证责任困难这一层面的考虑,对于企业使用机器或利用核能所发生的事故,在过失责任制度下,受害人请求赔偿时应就赔偿义务人的过失负举证责任,但现代危险活动多系高科技的产物,诸如航空器的构造、维修、飞行安全等属于专门知识,普通的受害人无能力为赔偿义务人有过失之举证,况且损害事故一旦发生,通常情况下设备已遭破坏,纵有专门知识也难以完成对受害人存有过失的证明。因此,如果固执于过错责任,则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为弥补过错责任的这一缺陷,危险责任便应运而生。6
三、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基本类型及其内容
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完全是由特别法来完成规制的,德国法上规制危险责任的特别法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较为重要的《损害赔偿法》。该法制定于1871年,其后经多次修改,曾试图将所有的危险责任类型与内容都纳入其中,以实现对危险责任的综合性规制和统一立法。但由于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和某些危险责任类型的特殊性及国际性,德国《损害赔偿法》的这一有益尝试未能实现。因此,现行的德国《损害赔偿法》仍然是包括若干危险责任类型的特别立法,是德国危险责任的重心。德国《损害赔偿法》规定的危险责任类型有以下两类:一为铁路事故责任;二为电力、煤气设备责任;在德国,除《损害赔偿法》对危险责任作出规制外,另外还有一些特别法对危险责任作出了规定,其他特别法上的危险责任类型主要有《道路交通法》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航空法》规定的航空事故责任、《 火车及电车物损害赔偿法》规定的火车、电车对物损害责任、《原子能法》规定的核能损害责任、《采矿法》规定的矿害责任、《水利规制法》规定的水污染责任和《国家狩猎法》规定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等。
(一)德国《损害赔偿损法》上的危险责任类型及其内容
德国《损害赔偿法》在我国有的文献中又称《帝国责任法》或者《国家责任法》。该法虽制定于1871年,但就其所规制的主要内容而言,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企业法》。德国《损害赔偿法》在其制定时规定的危险责任类型有铁路事故责任和雇佣人责任两大类。该法自制定以来,历经多次修改,其所规定的危险责任类型及内容也经历了多次增删。根据该法1978年1月4日的修订,现行德国《损害赔偿法》上的危险责任类型及其主要内容如下:
1、铁路事故责任
铁路事故责任是德国法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危险责任类型。其最早见诸于德国1838年《普鲁士铁路企业法》的规定。根据该法第25条的规定,《普鲁士铁路企业法》上的铁路事故责任的基本内容为:对铁路营运事故所造成的损害,不论受害人是旅客还是第三人,不论事故造成的是人身伤害还是财产损害,铁路企业均应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或者不可抗力所致。《普鲁士铁路企业法》第25条关于铁路交通事故的规定被1871年的《损害赔偿法》采纳而成为联邦法,通行德国全境。德国1871年《损害赔偿法》在采纳《普鲁士铁路企业法》关于铁路事故责任的过程中,虽然对铁路事故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基本精神未作改变,但在制度内容的具体构建上仍作了不小的变动。德国1871年德《损害赔偿法》将铁路事故造成的他人损害适用危险责任的范围仅限于人身伤害,对于铁路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害不能适用危险责任,仍需按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德国《损害赔偿法》将铁路事故适用危险责任限于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的立场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德国《损害赔偿法》也历经多次修改,但其对铁路事故责任适用危险责任限于人身伤害的立场从未有过改变,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根据1978年1月4日的修正案,铁路企业对“由于不可抗力和第三人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因为“不可抗力是大自然外在和固有的力量,而第三人的行为后果即使是采取最最极端的预防措施也难以防止。”7德国法上铁路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适用危险责任的前提是损害必须是在铁路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由诸如紧急刹车、火车脱轨、列车放电、信号失灵等任何技术操作导致的损害,都属于铁路运行事故造成的损害。铁路事故责任根据危险归责实行无过错责任,但允许加害人通过证明免责事由的存在而予以抗辩。在赔偿范围上,铁路事故责任实行限额赔偿,采取年金给付制,每人每年最高额不得超过1.5万马克。
2、电力、煤气设备责任
电力、煤气设备责任在原先的德国《损害赔偿法》中是没有的,这一责任类型是在1943年德国《损害赔偿法》第5次修改时增设的。德国法上的电力、煤气设备责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对因电力、煤气作用而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时,电力、煤气设备的持有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二是电力、煤气设备的持有人对由于其设备的存在而非因电力或煤气的作用而对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如果在损害发生之际,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该设备既合乎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无瑕疵,那么加害人能得以免责。1978年的修正将该责任进一步扩展到由管道输送的液体、烟气所造成的损害。
电力、煤气设备责任的完全免责事由有两个,一为不可抗力,但对于因供给设备的导线脱落所造成的损害,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免责理由。二为损害系由建筑物内的设备所致,而损害发生在该建筑物内或该设备营运人占有的土地内。如果损害的发生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那么加害人能减轻或者免除其责任。
电力、煤气设备责任也实行限额赔偿,对于人身伤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年金1.5马克,财产损害的最高限额为一次事故2.5马克。
(二)其他特别法上的危险责任类型
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德国法上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规定最早见于1909年的《汽车交通法》,依该法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汽车占有人对在汽车营运过程中造成的他人人身伤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果其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故所致,则其能免责。《汽车交通法》在1952年进行了全盘修正,改名为《道路交通法》。根据该法第7条的规定,机动车的管理人(通常不一定是机动车的所有人)必须对任何因机动车的“营运”而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管理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包括:“如果事故是由既不能归因于车辆制造瑕疵,也不能归因于车辆部件失灵的无法避免的事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事件尤指可归因于受害人或与车辆的驾驶无关的第三人或动物的行为,而机动车的管理人尽到了当时情势所需的注意义务的事件。”根据《道路交通法》的这一规定,机动车的管理人必须对轮胎脱落、轮轴因金属疲劳而断裂、刹车或方向盘失灵等车辆部件发生的问题负责,即使这些问题是不可预见和无法防止的。但是,如果事件是由于“外部原因”引起的,如恶劣的天气、路况不好、动物从机动车前跑过、或其他车辆的驾驶技术不佳等,只要机动车的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和驾驶员显示了“当时情势所需要的全部注意义务,”他就可以免责。德国法院将这种注意义务解释为一种“超出正常标准的注意,一种极端的和考虑周全的注意和审慎,”8但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事故是“不可避免”的情形非常罕见。9
2、航空事故责任
德国的航空业起步较早,也比较发达,因此对航空事故的无过错责任立法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德国在1914年就有了这方面的草案,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该草案直到1922年才正式完成并付诸实施,命名为《航空法》。1968年该法经过全面修订,但其名称未变。根据《航空法》的相关规定,航空事故责任是指飞机在营运之际,因意外事故造成乘客以外的人员于死亡或伤害身体或健康、或毁损承运货物以外的财物,飞机的占有人对其所生的损害应负的赔偿责任。这种损害是指在地球表面造成的损害,不管是飞行噪音造成的,还是由于飞机失事或迫降所造成的。
由于航空飞行的危险极大,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有鉴于此,德国《航空法》并未规定航空事故责任的免责事由。一般认为,加害人即使能够证明损害的发生起因于不可抗力,飞机的管理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与铁路事故责任和电力、煤气设备责任一样,航空事故责任同样实行限额责任赔偿,不同的是航空事故责任对人造成的伤害不实行年金给付制度,而采取总额给付,即一次性赔付,对人身伤害的最高限额为20万马克,对财产损害的最高限额为每件5000马克。而对物所造成的损害,原则上依飞机或承运货物的重量,按比例折算。
3、火车、电车对物损害责任
《德国损害赔偿法》上的铁路事故责任按危险责任处理只限于对人造成的伤害,对物造成的损害不能适用。这一规定虽受到众多批评,但一直未有修正。这一局面直到1940年《 火车及电车物损害赔偿法》的出台才得以改变。根据该法的相关规定,火车或电车在营运过程中导致他人财物受到损害的,营运人应负赔偿责任,除非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故”或者不可抗力所致。在赔偿范围上,对动产采取限额赔偿,一次事故造成的动产毁损的赔偿以2.5万马克为最高额。对于不动产按民法的一般规定处理,不实行限额赔偿。
4、核能损害赔偿责任
德国现行的核能损害赔偿责任规定于1959年的《原子能法》。核能损害责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核能的制造或加工设备,因其运转产生核裂变或放出放射性物质的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设备的持有人对所产生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损害如果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加害人也不能免责;二为非因核设备运转而产生的核分裂作用或放射性物质的放射而引起的核能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核能设备的持有人对此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损害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加害人可以免责。
核能损害责任实行限额赔偿责任制度,对人造成的伤害,每人的年金以1.5万马克为上限;对物造成的损害,原则上以物的“一般价格”为准,但核能设备的持有人对一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害的赔偿额以25亿马克为限。
由于核能的潜在破坏能力相当巨大,核能事故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个人、企业无能为力,有时连国家也难以应付。有鉴于此,德国《原子能法》在对核能损害事故作出规定的同时,也设计了两项配套制度:一为责任基金制度,即从事核能设备的企业在开业之初必须将一定金额存入银行,作为损害发生时的“赔偿准备金”。当损害发生时,由该基金支付;二为国家限额补充赔偿责任制度。即在核损害事故发生以后,当企业在动用了责任基金以后仍不足以支付赔偿额时,则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但国家承担的赔偿的数额以不超过5亿马克为限。超过该范围的损害,任何人均可以不负赔偿责任。
5、矿害责任
德国在1980年公布的《采矿法》中规定了矿害责任。根据该法规定,矿害责任是指矿山占有人或矿业产权人因采矿对土地所有人之不动产或其从物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只有损害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情况下,加害人才能免于承担民事责任。所谓采矿作业包括试探性采矿作业和在未取得批准前的探矿作业。
6、水污染责任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德国,水污染并未被视为环境污染现象而成为环境法的调整范畴,水污染与环境污染概念无关。水污染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危险责任的一个分支而独立发展。水污染危险责任规定于1957年制定的《水利规制法》(该法有的学者将其译为《联邦水利法》)中。根据该法的相关规定,德国法上水污染危险责任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物质排入河流、湖泊、大海或地下水等水体中,使得水体原来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属性发生改变而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排放人对所造成的损害即使是不可抗力所致亦应负赔偿责任。(2)因在从事制造、贮藏、加工、堆积、运输、或废弃物品的活动中,从其设备流出物质到水体中,造成水污染而致他人损害,该设备的所有人对此损害所负的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损害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那么加害人能够免责。
德国将水污染责任作为危险责任的一个类型是德国危险责任立法的一大特色。德国法上水污染的危险责任还有与其他危险责任不同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关于水污染的危险责任的赔偿范围很广,不论是人体伤害还是财产损害都可以得到赔偿,同时,加害人对此损害承担无限责任,及于其个人一般财产。另外,关于水污染的危险责任没有限额赔偿制度的规定,因此,对受害人的赔偿数量没有限制。10
7、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责任
在德国法上,对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也属于危险责任调整的范围。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危险责任原来是由德国《国家狩猎法》规定的,今天,这一危险责任类型规定于德国的《联邦狩猎法》。根据该法第26条到第35条的规定,二蹄兽(鹿、猪)或野兔等野生动物对土地及土地上的植物加以损害的,狩猎合作社对此应负赔偿责任。德国之所以将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纳入危险责任调整的范畴,这主要是为了配合野生动物的保护所采取的举措。
四、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共性分析
德国对危险责任立法践行的是类型化的立法思路,危险责任依社会的需要而个别予以承认,通过以上对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属性:
第一,类推适用的禁止。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条款是封闭的,不能类推适用。这一立场在德国司法实践中被作为一项原则而被严格遵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4年11月7日的一项判决中认为:“通过特别条款规定的对特定危险状态和设备的危险责任使用于其他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危险设备……是不允许的。”11早在1935年的一起涉及高压电线掉下来导致位于十字路口的步行者死亡的案件中,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就曾指出,不能“在没有衡平之最高责任限额规定的情况下超越现行法将危险责任的规定延伸至电力设备领域。”12立法者在认为必要时会引进“无须证明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既然没有这样做,就说明他们是拒绝这样一个偏于极端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延续了这一司法实践,它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侵入立法领域而在没有特别法规定的情形下对责任构成进行延伸适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从来没有对特别法作过哪怕是扩张性的解释。13
第二、实行限额赔偿。通过以上对德国法上各个危险责任类型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危险责任的损害赔偿一般都有一定最高金额限制。实行限额赔偿的立法旨意在于使承担危险责任的主体可预见并预算其所负担的危险责任,而依其经济能力,从事保险。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企业从事对人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危险活动,推动科技创新。
第三、赔偿范围的限制 .在对危险责任赔偿范围的规制上,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最富有特色。德国法上的危险责任从未许可过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的例外迄今只见于军用飞行器造成的地面第三人损害(德国《航空法》第53条第3款)和欧洲人权公约下的不法剥夺自由的责任;另外,纯粹经济损失也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水利规制法》第22条。而且除了人身伤害外,在危险责任领域内通常只赔偿有体物的损害,不包括无体物的损害,德国法上的所有的危险责任条款均以“被致死、身体或健康遭到损害或物遭到破坏”为前提。14著名的比较私法学者冯?巴尔曾指出:“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仅是德国危险责任的特色,它不过是一个走向误区的制度和理论体系的结果而已” .15
注释: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2[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3Larenz,Karl,Lehrbuch des Schuldrechets,1987,541.
4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6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7[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8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见《保险法期刊》,1962年卷,第164页,转引自[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9[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10参见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页。
11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74年11月7日之判决,载BGHZ63,第234、237页。转引自[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页。
12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35年4月11日之判决,载BGHZ147,第353、355页。转引自[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页。
13[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页。
14参见德国《航空法》第33条,《道路交通法》第7条。
15[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472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博士·赵家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