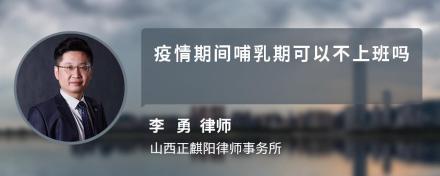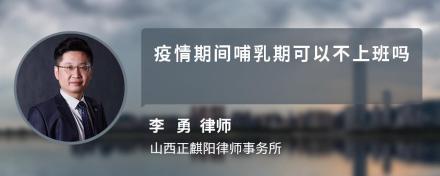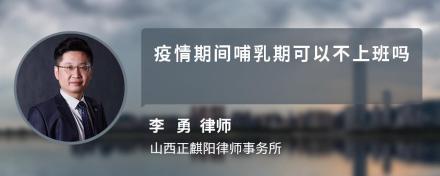羊水栓塞纠纷
案情介绍:某产妇因孕39周第一胎、不规则腹痛14小时,已见红、破水,于某日10:30入某县妇幼保健院(下称A医院)。入院诊断:宫内孕39周,左枕前位临产,妊娠高血压症。入院后宫缩不规律,予1%催产素静脉滴注。12:38分在侧切、胎吸下娩出一女婴。产后出血200ml,给予催产素20单位肌注,子宫收缩好,血压112/68mmHg。产后30分钟血压开始下降,子宫收缩好,压迫宫底,阴道流出约200g血块,立即补液、止血、吸氧。产后1小时产妇开始出现意识障碍,血压为0mmHg,阴道持续流出多量不凝血,先后两次行清宫术及腹部加压,未清出胎盘及胎膜样组织。产后10.5小时产妇意识转清,血压回升。产后21小时产妇呕吐咖啡色物,无尿,皮肤出现淤血斑,即请某医学院附属医院(B医院)妇产科主任前来会诊,考虑羊水栓塞、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肾功能衰竭,静脉予呋塞米(速尿)200mg、肝素50mg等,输注同型血900ml,但仍无尿,阴道持续流出不凝血。产后29小时转入B医院。入B医院时患者生命体征尚平稳,血压120/90mmHg。全身高度水肿,注射和穿刺部位有大片淤血斑,阴道持续流出不凝血。肝功能、肾功能及心肌酶各项均明显异常。B医院入院诊断:羊水栓塞,DIC引起心、肝、肾等多器官功能衰竭。经积极输液、输血,应用肝素和止血、利尿、强心剂等救治措施,于转院后10小时(产后39小时)抢救无效死亡。
患者死亡后,家属向县卫生局提起医疗事故鉴定申请。县医鉴委认为产妇直接死亡的原因可定为羊水栓塞、DIC 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家属对此结果不服,继而向市、省两级医鉴委提出复议。市、省两级医鉴委的鉴定结论否定了羊水栓塞的诊断,认为A医院对该产妇产后出血原因未能及时明确诊断,抢救措施不得力,以致出现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B医院会诊时未做详细检查,即同意羊水栓塞的诊断,并使用肝素,诊治措施欠妥。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医疗纠纷定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两家医院对医鉴委的鉴定结果不服,县人民法院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下称鉴定中心)对此案进行了论证。鉴定中心邀请北京数家大型医院妇产科专家对案情进行技术分析后,做出如下司法医学技术鉴定:①该例羊水栓塞的诊断可成立。②A医院在该产妇的救治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得力而及时的。虽有欠妥之处,但作为县级妇幼保健院,受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又因羊水栓塞的死亡率极高,因此该院的抢救基本符合医疗抢救原则,不构成医疗过失。③被鉴定人在转入B医院后,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已严重衰竭,难以救治。虽然病程晚期使用肝素为选择时机上的错误,但与其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
在法庭辩论中,A医院辩称:在该产妇救治过程中,经上级医院专家会诊诊断为“羊水栓塞”。全院上下竭尽全力,多方会诊,采取有利措施使产妇生命体征平稳后,由专人护送转至上级医院。我院对该产妇的死亡,无过失责任。B医院辩称:我院非本案当事人,县、市、省三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都是针对该产妇与A医院的医疗纠纷做出的。产妇在A医院住院期间,我院妇产科主任前往会诊,但与患者并未形成直接医患关系,故对诊断治疗不负有任何责任。患者转我院后,虽形成了医患关系,但我院医疗行为并无过错。
法院审定结论:该产妇与被告的医疗纠纷属于一级医疗技术事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的规定,省级医鉴委的鉴定为最终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不能否定省级医鉴委的终极鉴定。B医院妇产科主任在为该产妇会诊时,已构成了医患关系。虽然各级医疗事故鉴定是针对A医院做出的,但在鉴定结论中说明了会诊诊断仍同意“羊水栓塞”并在转院后应用肝素治疗是欠妥的,所以应为产妇死亡承担一定责任。两被告应赔偿因产妇死亡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87 531.33元和精神损害费3万元。
2 案例分析
记者:为什么羊水栓塞容易引起医疗纠纷?
边旭明(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羊水栓塞是产科罕见的、极其危重的并发症,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死亡率在80%以上,多数患者在发生肺栓塞后几分钟内死亡,往往猝不及救。随后发生的DIC,ARF、严重休克及多器官功能衰竭,也使临床处理非常困难。有的产科医生一生也遇不到一例。我到协和医院20年间,也仅遇到了3例。这3例中,2例抢救成功,但协和医院的诊治水平不能代表全国医院产科技术的整体水平。许多羊水栓塞发生在基层医院,受医生诊断经验和医院设备条件的影响,死亡率极高。因为羊水栓塞的发生率极低,所以我们在产前向家属交代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时,一般不将此列入交代范围,实际工作中也不可能把所有罕见的并发症都向每位产妇家属交代。而一旦发生羊水栓塞导致产妇死亡后,家属往往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加之对羊水栓塞这一并发症的危急程度不了解,会认为医院在处理分娩过程中有失误,而引发纠纷。
谢培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教授):羊水栓塞的病情复杂而危重。本病例在抢救过程中存在一定缺陷,但并不是造成产妇死亡的直接原因。不能把医学上的绝症称作医疗事故,社会上有些舆论很不负责,是违背科学的,长此以往,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是无利的。
孙东东(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据我了解,近年产科引起的医疗纠纷,占所有医疗纠纷的20%左右。目前产妇各类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比例大约是千分之一点五,由此而引发的医疗纠纷也随之增多。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育龄的提前、胎儿发育过大等因素有关。
记者:本案中,医鉴委的鉴定结论和司法医学鉴定结论相佐,主要矛盾点在于羊水栓塞的诊断是否成立,这也是判断是否存在医疗过失的焦点。您认为本例羊水栓塞的诊断能成立么?
边旭明:羊水栓塞的确凿诊断需要尸检获得病理学资料。此例未行尸检,所以羊水栓塞只是临床诊断。本例的突出表现是DIC以及由此引起的失血性休克。DIC是羊水栓塞的二期主要表现,但引起DIC的产科并发症有许多,故不好推测其DIC确实为羊水栓塞所致。
孙东东:虽然从专科角度讲,诊断最确凿的依据是尸检获得病理学资料。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尸检率相当的低,如果拘泥于此,将有许多案例无法做出判断。即便在临床上,许多死亡诊断也是靠排除法推断出来的。法医学鉴定必须要拿出一个结论来,有时处于两难局面。根据临床表现和过程,对死亡做出的推断性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不可能说,没有尸检就不能做出死亡诊断了。而且,从另一角度讲,没有尸检,也无法完全推翻羊水栓塞的诊断。在修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时,曾提出过所有引起医疗纠纷的案例均应行尸检。但这与国情不符,我国公民的观念尚未转变,家属不愿意配合,难以接受尸检。目前我国医院死亡病例的尸检率极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使得许多医疗纠纷的裁定很困难。[page]
刘培友(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本人认为该例司法鉴定羊水栓塞的认定不可成立。 当前,临床诊断符合病理诊断率尚存在很大距离,而临床诊断羊水栓塞的病理诊断符合率差距更大。近有作者报道32例妊娠死亡的尸检结果,临床诊断羊水栓塞16例,法医病理学诊断羊水栓塞仅2例,符合率为12.5%。在此案中,对羊水栓塞诊断的质疑集中在产妇没有经过尸检。若本例司法鉴定羊水栓塞成立,有如把只有12.5%的几率泛化为是100%的事实,于鉴定属大忌,实属没有根据的结论。正因为认定为羊水栓塞了,羊水栓塞属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死亡率高,由此对“本例在诊治过程中存在一些处理不当”也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只有教训可汲取,而不是与死亡有因果关系的过错了。
尽管司法鉴定中心的如此鉴定结论,法院对本例的审定结论倒是难得的,既认定了A医院的过错后果责任,还认定了B医院也要承担过错后果责任。的确,B医院虽只是受医院所邀会诊,这也已事实地发生了通过A医院而与病员的关系,况且在转入B医院之后也有不当医疗行为。
医疗过程中发生了纠纷,依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走上了医疗鉴定的程序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当进入诉讼,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举证提出异义,需司法鉴定显然更难了。一旦司法鉴定的结论出现不实或瑕疵,欲予纠正,那又难上难。因此,作为法医学鉴定,需更遵从于客观事实,把鉴定结论牢固地立足于以客观的依据为前提,不容依从于推理与分析。
记者:羊水栓塞的救治难度在哪里呢?临床上有许多类似的难以避免的医疗并发症,是否能够认为系医务人员过失行为造成的医疗事故呢?
边旭明:羊水栓塞是产科的危重并发症,但其主要病变是肺栓塞、DIC等,这些急症的救治大大超过了产科医生常规的业务范畴。而且,它的发生发展太迅速,常常不容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患者即死亡,所以,救治难度很大。产科医生能做到的,就是及早发现征兆,及时诊断,果断采取急救措施维持生命,并请心血管内科、血液科医生到场实施进一步的抢救。因此,就羊水栓塞的诊治难度及其难以预见性,和产科医生的知识面来讲,它的发生并不存在明确的医源性因素,它是目前医学科学发展水平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的并发症,不应算做医疗事故。
参加司法医学鉴定会议的妇产科专家们在鉴定中认为,本例在诊治过程中存在一些处理不当,虽然与产妇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有下列教训需要产科医生汲取:①入院时宫口已开全,胎头很低,胎心不好,这时静脉用1%催产素,浓度偏高,以0.5%的浓度较好。②产后32分钟时,子宫出血400ml,但血压已降至42/22mmHg,出血量与血压不符,此时考虑羊水栓塞血液呈高凝状态、过敏性休克,应及时给予肝素和地塞米松,而不应再用止血剂进一步消耗凝血物质。③产后近3小时,患者已深昏迷,阴道出血不止,不应再清宫及腹部加压,因清宫将进一步促进宫壁血管内的羊水进入血液循环。④产后3.5小时内科会诊诊断失血性休克,未进一步检查失血原因。若此时发现血液不凝,及早考虑切除子宫,可避免羊水继续进入血液循环。⑤对肾功能衰竭重视不够,利尿药剂量不足,且发现尿少后补液量未减,产后18小时内补液量达8300ml。⑥在产后21小时和29小时还使用肝素,显然是错误的,时机掌握不当,进一步加重了血液不凝状态。
记者:在法院庭审中,医疗事故鉴定和法医鉴定哪一个更公正?此案例的判决,法院依从了省级医疗事故鉴定,您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是否合理公正?
刘革新(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主任法医师):司法医学鉴定是由法医鉴定机构所做出的,当然是由一两个法医主持的。虽然法医都是学医的出身,也不能全面掌握临床各科知识,所以鉴定时通常要聘请数位该学科的专家,对欲鉴定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鉴定结论。只不过出于对专家保护的目的,仅将主持该案的法医做为鉴定人。因此,司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医鉴委是一致的。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医患双方都有可能对医鉴委的鉴定提出强有力的质疑,那么这一证据的证明力就需要法庭进一步考证。由于医学的专业性较强,法官不可能也不应该自己对此做出判定。在这种情况下,委托司法医学鉴定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司法医学鉴定可以根据案情及庭审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予以分析,如本案中“羊水栓塞”诊断是否成立?对该病人的治疗是否及时准确?A医院是否有责任?作为上级医院的B医院是否有责任及其责任大小?从而明确审判中所要解决的有无侵仅事实、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侵权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问题,以真正全面适应司法审判的需要。而医鉴委的结论仅仅确定是否医疗事故。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强调指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
孙东东:就有关医疗纠纷的鉴定而言,法医学鉴定注重从因果关系上判断医疗行为有无过失;而医疗事故鉴定往往侧重从临床过程中分析有无过失,这就容易形成两家鉴定结论恰好相反的局面。在我们所接受的鉴定案例中,与医鉴委意见相佐的相对较多。由于法医学鉴定多从直接因果关系上进行推理分析,且鉴定人与双方当事人之间无利害关系,鉴定结论相对公正。两种鉴定只是法院在判决案子是否存在过失行为的依据,法院有权在两种结论中采信其中之一。一般来说,最初始的鉴定结论比较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原始记录删改和做假的概率比较低,但目前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实行是下级鉴定服从上一级鉴定的原则。至于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不好断言正确与否,但可能有人为因素在里面。
程宗璋(北京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保护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依个人之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法院的最终判决应依据医疗事故鉴定还是法医鉴定。法院之所以有权在两种鉴定中采信其一,是由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所确认的“只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做出的结论才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与作为国家基本法的三大诉讼法相冲突所造成的。事实上,根据法制的统一性要求,行政与司法应保持一致,而且行政调处纠纷的裁决,并非最终裁决,最终裁决权应归于司法。如遇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一的情况,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由参与鉴定的机构出庭质证,这样才能认清事实,避免暗箱操作。[page]
记者:在本案审理中,还有一个矛盾点,第二被告B医院称其妇产科主任在会诊时,为产妇做出的诊断和处理意见,并未形成医患关系。这样,即便诊治意见有误,也不承担过失责任。您认为,医生在院外会诊过程中,是否同接受会诊的患者形成直接医患关系?
程宗璋: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医患关系”的界定问题。“医患关系”在民法上属于一种“契约关系”,医患双方当事人即契约当事人。从我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和法律上来讲,医患关系中所称的“医”主要是指医疗单位及其医务工作者。本案中的B医院妇产科主任虽参与了会诊,但他与组织实施会诊的医疗单位的关系属于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而与患者并未直接形成某种“契约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医患关系。依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中的该妇产科主任及B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在此案中,对羊水栓塞诊断的质疑集中在产妇没有经过尸检。可见,尸检与否,对处理医疗纠纷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极低的尸检率,使医疗事故的鉴定难度大大增加,以致于出现了本案这样几家鉴定结论莫衷一是的局面。如果产妇死亡后,医生能及时动员家属进行尸检,家属在对医疗救治工作产生怀疑时也能及时提出尸检请求,那么,这个案子的处理,想必会简单明了许多。案例剖析的目的在于把事实摆出来,让公正说话,以便在今后类似的医疗纠纷案件中,于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本人,于病人及家属,都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