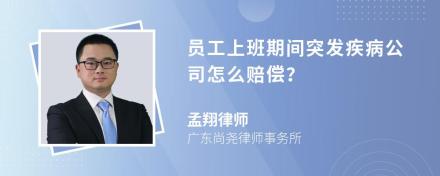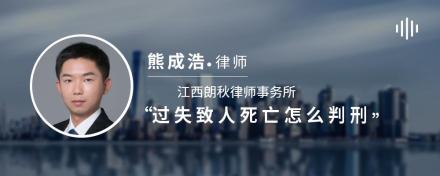相关知识推荐
-
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是否认定为工伤
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是否认定为工伤劳动部1996年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由于工作紧张突
工伤认定范围人看过
-
员工上班期间突发疾病公司怎么赔偿?
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自身原因的原有疾病不能申请赔偿的,如果是因工作原因导致的职业病或者是因工作原因
劳动法人看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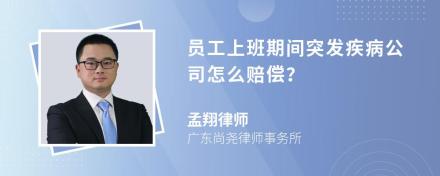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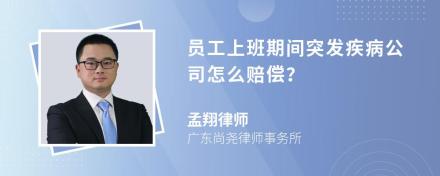
-
许某过失致人死亡案辩护词
许某过失致人死亡案辩护词许某过失致人死亡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许某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人看过
-
过失致人死亡罪立案标准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
刑事辩护人看过
-
过失致人死亡怎么判刑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
刑事辩护人看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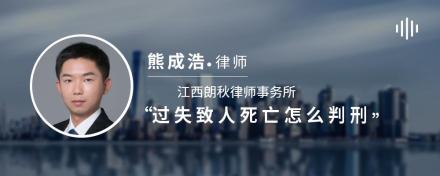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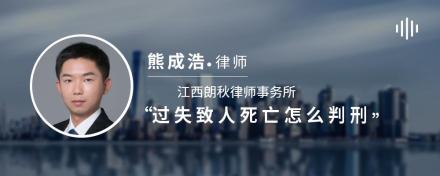
-
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属于工伤吗?
核心提示: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属于工伤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劳动法人看过
-
被动物咬了是谁负责
被动物咬了一般应当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负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若是其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
损害赔偿人看过
-
民事诉讼脑震荡赔偿范围有哪一些
因遭受人身损害导致脑震荡的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进行赔偿的范围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
损害赔偿人看过
-
《民法典》被人打成轻伤了可以要求民事赔偿吗
被人打成轻伤了可以要求民事赔偿。侵权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
损害赔偿人看过
-
《民法典》规定同等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怎么赔
同等责任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方式为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侵权
损害赔偿人看过
-
事故理赔费用怎么处理
事故理赔费用应当首先由当事人所购买的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承担,保险赔偿额不足以承担的,再由当事人自身的
损害赔偿人看过
-
污蔑罪怎么赔偿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没有污蔑罪,只有诽谤罪。赔偿的数额与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损害赔偿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