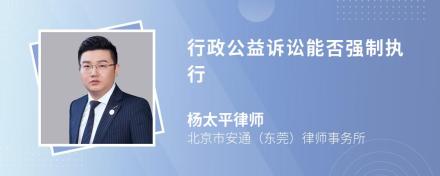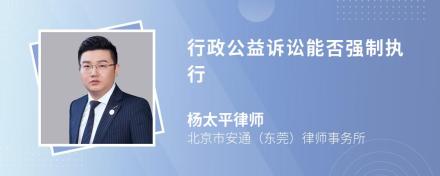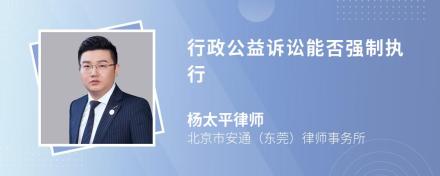公益行政诉讼是我国学界独创的一个概念,在国外并不存在,其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纳税人诉讼”和日本以及我国
台湾地区的“民众诉讼”。关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概念,学界虽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大多认为是指在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公民或组织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的一种诉讼类型。
范式,就是世界观,是一个学科范围内最广泛的共识单位,是人们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它包括概念、理论、观点、方法等。它是指导和解决问题的选择——直到另一个范式将其取代。范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巴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最早提出的。由于这一理论对于各门学科的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各自学科的发展规律有重要意义,故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的发展研究中。今天,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用来描述一种理论模型或思维方式,同时,也被应用于实践领域:作为重要社会学科的法学领域也存在一系列范式,如行政法学研究中的“控权论”范式、“平衡论”范式等。同样,作为行政诉讼法学研究领域之一的公益行政诉讼也存有一系列的范式,如开篇所述公益行政诉讼的概念就是范式之一。然而,当笔者对我国当前公益行政诉讼中的范式进行学习研究时,却时时感到由理论自身及理论与实践间的脱节而引发的困惑。因此,笔者尝试对其进行解读。
一、范式之一 ——公益行政诉讼必须有法律授权
换言之,该范式亦即若无法律授权,则不能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几乎是我国研究公益行政诉讼的学者皆持有的观点。该范式实际卜来源于保护规范理论,而保护规范理论的产生,则肇始于对公法上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划分。当法律规范之目的除保护公共利益外,尚有保障特定人之生命、身体及财产之法益时,受保护之个人即因该法规享有公法上之权利,而非仅享受到反射利益而已。即是否存在公法上权利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其一,应有法律之规定,且课于行政机关从事特定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其二,行政机关所负之义务是否在保护公民个人之法律上利益。简言之,设定法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公益,还兼有保护特定人的私益(这一法律目的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则该特定人具有公法上权利,得提起行政诉讼;而如果设定法规仅仅为了保护公益,则特定人仅具有反射利益,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所谓反射利益(又称法的寄生物),是指行政主体实现维护或增进一般公共利益时,反射带给私人的好处,此种好处并非法规设定行政主体义务的目的,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利益,人民“获之则幸,无之则命”。此范式被大多台湾学者所接受。照此范式,如欲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则必须有法律上的特别授权。比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有特别规定者为限”。譬如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民众是无权就环境污染事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台湾称之为民众诉讼)的,概“因其现行法律中,并无就空污事件设有民众诉讼条款”。
但随着现代法治理论的发展,上述范式无论在理沦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了挑战;在德国,以“镲锯事件”的判决为标志,法院开始承认国民之公法上权利,不以法律之明确规定为必要,而应以法律之日的为必要。尤其是有关国民生命、身体以及健康的权利,法院解释为除保护公益外,也有保护特定私人之目的。在有关公法亡请求权与反射利益之区别上,日本初始也接受德国之理论,同时法院也经常以反射利益之法理不予受理一般民众之起诉。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不少学者开始认为反射利益思想系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时代之产物,与福利国家的宪政原则不相符。更有学者提出“健康权”理论,即认为凡是保护人民生命、身体、安全或环境的行政权力,无论是否保护特定人之私益,皆视为公法上权利。这一时期,法院的判决也发生相应变化,承认宪法上之基本权利是人民公法上之权利,进而提出“裁量权收缩”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行政主体因裁量权收缩为零而有作为义务,已逐渐缩小反射利益之范围。总之,德日两国的发展趋势是:反射利益的公法权利化日益明显。与之同时,一些台湾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检讨。如台湾学者陈诚认为,公法上权利与反射利益二者的界限是流动的、相对的,“此系进步之法治国家均致力于将反射利益予以公法上之权利化,自课国家及其他行政主体一定之法律责任,使人民各种利益均有实现的管道”。
基于此,笔者认为,以必须有“法律的特别授权”,作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限制条件,无疑是对公民诉权的限制与剥夺。这不仅与公益行政诉讼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而且将会延缓我国的法治进程。况且,现实生活中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事项很多,如果苛求法律对每一事项逐一列举、授权,则既不可能亦不现实。
二、范式之二 ——我国目前立法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尚无规定,因此当前法院对于此类诉讼无法受理
这也是当前行政公益诉讼研究领域的流行范式。笔者认为,将“法律没有规定”作为一种否认行政公益诉讼的理由,看似有理,但仔细分析却不无牵强。因为法律来自社会实践,法律自身需要变革,过分强调法律的刚性,忽视法律自身的成长,必然会阻挡社会的进步。分析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固然有立法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司法实践的惯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第12条之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卜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按照通常的观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也有切身利害关系与非切身利害关系之分。不仅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自勺人享有原告资格,而且有间接利害关系甚至可能利害关系的人也都应该具有原告资格。应当说,《解释》的这一规定反映了现代行政诉讼法不断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趋势。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法律就是朝着允许全体公民起诉他们所感兴趣的任何行政裁决的方向发展”。而公益与私益在本质上并非对立,而是一致的,二者有时甚至交织在一起。德国学者鲁道夫·冯·叶林曾指出,“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力实现的情形下,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的权威、威严这样一个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也能感受得到的、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即一种能够保持个人所关注的交易性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也认为,就公益和私益的本质而言,公益的概念并非绝对排斥由基本权利所赋予人们的私益。因此,一切法律都必须建立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使个别成员的利益也得到满足这一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对公益的侵害就是对私益的侵害。
不幸的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把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解释为直接利害关系。这样一来,无疑将公益行政诉讼的大门关闭。如浙江沈李龙因举报某企业偷税,后认为税务机关查处不力,以“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诉国税局案;浙江画家严正学因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某“娱乐总汇”有色情表演行为未果后,诉台州椒江区文体局行政不作为案,都被法院以原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不具备主体资格为由而判败诉。笔者认为,按当前司法的发展趋势,法官不仅仅是审理案件,而更应当是通过审理案件这一方式获得决策参与权。正如埃尔曼所指出的,法官的司法审查行为是对政策制定权的一种分享,这一点昭然若揭,以至于在行使此种权威时,他已经很难托称他只是在适用法律了。现代法院的决策功能首先与其法律解释行为联系在一起,而法律解释行为要求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填补法律漏洞;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根据正义原则、衡平理念进行创造性解释或创制新判例。“在某些案件巾有必要离开法律文字(即狭义)去追求理智和公正所要求的内容,追寻公正本来的意图……:”因此,对于社会来说,法官的裁决已超㈩具体案件的范畴而波及到该纠纷涉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进而对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产牛影响:因此,如果说在这一问题上立法机构确有责任的话,那么对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来说则更是难辞其咎。作为司法实务界,在法律规定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应当调整行政诉讼实践的思路,转变观念,跳出现有范式窠臼,充分发掘现行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的内涵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该被动地等待立法机关制定、完善法律之后再去解决。因为法理产生于公理,法治应当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民对法官的要求不仅仅是忠实地执行法律,更应该是担负起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艰巨任务。
依照这一理论,如前所述的沈李龙起诉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完全可以立案受理。冈为国家收取税收的目的是为厂全社会的福利与发展公共事业,税收的减少也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投入的减少,因此,偷漏税行为不仅仅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也是对全体国民利益的损害。如果税务部门怠于查处偷漏税行为,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每个公民。(公益与私益达到了统一,并且交织在一起)。从这一角度讲,沈李龙作为公民个体起诉税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其虽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但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包括自己在内的公益,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应认定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然以原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否定其诉讼资格,则只能是司法实务界的悲哀;在我国当前法治进程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法律的欠缺与滞后并非短时期内能得到彻底改观,因此,与其被动地等待立法,倒不如像梁慧星先生所说的:“公益诉讼可以先从司法实践中做起,由法院的判例来推动其发展。”“因为尽管我国传统上接近于大陆法系,但“法官造法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一个小争的事实”。
三、范式之三 ——当前阶段,我国的公益行政诉讼应当由检察机关或社会团体提起,而不宜由公民个人提起
这一范式的理论基础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目前也仅仅处于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公民的法律素质普遍不高,因此由普通公民担当公益行政诉讼这一重任不现实,并且容易引发滥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笔者认为,且不说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是否名正言顺,单从宪政的角度看,禁止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一范式就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因为在法治国家里,接受司法裁判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法治国家里公民的社会生活关系不是受人的支配,而是受法的支配。为了解决公民之间因社会生活关系方面发生的法的纠纷,就必须保障公民有利用司法解决权利义务之归属的权利。何况公益行政诉讼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设立的诉讼制度,就更应该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允许能够更广泛的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提起诉讼。因此,将公民个人排除出诉讼主体殊不明智。
至于滥诉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全不必担忧。因为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打官司不为牟取私利,纯粹是为了社会公益,并且因为被告往往是强大的国家机关,因此要冒极大的风险;再加上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着“民不与官斗”、“和为贵”等观念,冈此普通公民个人是不会轻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另外,法院还可以通过严把立案审查关来加以限制,冈此,滥诉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从现实情况看,在我国已经出现的几起公益行政诉讼案件,并未出现如有些学者所担心的“捣蛋者诉讼”,因此,以所谓的滥诉理由禁止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甚至已经桎梏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科学进步的标志之一是把反常问题和未解决问题转变为已解决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领域存在的反常问题,就必须突破原有理论框架,更新观念,进行范式的重新构建。
作者: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