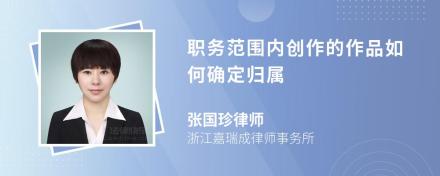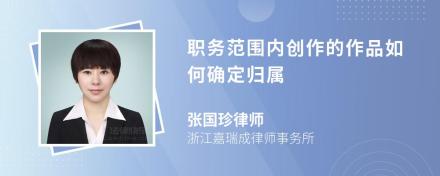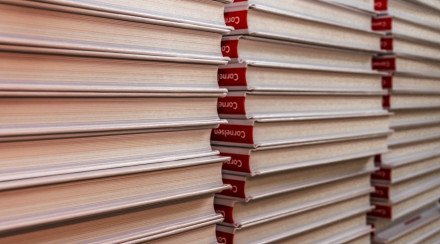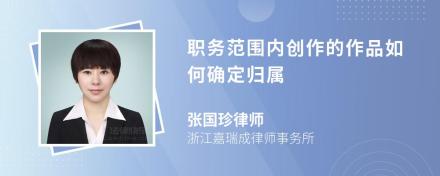编者按:
引用与抄袭同样都是一种写作手段,但其性质却迥然不同。前者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后者则属于违法侵权行为。本文认为,引用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这是引用的前提;引用必须坚持适当的原则;被引用的必须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人还没有发表的作品则不宜引用;引用必须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现实中作品的类型千差万别,无论引用还是抄袭,都有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任何的普遍之中都有特殊,一般之中都有个别,绝不可一概而论。
在作品的创作中,引用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手段,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领域,大概所有从事写作的人,没有人不会用到它。尤其在科学研究中,借用前人的学术成果,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知识,造福人类社会,是人所敬仰的高尚事业。学术论著中如果引用得当,不但道理说得清楚,还会给人留下知识渊博的美好印象。
然而,抄袭却不然。尽管抄袭也可以说是一种写作手段,但它是攫取别人劳动据为己有的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既不正当又不光彩,为社会鄙视也为人们所不齿。引用者主动声明,光明磊落,抄袭者卑劣龌龊,总是不肯承认;引用者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抄袭者遮遮掩掩,猥猥琐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引用是法律许可的公民权利,是合理使用,受到法律保护;抄袭剽窃则属于违法侵权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一旦被认定抄袭,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引用和抄袭,二者虽然性质不同、是非分明,但却有一个彼此相同的特征,它们都是对他人作品的使用。由于有此相同的“相貌”,二者很容易混淆,不好鉴别。
引用属于合理使用
在著作权法律中,规定了一种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公民可以依法对他人作品自由、无偿地使用而不侵权。这是国家为保护社会公众分享文化、艺术、科学成果而对权利人的著作权做出的一种限制。由于这种限制的实质是对社会公众和著作权人双方利益的一种平衡,对其适用范围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并不得随意扩大,因此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对该项制度的规定是:“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接着该条第二款列出了12项可以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况,其第二项就是引用:“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此外,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又对引用作了进一步的限制:“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是引用的前提
引用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这是引用的前提。就是说,判定是不是引用,首先要看引用的目的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法律规定的引用目的仅限于三个:一是推荐或介绍某一作品;二是分析或评论某一作品;三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或某一观点。除此三个目的之外使用他人作品,就不属于引用,就涉嫌抄袭。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有一篇以河流航行为背景的小说,有人发现其中大量的景物描写和国外一个作家的描写相同,显然,这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介绍、评论作品或者说明问题等三种引用目的,所以,其属于抄袭无疑。再如,在诗词作品中,一般也不存在法定的三种引用目的,如果一首诗或一首歌词的某一节某一段使用了他人的作品,当属抄袭。
至于在音乐曲谱中,就更不存在法定的引用目的了,如果使用和他人相同的部分乐章,对方必然指控你抄袭。还有,学生用的教课书和报纸、期刊,都是汇编作品,著作权法规定教课书的编写可以不经许可使用已发表作品的全部、部分或片断。报纸、期刊可以不经许可地将其它报纸、期刊已发表的作品作为文摘资料刊登。这两种方式同为不经许可就部分地使用他人作品,但不属于引用,因为两种情形均不存在法定的引用目的,所以不能合理使用,它属于法定许可,必须向作者支付报酬。
有人主张,引用应当有字数限制,即相同字数达到多少以上才是抄袭,达不到的则不算;甚至曾经有的部门发文规定,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超过者就属于抄袭等。这些主张和意见,应当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有片面性,目前都没有法律依据。在实际的作品创作中,以字数划线是和著作权法的规定原则相悖的。比如在学术论战中,为了不歪曲对方观点,常需要大篇幅地引用对方的原文,然后逐一予以反驳。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哲学论著就是这样,甚至有引用几千字以上的情况,由于这里存在着法定的引用目的,所以是合理的。然而,一首仅有二十余字的四言诗,只要有一句仅五个字或七个字相同,由于没有法定的引用目的存在,就应认定为抄袭。所以,单就文字作品来说,不能以字数的多少,而要以是否符合法定的目的来确定是属于引用还是抄袭。
引用必须适当何谓适当呢?必须坚持两条原则。
其一,不得影响被引用作品的正常使用。作品的正常使用指的是作品正常的复制、发行。这就要避免引用全文,要把引用限定在必要的程度内。对于引用,一般只能是借用他人作品的某些部分,而不能全文引用,即使符合法定的引用目的,也不得全部照搬。比如,评论或介绍某一部小说选集时,文中如果整篇小说地引用,必然影响被引用作品的正常使用,这里虽然符合引用的目的,但没有引用单篇小说全文的必要。当然,坚持必要的原则也不是机械地“一刀切”。例如,介绍或者评论一首小诗,一则广告,或者一张照片、一幅漫画,全部引用就是必要的。然而,这毕竟是一些特例,而且对作品的正常使用有促进作用,也符合必要的原则。[page]
其二,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把引用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引用一个作品的部分不能比评论、介绍或者说明的部分还长。为什么呢?如果一篇作品的大部分或者说主要部分都是引用另一作者的,自己写的或者说自己的东西只占次要部分或小部分,结果该作品却以引用者的名义发表,岂不有失公正,岂能不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再比如,我们说评论、介绍一首短诗或者一则广告出于必要可以引用全文,但如果评论或介绍部分的文字还没有这首短诗、这则广告的字数多,这能说合理吗?
当然,合理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也不能机械地“一刀切”。比如,综述某一次学术研讨会的研讨情况,肯定是多人发言和观点的综合。在此情况下,引用他人作品的部分肯定会构成这篇综述作品的主要部分,但它却是为说明该次研讨会情况所必须,因而是合理的。由此也可以说,对一个作者作品的引用构成引用者作品的主要部分不可以,而对多个作者作品的引用构成了引用者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则是可以的。
引用和抄袭的分界线
被引用的必须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人还没有发表的作品则不宜引用。虽然,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一经完成不论是否发表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没有发表的作品,由于还没有公之于众,没有与社会建立关系,处于权利人的绝对控制之中,因而社会对其完成情况全无了解,如果进行引用,一旦双方发生纠纷,谁是引用者谁是被引用者很难鉴别清楚。同时,法律无论对被引用作品的保护还是对其著作权的限制,由于涉及诸多法律关系,都是难以实现的。而作品一经发表即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此时对作品的合理使用既容易也有法律的保障,因此,引用只限于已经发表的作品。
引用必须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这是区别引用和抄袭的分界线。引用的实质是借用。既然是借用,就要借得光明磊落,让读者一看便知是借的。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一要把引述的内容放在引号里面,把借用别人的和自己的东西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种对引用部分不加引号、不分清楚明白的做法,实际上有隐瞒、化为己有之嫌。二要通过文中道明或脚注、尾注的方式,指明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甚至连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及引用部分所在页码一并标明更好。
做到这两点,就能如实告知读者哪些是别人的成果,哪些是自己的创作。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原作者作品的尊重,也给读者提供了同类作品的丰富信息,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构成引用的四个必备条件中,指明被引用作品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这一条很关键。因为即使其他三个条件都符合了,唯独没有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也构成抄袭。反过来,只要指明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即使不符合引用目的或者引用不适当,也只是不当引用、过量引用的问题,不至于被指控为抄袭。
那么,是不是引用一律都要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呢?这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有的时候,引用者已征得作者同意不指明,那就无需指明了。这符合著作权约定优先原则。有的时候,由于特殊的使用方式导致指明有困难的,比如在电视节目中发布的广告,一分一秒都是天价,要在广告中指明作者及引文作者确实有困难,可以改换为别的方式。有鉴于此,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这里要注意,此种情况仅限于“无法指明的”,显然能够指明的,就一定要指明。
认定抄袭的法律要件
在著作权法上,抄袭与剽窃是同义语,都是有意无意地将他人作品的部分或全部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从抄袭的这一定义可知,构成抄袭的必备条件或者说法律要件有两个:
第一,是使用他人作品。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经作者许可地偷窃使用,这是最常见的;另一种是作者许可使用,这是少数的。比如在一次职称评定工作中,有人出于相互利用,许可他人将其已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抄写为自己的论文交给单位,助其评上了高级职称。过后两人因别的事发生矛盾后许可者反悔,投诉到版权管理部门,经鉴定后被认定为抄袭。其实,即使在两人发生矛盾之前,这也属于抄袭无疑。因为,已发表作品的作者身份已向社会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可以将该作品的财产权许可或赠送他人使用,但属于著作人身权的署名权是不能许可或赠送他人的,所以,即使是作者许可,这种情况仍然属于抄袭。所以,抄袭并不以是否获得许可为转移,而在于是否确切无疑地使用他人的作品。
第二,以抄袭者的名义公开发表。抄袭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他人作品据为己有,这就决定了抄袭者必然要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不这样,据为己有就无法实现。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一个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包括行为人过错、行为违法性、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损害后果的客观存在等四个要素。在此四要素中,关键在于侵权行为的实施及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抄袭,将他人作品以自己名义的公开发表,既是侵权行为的实施又是客观的损害结果,所以,此要件是构成抄袭的关键。当然,这里的以自己名义发表,是没有指明被使用作品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如果指明了,自己的和别人的都分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而不是抄袭。
抄袭严重损害作者利益
抄袭对作者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他不仅使读者误以为所使用部分是抄袭者自己创作的,从而使抄袭者不当地占有他人著作,同时还使读者对所使用内容的创作者身份发生动摇,误解,从而使原作者在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方面均受到侵害。因此,发生抄袭行为的,抄袭者和出版者都要承担侵权责任。
抄袭可以分为低级抄袭和高级抄袭两种。低级抄袭的认定比较简单:只要在发表的作品中,照搬了他人作品的部分或全部却不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就是抄袭或者说剽窃。高级抄袭则没有全部照搬的情况,一般都是在部分使用的情况下发生,而且常常对抄袭部分要进行一定的改写和加工,注入抄袭者一定量的创造性劳动,但却抄袭、模仿了被使用作品的观点、论据和部分情节、内容。例如,2006年终审宣判的庄羽诉郭敬明侵犯著作权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初的一审判决书中指出:郭敬明在其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中“剽窃了庄羽作品《圈里圈外》中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关系的内容及部分情节和语句,造成《梦》文与《圈》文整体上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此类高级抄袭的鉴别和认定比较复杂,需要专业机构和司法部门完成。[page]
上述引用与抄袭的认定问题,仅是依据现行著作权法律规定的一般阐述。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作品的类型千差万别,无论引用还是抄袭,都有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任何的普遍之中都有特殊,一般之中都有个别,绝不可一概而论。只要我们熟练掌握引用与抄袭的构成要件,善于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对引用与抄袭的鉴别能力,从而促进各类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相关链接
文坛抄袭风波
2007年4月,著名军旅作家石钟山被天津作家龙一起诉到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龙一称,石钟山的小说《地上,地下》的部分内容无论是在戏剧结构、主要背景、人物关系设置还是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均与他的小说《潜伏》存在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抄袭了《潜伏》中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因此要求赔偿其损失共计23万元。
2006年底,网名为“江湖夜雨”的石继航在网上发表名为《安意如多处文字照抄某网煮酒写手江湖夜雨的文章》的帖子,引发巨大波澜。石继航称,当红美女作家安意如的两本书《人生若只如初见》、《思无邪》有50处段落涉嫌抄袭自己的作品。
2006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庄羽诉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其作品《圈里圈外》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判决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春风文艺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停止《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出版、销售行为,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2005年12月22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涉嫌剽窃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叶辛侵犯了中国作协会会员段平的著作权,判决叶辛赔偿段平经济损失9万余元。段平于1998年出版了《急公好义》一书。2004年,他向法院提起诉讼称群众出版社公开出版署名作者为叶辛的《商贾将军》一书抄袭和剽窃了他的作品。
2003年,重庆作家张育仁指控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张育仁表示,余杰的文章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实质部分,如写这篇文章的主要依据——有关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现的“罪状”,除了有关余秋雨写《胡适传》一事引用他人作品外,其他都引用张育仁的文章。
学术剽窃事件
2005年12月,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因文章涉嫌剽窃而主动提出辞职。200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张志安发现,胡兴荣发表在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的文章《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抄袭了自己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初探》一文。张志安发现这篇文章有数处和自己的论文雷同,而且没有标出引文出处。
2005年7月,河南大学宋史专家周宝珠教授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了他的《略论吕惠卿》长达1.1万字的论文,剽窃者只把文章名字改为了《吕惠卿论》。2005年12月,法院做出判决:被告沈履伟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将原告的文章通篇复制,仅将题目作略微改动,即作为自己的文章送交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其行为构成剽窃原告作品,判令被告在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并向原告周宝珠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此外,天津市语言学会发现沈履伟为申请正教授而出版的论文集《求是集》中的13篇学术论文为剽窃所得。
侵权索赔案例
2003年10月,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对18名新浪网旅游论坛网友状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自助游》一书大规模抄袭、剽窃他们在旅坛上发表的文章一案,做出一审判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立即停止出版发行《中国自助游2002》和《中国自助游2003》,在新浪网旅游论坛向原告公开致歉,分别赔偿260元等不等金额。
2001年,季羡林等16位全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及继承人、漓江出版社等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小说精选》剽窃侵权。6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中国物价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2万余元。(知识产权报 王葆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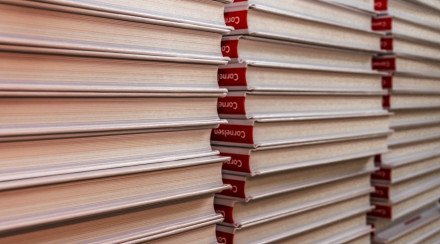
 01:38
人已看
01:38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