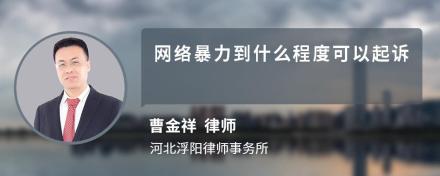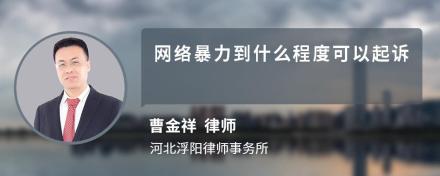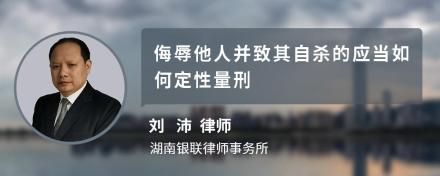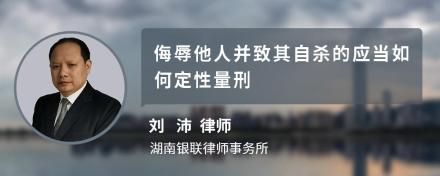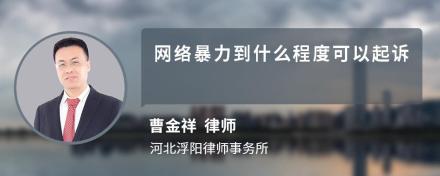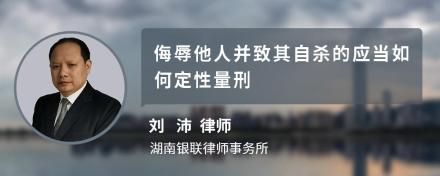□《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记者
编者按 近来,各地接连发生多起记者正常采访遭遇阻挠、记者被殴打围攻等暴力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记者正常采访缘何屡遭阻挠?《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结合热线电话维权情况,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采访,探寻问题根源,寻求解决之道。本报道共分四部分:
现实
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开通9个月以来共接到热线电话800多个,近99%的热线涉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比如,农民土地占用、房屋拆迁、农民工维权、环境污染等,其中很多都存在媒体因为受到种种阻挠而无法进行采访的情况。同时,据热线中心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全国主流媒体发布的有关记者采访遭遇粗暴阻挠的新闻事件不下70起,月均4起。
最近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8月8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大连采访“梅花”台风冲垮的一家化工企业防潮堤坝时,遭到该企业数十人围殴。
8月3日,江西宜春电视台两名记者在采访一处工地塌方事故时,遭到一伙人的围殴。
8月3日,《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3名记者前往一工厂采访火灾情况时,被诱骗入厂后遭到强行控制,采访器材被抢夺。
7月8日,《法制日报》一女记者在浙江省兰溪市马涧镇采访时,当地政府机关人员恶语相向,“谁允许你来采访的?记者算个什么东西?”
7月4日,《广州日报》记者在塘厦欧雷玛电源有限公司采访铅污染一事,该公司多名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强行阻挠,抢夺记者手中材料。
7月4日,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记者在拍摄待整治的曙光硅烷化工有限公司外景时,与厂里人发生冲突,机器被抢走。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6起阻挠记者采访的事件。2003年曾被称为“记者被打年”,引起较大反响的记者被打事件不下数十起。显然,8年后,采访遭遇暴力阻挠的现象依然存在。
软硬兼施 阻挠没商量
暴力阻挠多发 殴打扣押不断
“下午4点半左右,本台记者在维持现场秩序的大连市交警部门的指挥下进入到厂区,却遭到企业内冲出的数十人推搡阻拦,动手抢夺记者的摄像机,并殴打记者。”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8月8日在台风“梅花”过境大连,采访一家名为福佳大化的化工企业时遭遇的惊险一幕。
当日上午,“梅花”过境大连,冲垮了大连金州开发区一家化工企业在建的防潮堤坝,厂区内大量剧毒化工产品有随海水泄漏的危险。为了解剧毒化学品到底有没有泄漏,中央电视台记者到福佳大化采访,结果却出现了上面的一幕,随同记者前往的大连市多个部门负责人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场景在当天中午12点也发生过,当时记者刚打开摄像机,厂内就围上来多人,还没等记者说明来意,他们就推搡记者,并抢夺摄像机、打碎机器。
去年3月24日,《京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采访遭袭》的新闻,报道称该报两名女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路奥体中心西门南侧的一个大院内采访一起火灾时,遭院内数名男子推搡,其中一名文字记者被几名男子拖出事发现场。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央电视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腾讯、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以及各大论坛转载了此报道,中国记协和一些社会学家、法律界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谴责物业安保人员及大院施工方的野蛮行为,呼吁保护记者权利。
警察:“是不是记者?”
记者:“是!”
警察:“抓的就是记者!”
这是2010年记者在伊春采访空难事件时,当地警方与记者的真实对话。《华商晨报》、《法制晚报》、《第一财经周刊》的4名记者分别遭到警察的强制扣留,虽然他们再三声明其记者身份,但还是被扣押了两小时后才获得自由。此前发生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披露国有资产流失内幕,而遭到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的事件,也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暴力阻挠事件时有发生,这种看得见的阻挠让我们直接看到和感受到了从事舆论监督采访的记者们的艰辛,更让我们为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而揪心。
软暴力增多 明里暗里防不胜防
在舆论监督过程中,记者的种种遭遇除了暴力伤害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压力和心理伤害。
《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曾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安徽省一位沈先生反映,安徽某报记者在报道他的果树被砍伐一事后受到很大阻力,后续报道没有做下去,这位记者很无奈,不久也离开了报社。沈先生希望通过热线向这名年轻的记者表达一个心愿:不要因为这次报道耽误了他的前程。
还有一位四川省的张先生反映,《华西都市报》记者因为帮助农民维权,采写报道后受到不明身份的人的威胁,向他表示报道无法再进行了。
据了解,这种暗地阻挠采访的事件正不断增加。有人称这种阻挠为“软暴力阻挠”,其形式如今越来越多样化,比如,跟踪、围堵、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暗地疏通关系、全程陪同、越界质询等。
跟踪、围堵、冒险……这场景听起来好像谍战电影,让人不由得紧张。而这种遭遇在新华社采访河北香河违规“圈地”事件时就发生过。参与采访的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刘敏向《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记者讲述了5月15日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经历。
“这次采访任务是保密的,是一次暗访。新华社驻河北记者站的王炳美,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记者,他亲自驾车,对外自称是司机。我们一开始在采访村民的时候就被盯上了,最初是一个人跟踪,后来增至3辆车跟踪,很难甩掉。我们一停车,他们就敲车门。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压力,甚至危险。在这些跟踪的人当中,有两个人自称是县委的。最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另一位记者去采访知情人,而我和王炳美老师决定冒险进入小刘王村采访村民。天全黑的时候,我们悄悄进入一户农家采访。晚上9点左右,有位村民告诉我们,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和四五辆陌生车辆围堵在村子东西两头,而且人越来越多。我们先后两次拨打当地110请求保护。但令人失望的是,第一次拨打110时,竟被质问为何这么晚要去村里采访,为何不经县里批准,当记者请求保护安全时,对方表示需请示领导,然后便没了消息。最后,40多名村民自发聚集十来辆机动车为我们组成护卫车队,拿着大铁棍子把我们送回了宾馆。所幸的是,当时激动的群众和村头围堵的人群没有发生冲突事件。”[page]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谭芸则向《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记者讲述了另外一种遭遇。
“不久前,我们到湖南浏阳某村子采访重金属污染一事,在采访当地村民的过程中被村干部发现,他们问我们来干什么,说可以带我们去镇上见书记,我们表明了身份,他们没再刻意阻拦,只是跟着我们,有时还帮我们主动联系采访对象,比如,环保局的人、其他村民等。后来到镇上采访,我们要求采访一些部门,他们都帮忙联系,但县里的领导还是请求不要播这个节目,我们没有答应。可从他们接待记者采访时轻松的表情,我们已经感觉到这次采访节目可能要被‘关掉’。果不其然,回来后节目没有播。后来村民发短信说我们是骗子。”
村民的愤怒,真的比身体的受伤更让记者心痛。
“这种暗地阻挠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是节目做完了不让播,有时候是做到一半就让停了,我们为此感到很无奈。”《新闻调查》栏目编导胡劲草对此深有感悟,“为了跟这些人赛跑,我们都抢时间做出节目,尽可能快地播出”。
《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记者,现在他们报社每年发生的记者采访遭遇暴力的恶性事件并不多,也就一两起,但更多的是其他方式的阻挠,有推三阻四拒绝记者采访的,有要贿赂记者的,有所谓全程陪同安排的,有把记者叫去质询的,有无理要求更换跑口记者的,更有托关系阻挠稿件刊发的。
“这种软暴力阻挠现在特别多。有时候去采访,门卫就可以为难你不让进。即便进去了,找到相关人员,人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是推说得一级一级部门请示,来回推。前些日子,我去河南南阳采访一个案子,结果市、区两级检察院相互踢皮球,白白耗费时间,等很久也没结果,只能无功而返。这种现象在公检法部门比较突出。”《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多次碰到过这种情况。
直接的暴力阻挠,我们可以通过报道和法律去应对,维护记者采访权和媒体的尊严。但那些暗地看不见的阻挠之手,让记者和媒体既头疼又无奈。
提要
六问舆论监督报道
问:为何记者被打现象频现?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民众和机构,当然也包括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还不习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新闻记者在开展新闻采访活动特别是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也存在采访经验不足、表达方式不当、沟通态度欠妥等问题,引起了采访对象的反感。此外,一些不良记者滥用新闻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谋取私利,一些社会不法人员假冒新闻记者大搞新闻敲诈,不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更给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造成了巨大冲击,损害了记者的形象和媒体的公信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暴力阻挠只是表象,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工具,自然就处在了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记者采访遭遇阻挠是社会利害冲突的一种反映,是利益冲突激烈的一种折射。
问:在舆论监督过程中,记者自身应注意哪些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唐远清:做舆论监督报道经验越丰富,越容易应付各种突变情况。但现在有些记者刚进报社就被派出去做此类报道,有的甚至还是实习记者,言语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引发矛盾。
夏学銮:记者要保持报道的客观公正,采访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即便跟随投诉人去采访,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绝不能陷入当事人的纠纷之中。
问:如何充分利用能够保护记者权利的法律?
唐远清:有些法规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细化正当采访权和报道权、明确记者采访的底线等,越明确越利于执行。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军:现在涉及保护记者权利的法律法规大约有200多条,但问题是,很多记者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法律法规,不掌握就无法运用法律的武器避免伤害,保护自己的权益。
问:如何提高记者的素养和应对能力,以减少舆论监督中遭受的暴力阻挠?
《京华时报》机动部主任潘澄清:经常对记者进行如何开展舆论监督方面采访的培训,让老记者介绍相关经验,让记者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并告诉他们阻挠到了哪种程度该如何去做,尽量不要发生正面冲突。如果不能直接接近现场,可以采取其他渠道获得信息。一旦发生冲突,要注意保留证据。
《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记者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陷入矛盾双方的纠纷中,要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判断能力。
问: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会提供哪些帮助?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根据职责分工,新闻出版总署一直高度重视新闻记者队伍的建设,在加强记者权益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印发了《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编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新修订了《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顾勇华:近年来,传媒行业发展得很快,这为行业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专业训练、基础知识的教育应该成为必修的入门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受中国记协委托,我们正在完成一项名为《中国职业记者手册》的科研项目,以大众传播法学、媒体伦理学和新闻传播学三大学科的理论为依据,为一线记者提供可以随时查找并运用的职业行为规范。比如,遇到对方拒绝采访了怎么办、遇到人身被扣押了怎么办、隐性采访的处理原则等。
问:如何提高全社会的媒介素养,让舆论监督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郑保卫:要适时开展对权力组织、权力部门及相关公务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其掌握一些媒介知识,学会善待媒体和善用媒体,积极支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这有助于减少阻挠和压制舆论监督报道的现象。[page]
徐迅:要提高媒介素养,还要从学校教育抓起。在发达国家,排名前50的大学不仅开设有媒介法和媒介伦理两门课,而且都作为核心课程来安排。而我国不要说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大学新闻院系在这方面的教育也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