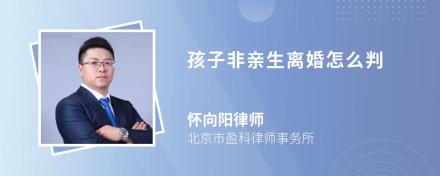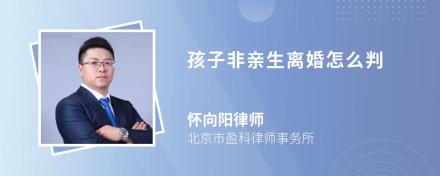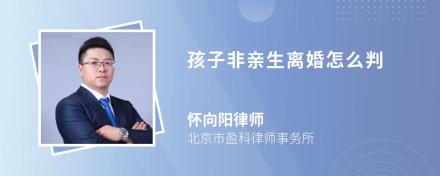(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2001)青民初字第359号
2、案由: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朱华江,男,1983年6月5日出生,汉族,
青州市昭德街道办事处小杨村人,住本村。
委托代理人:李宗习,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文刚,男,195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青州市昭德街道办事处小杨村,系原告之父。
被告:张景斌,男,198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青州市看守所。
委托代理人:王国华,山东九州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冯磊,男,198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青州市王府街道办事处
朝阳村心寺街东巷20号。
被告:冯新华,男,195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州市王府街道办事处朝阳村心寺街东巷21号,系冯磊之父。
被告:张桂美,女,195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冯磊之母。
以上三被告委托代理人:房德业,山东九州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元兴,男,195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青州市烟草公司职工,住青州市王府街道办事处朝阳村八腊庙街20号。
委托代理人:马光诚,山东九州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一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审判机关: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刘敏;审判员:孙勇、杨远珍。
审结时间:2001年7月27日
(二)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2000年2月9日下午2时,原告朱华江到青州市千百惠旱冰场找人时,因琐事与张景斌发生口角。争吵几句后,遂下楼发动摩托车准备离去,但张景斌和冯磊追至楼下,先下楼的冯磊用手击打原告的面部,并将其拽下摩托车后用一整砖猛击头部、肩部,将原告打倒在地。原告刚从地上爬起,又被张景斌抓住头发,用膝盖猛击腹部,随后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刺向原告上背部,致原告T6-T7处胸髓95%断裂,经法医鉴定,原告双下肢瘫痪,肌力为“0”级,大小便失禁,构成一级伤残。原告受到的伤害及遭受的损失,是张景斌、冯磊共同行为造成的,主观上冯磊与张景斌有对原告实施伤害的共同故意,系共同侵权,应共同承担对朱华江的侵权责任。张景斌、冯磊在实施侵权行为对原告朱华江造成伤害时均属未成年人,且现仍由其监护人抚养,既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赔偿能力,根据法律规定,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监护人的冯新华、张桂美、张元兴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赔偿医疗费30064.80元,今后治疗费15000元,护理费36600元,误工费8143.20元,残后护理费12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4元,朱华江父母门市部歇业6个月直接经济损失4500元,营养费2287元,轮椅费8800元,交通费16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6000元,残疾者生活补助费41995元,精神损失费200000元,共计493573.20元。
被告张景斌辩称:本案由原告挑起事端,先后两次用手点划我的头,扬言没人敢惹他。原告的行为激怒了尚未成年的我和冯磊,再加本人患有失控性障碍,系限制责任能力人,为逞一时之勇才打将起来,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三方当事人都有过错,赔偿责任应三方分担。张元兴作为我的监护人已尽到了监护责任,按《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本案纠纷是因本人的犯罪行为引起,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无法律依据,《刑法》第36条规定,因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只能请求经济赔偿。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即是安慰了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失,不需要再承担其精神损失费。原告主张的12万元护理费,在其伤残评定书中并未涉及,我国现行法律对此也无具体规定,故其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36000元,原告父母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对此请求没有依据。伤残补助费的计算应使用1999年的数字标准。综上所述,本案中的过错属于混合过错,三方当事人对伤害事件都存有过错,民事责任应由三方分担,原告主张赔偿49万元要求过高,一些主张无法律依据,有些计算标准过高。
被告冯磊、冯新华、张桂美辩称:对原告及其家庭的不幸深表同情。本案原告的损害后果,是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只有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才应当对这一损害后果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冯磊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没有实施致受害人伤残的行为,要求冯磊对因他人犯罪行为而造成的伤残这一损害后果承担刑事上的或者民事上的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损害后果是由张景斌的行为造成,有充分证据证明冯磊没有实施该行为,因此不能视为共同侵权,不能让冯磊对损害后果共同承担连带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1条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冯磊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对其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人张元兴述称:除同意第一被告张景斌的答辩意见外,另就原告主张的精神赔偿谈以下意见:一、本案尽管是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但由于它是由被告张景斌的同一行为引起的,所以仍然是一种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没有张景斌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诉讼,就没有这起民事诉讼。本案应适用《刑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只进行经济赔偿而不进行精神赔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有明确的解释,该规定第一条所说的赔偿范围,只包括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产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失。另外,被告张景斌初中未能毕业就被第三人送至
潍坊教育学院大专班当旁听生,每年交付3000元,目的就是加强对他的监护,防止他流入社会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第三人作为张景斌的监护人已尽了监护职责,应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就本案发生的原因而言,不能不说原告也有一定的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原告也应承担一部分民事责任。
(三)事实和证据
2000年2月9日下午2时30分,被告张景斌、冯磊等人到青州市千百惠旱冰场滑冰时,与原告朱华江发生口角,争吵过后,朱华江下楼准备骑摩托车离开该处,被告冯磊上前将其拽下摩托车并用砖块击打朱华江头部及肩部各一下,并与张景斌对朱华江进行殴打,张景斌用其随身携带的刀子捅入朱华江后背部致朱华江受重伤。
朱华江伤后入住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治疗,住院66天后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9医院、山东省省立医院治疗。2001年1月15日,本院法医对朱华江伤情鉴定后,认为:1、朱华江背部正中T7水平有明显外伤5.0cm,体征自剑突下感觉丧失,各种神经反射消失,脊髓断裂。认定T7胸髓外伤性断裂;2、T7胸髓断裂致高位截瘫,构成伤残一级;3、因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时有必要的抗感染治疗,约计今后治疗费15000元。
同时查明:朱华江受伤后因治疗创伤,用去医疗费30035.70元、护理费9534.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8元、营养费2287元、交通费1600元、损失误工费7707元。依据法医鉴定应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41995元、残疾用具费8800元、今后治疗费15000元、残后护理费120000万元,合计237157.36元。
原告朱华江受伤前与其父母在青州市青州中路开办兴隆综合门市部,经营土产杂品、五金、油漆等,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事故发生后张景斌的监护人通过公安机关已向朱华江赔偿20000元,冯磊的监护人通过公安机关给付朱华江5000元。
另查明:2000年12月7日,
北京市安定医院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对张景斌责任能力进行鉴定,临床诊断张景斌冲动控制障碍,鉴定为限制责任能力人。2001年1月16日,本院以(2001)青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张景斌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已生效。
(四)一审判案理由
法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法律方式。关于本案是属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院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从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述内涵中不难看出,附带民事诉讼是以解决刑事责任的诉讼为主,以解决民事赔偿的诉讼为辅。张景斌应负的刑事责任现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关于本案系附带民事诉讼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人的生命健康权同时受我国刑法和民法的保护,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同的,二者的功能是并行不悖的,不能相互替代。对被告人进行刑罚处罚适用刑法,追究被告的民事责任适用民法,二种责任的法律基础、归责原则、承受主体、承担方式各不相同。本案是对被害人遭受的不法侵害进行的民事赔偿,理应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民事法律政策。对被告及第三人主张适用《刑法》第36条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本院认为,2000年2月9日下午,原告朱华江与被告张景斌、冯磊在旱冰场因故发生口角后,朱华江下楼已准备骑车离开时,冯磊又上前将其拽下并用砖拍打其头部、肩部,朱华江从地上爬起时,张景斌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其捅伤。就事件发生的过程看,虽系双方的争强好胜引起,但朱华江本人并无与两被告打斗的主观故意,而是想离开、想回避,但两被告追至楼下,先是冯磊将其拽下车,用砖块打击,继而张景斌用刀捅入朱华江背部造成其重伤。被告冯磊、张景斌的主观过错是明显的,对朱华江所受的伤害应负过错责任。根据青州市公安局法医门诊、本院法医所做的鉴定及朱华江在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等证据,原告受伤致残的原因是清楚的,也是唯一的,即被告张景斌用刀捅伤其背部伤及胸髓所致,对此造成的后果张景斌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从朱华江受伤的整个过程分析,冯磊将其从摩托车上拽下并用砖殴打与张景斌用刀伤人的行为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冯磊也应对朱华江的受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张景斌、冯磊实施的是共同侵权行为,应对朱华江所受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两份司法鉴定书的内容和庭审中第三人张元兴所作的陈述,可以证实张景斌患有冲动性精神障碍,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系限制责任能力人。第三人对被监护人精神状态及行为能力状况是熟知的,第三人在履行其监护职责时,理应比一般监护人更注意、更谨慎,没有证据证明张元兴已尽到了完全的监护义务。张景斌现在又无个人财产,对其违法行为给朱华江造成的损害,张元兴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辩解已尽到监护责任,应当减轻民事责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冯磊在其实施侵害行为时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虽已从事临时工工作,但其尚无独立的财产和经济能力承担民事责任,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应由原监护人冯新华、张桂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范围,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的规定,原告朱华江因被告张景斌、冯磊之过错受伤致残,其遭受的损失如前所述监护人应承担民事赔偿,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今后治疗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第三人张元兴及被告冯新华、张桂美应予赔偿。原告主张的残后护理费以每月400元计算25年,共计12万元的请求,考虑本案原告朱华江系高位截瘫,日常生活完全依靠别人扶助的事实,且原告请求的数额未超出有关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伤害事故发生时原告尚未成年,因被告张景斌、冯磊的伤害行为致使其高位截瘫,劳动能力完全丧失,终生依靠他人扶助,严重妨碍了原告的生活与健康,除了肉体上的疼痛外,不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生的遗憾和痛苦,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害后果、责任能力及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等,原告请求20万元的数额偏高,应综合上述因素合理确定,其高出部分不予支持。
(五)定案结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第13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0条及有关民事法律政策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华江损失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残后护理费等共计237157.36元,第三人张元兴赔偿213441.36元,扣除其已支付20000元,其余193441.3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100000元,2002年7月30日前支付93441.36元。
二、被告冯新华、张桂美赔偿原告朱华江上述损失23715元,扣除已支付的5000元,其余187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第三人张元兴赔偿原告朱华江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四、被告冯新华、张桂美、第三人张元兴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朱华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36元,被告冯新华、张桂美承担536元,第三人张元兴承担6000元。
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并已部分履行。
(六)解说
一、本案涉及到附带民事诉讼,该制度的意义,从诉讼法上的意义上讲是为了尽快结束民事关系的紊乱状态,稳定和促进民事流转。因此,现代各国的诉讼制度对于以强调在保证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实体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迅速及时为内容的诉讼经济原则无不给予高度重视。
对一个违法行为可能有不同的法律评价。从刑法的角度看,它是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从民法方面来说,它又构成了民事侵权行为,负有民事责任。实体法上这种同一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并存的情形,使诉讼法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要么分别交由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去解决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责任问题,要么就专设一些特别规定允许在同一程序中一并予以解决。
采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被告人的民事责任问题,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可以利用刑事诉讼程序查明的案情一并处理两个密切相关的诉讼,而不必另行组织审判组织重复进行法庭调查等诉讼活动,这就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对诉讼参与人来说,也可以避免因另外提起民事诉讼而不得不两次以上起诉、应诉、作证、鉴定等以至较长时间耽于讼累的情况,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
可见,同一行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并存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法前提和基础。附带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实体问题则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民事责任问题,其实质是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法依据是民法。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是我国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同样也只是一种侵权赔偿,应当适用民法有关侵权赔偿的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都是独立的法律责任,不能互相代替。
可见,本案原告在刑事诉讼后单独提出民事诉讼并无不妥。
二、关于赔偿责任主体的见解:
(一)一般情况下,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也就是刑事被告人本人。
(二)对被告人的行为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
民事责任并不永远都是由具体实施民事违法行为的自然人承担。有时,由于犯罪行为发生的民事责任可能依法应由实施犯罪行为的刑事被告人以外的人来承担。主要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
(1)刑事被告人是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情况下,他的监护人可能成为民事诉讼被告。
具体分析,监护人作为民事诉讼被告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刑事被告人已满18岁并且精神正常的情况下,不发生监护人充当民事诉讼被告的问题。
第二,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并不是一律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公民担任监护人的,只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只对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无力赔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大致可能有这样几种情况:其一,不满18岁的刑事被告人自己没有财产的,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民事诉讼被告;其二,不满18岁的刑事被告人自己有一定财产但不足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应将监护人和被告人本人一起列为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其三,不满18岁的刑事被告人自己的财产足够赔偿损失的,只能将其本人列为民事诉讼被告;其四,如果刑事被告人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的,根据其财产情况,也分别相应地依上列三种情形处理,如果刑事被告人是于实施犯罪行为后才精神失常的,就只能以刑事被告人本人作为民事诉讼被告。
第三,法定代理人和监护人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明显区别的范畴,不可混为一谈。法律设定监护人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而设定法定代理人的目的则在于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行为和诉讼行为,也就是说,法定代理人不过是法律赋予监护人以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的一种法定身份。当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法律责令监护人承担责任的根据在于其没有尽到管束被监护人的责任,而不是由于其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过错负责,不是在代理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承担民事责任。所以,确切地说,在刑事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民事诉讼被告的只能是其监护人而不能说成是其法定代理人。实践当中,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这两个术语常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判令监护人承担的责任往往被笼统地说成是法定代理人承担了。我们认为需要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诉讼中,监护人实际上是一身兼二任,他既是民事诉讼被告,又是刑事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兼当事人和代理人于一身。只将其列为法定代理人,就意味着他本人不是诉讼当事人,而只是刑事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其职责只是代为诉讼行为,本身和诉讼结局并无利害关系。判决法定代理人为被代理人承担责任在民法上是说不通的。
(三)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其他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人
这是指那些在刑事诉讼中未被起诉的其他同案人。与前一类人参加民事诉讼只是因为依照民法他们应当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不同,这类人参加附带民事诉讼是为了解决其亲自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在多人共同作案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些人可能会因未被起诉而不再成为刑事被告人。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应负的民事责任也同时消灭了。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对同案人决定不起诉的时候,通常也一并对他们的赔偿问题进行处理,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能自觉履行其赔偿义务。
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同案人的赔偿责任问题未作处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尚示彻底解决,人民法院可以将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解决其赔偿责任问题。
虽然由于被不起诉或同案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不再成为刑事诉讼的客体,应该说,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事实就不应再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但是,由于同案人参与刑事被告人实施的犯罪活动,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截然分开。因此,把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同案人亦列为民事诉讼被告,一并彻底解决其赔偿责任问题,符合法律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宗旨。
反之,如果不允许将同案人列为被告,只能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只把刑事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被告,责令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再就是,干脆不处理本案的赔偿问题,将刑事被告人的赔偿责任问题一并交由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前一种办法,不但往往由于被告人无力履行全部赔偿责任而损害被害人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还会导致一个官司两次甚至多次打,从诉讼经济角度来看也是不可取的。
虽然法律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也缺乏研究,但不少地方的司法实践中都本着便民这一指导思想,采取了将同案人作为民事诉讼被告一并彻底解决赔偿问题的做法。
三、关于精神损害与物质抚慰
痛苦,尤其是精神痛苦纯属受害人的主观体验,隋受害人的心理随能力、修养、性格、年龄、健康等的不同而有差异。
从经济学角度说,任何物质享受都有一个饱和点,超过这一点,则非但不是享受,反而是累赘;而精神享受却不但没有饱和点,相反还会越追求越引入而深层次。同理,物质痛苦是一时的、容易医治的;而精神痛苦却是长期的、甚至伴随终身的。“人类所感受之痛苦,纵嗣后不再感到痛苦,但已发生并已感受之痛苦,就痛苦之当时言,将永远烙存。痛苦纵嗣后不再,仅止乎痛苦,自某嗣后之时点起消灭而已,绝无溯及使已发生之感受之痛苦,自始不存在。”(转引自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以改变人所处的外环境为目的,促进生物内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帮助受害人克服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身心的健康。(1)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的功能。因为金钱所具有的购买力,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2)慰抚金在某种情况下具有惩罚功能。因为金钱的支付,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感,以赎其加于被害人的痛苦。(3)人之存在为一个单元,法律的保护应及于同一单元的各种属性,包括非财产上之属性,损害赔偿如仅局限于其中某些属性,则又难有明确的分界。因此,金钱赔偿应及于各种属性的维护,当然包括非财产上之损害。(4)损害是否应予赔偿,固然可以视情形而定,但在现代求偿殷切之意识下,不应逆时代潮流而行。既然肯定应予赔偿,除金钱赔偿外,另无他途。
因此本案判决3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并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