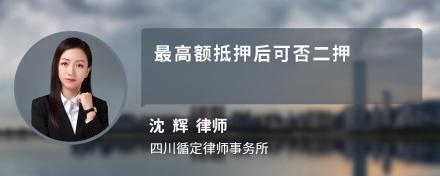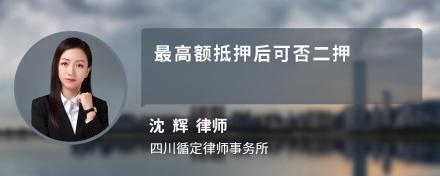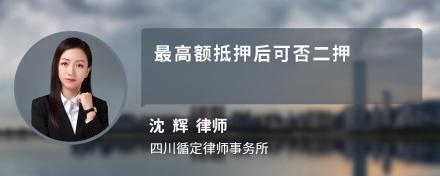最高额抵押是为“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所设定的抵押担保,其担保的对象不是一定期间内实际发生的各“具体之债”而是“债之余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已明确予以确认。基于此,最高额抵押在制度设计上不象普通抵押一样随所担保的具体之债发生、转让、消灭而发生、转让、消灭;对此,在学理探讨中,有人将其诠释为最高额抵押的独立性,有人将其诠释为最高额抵押的相对独立性,也有人将其诠释为抵押担保从属性的特殊表现形式(1)。本文在此无意对有关概念作进一步区分与探讨,而是就最高额抵押因上述在担保从属性方面区别于普通抵押的特点而引致的若干审判实践问题作粗浅的思考。为增强所探讨问题的直观性,本文将结合下述案例展开阐述。
〔案情要点〕
(1)1999年4月22日,原告A银行与被告B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以其所有的C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评估价值593485000元)作为抵押物,担保原、被告在1999年4月22日至2004年4月22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信贷业务;担保最高限额为41544万元;担保范围包括贷款债权总额、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因主合同借款人违约行为导致的费用;在主合同履行期间,如出现以下情况的(具体情况略),原告有权提前收回主合同项下已发放的贷款本息或提前处分抵押物。此后,原、被告依据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了抵押物登记。
(2)1999年5月至2000年11月,原、被告分别签订99FDCL003、99FDCL004、99FDCL009、99FDCL010、99FDCL017、99FDCL020、2000ZF002、2000ZF009等八份《借款合同》,依次约定:原告向被告发放贷款;金额:1亿元、6000万元、3000万元、5000万元、1500万元、1500万元、9000万元、4000万元;期限:自1999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自1999年5月18日至2002年5月18日、自1999年5月26日至2002年5月26日、自1999年5月31日至2002年5月31日、自1999年8月20日至2001年8月20日、自1999年8月25日至2001年8月25日、自2000年6月13日至2001年6月13日、自2000年11月27日至2001年5月27日。
(3)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发放合同项下贷款共4亿元;被告偿还各笔贷款至2001年6月20日止的利息。
(4)2001年6月,原告以被告拖欠2000ZF002、2000ZF009两笔到期贷款本金为由向法院起诉,同时以约定条件成就为由主张解除其他六笔未到期贷款,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贷款本金4亿元及利息、逾期罚息;2、处分约定的抵押物优先偿还上述债务。法院依据八份《借款合同》作相互独立的八个案件立案受理。
(5)上述案件经合并审理,判决如下:一、被告B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A银行借款本金4亿元及利息(利息计算略);二、被告B公司逾期未偿还上述债务,原告A银行有权依法处分C房产并在41544万元范围内从中优先受偿。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上诉期内均无上诉。
上述案例是较为典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案件,对该案件的审理引发了以下几点思考:
一、确认最高额抵押权必须以综合审查实际发生的全部具体之债为前提
实践中,当事人经常依据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某一具体之债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同时请求确认对该具体之债的抵押权;而即使当事人依据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全部具体之债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同时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往往也如上述案例一样--依据不同的具体之债分别立案受理。因此,就单个案件而言,其诉讼请求往往只涉及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部分而非全部具体之债。如上述案例的八个案件,每个案件的诉讼请求均分别是:1、判令被告还款1亿元(或6000万元、3000万元、等等)及利息;2、确认原告就抵押物对上述债权享有抵押权。在此情况下,审判实践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民法院对单个案件的审理是否也相应地仅以当事人所主张的具体之债为限呢?对此,笔者认为不是。
如前所述,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对象是“债之余额”而非某笔或某些特定的具体之债(否则,即使相关之债在担保设立时尚未实际发生,也应认定为普通抵押),因此,认定“债之余额”是确认最高额抵押权的基础。而由于各具体之债均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之内,均是“债之余额”平等的构成要素,均应得到彼此同等的抵押担保,因此,对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权的案件,不论当事人是否主张了全部具体之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均必须综合审查实际发生的全部具体之债,才能正确认定“债之余额”。否则,必将违背最高额抵押之本意,导致可能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后果。
以上述案件为例,该案最高限额为41544万元,实际发生借贷之债八笔,合计欠款本金40000万元,至判决确定日已产生欠息逾2500万元(且该欠息仍继续发生至款项清偿之日)。审理该案件的人民法院综合审查了八笔具体之债,作出“确认原告对40000万元及息(即债之余额)在41544万元范围内享有抵押权”的判决;如此判决,则不论各具体之债此后如何增减,抵押物上所负担的义务均以41544万元为限,完全符合最高额抵押设定的本意。而如果仅以各案当事人所主张的主债为限分别单独审理,由于各具体之债均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之内,则应分别作出“确认原告对1亿元(或6000万元、3000万元、等等)及利息(实为各具体之债)在41544万元范围内享有抵押权”的八个判决;如此判决,不仅实际上已将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对象转变为具体之债,违背最高额抵押的特性;更严重的是基于这八个判决,本案抵押物所负担的责任实际上已远远地超出41544万元(理论上如利息不断发生,每笔具体之债均可累计达到41544万元,则依据判决,抵押物上应负担的责任实际最高可达332352万元),完全违背最高额抵押担保设定之本意,损害抵押人和抵押物上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说,上述案例因“债之余额”本金40000万元小于或等于最高限额41544万元,故仅以当事人所主张的主债为限单独审理所造成的弊端尚有一定的隐蔽性的话,那么,对于“债之余额”本金大于最高限额的情况(假设上述案例再发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使欠款本金达45000万元),则仅以当事人所主张的主债为限单独审理的弊端就更是一目了然了。可见,以当事人所起诉的主债为限分别单独审理并确认抵押权,必将可能使抵押物负担超出最高限额的义务,从而损害抵押人的合法权益。
对此,也许有人会提出:如果法院已先判决确认了某笔具体之债的抵押权,那么只要将该生效判决作为一案件事实,在此后确认相关具体之债抵押权的诉讼中相应作最高限额的扣减,则不存在上述超出最高限额的问题,从而能够在不综合审查全部具体之债的情况下解决上述损害抵押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例如,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法院先判决确认原告对第一笔具体之债10000万元及息在41544万元内享有抵押权,则对后判决的第二笔具体之债6000万元及息,只要确认原告对该笔债权在31544万元内享有抵押权即可;此后再以此类推,最后判决的超过41544万元部分的具体之债(如果有的话),则不享有抵押权。应当指出,如此审理实质上也已超出了单个案件当事人所主张具体之债的界限,部分地--虽然还不是全部--审查了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其他具体之债。但即便如此,该处理实践中仍不可行。对此,我们姑且不论程序上存在等待以前判决生效而裁定中止的问题,也不论因先判决债权的利息在后判决作出时往往不确定而导致上述处理方法实际上无法操作的问题(别忘了利息也属于担保范围内),单就其认定后判决的具体之债超出最高限额部分(为讨论方便,假设上述案例中没有欠息且再发生的一笔5000万元逾期贷款,则该部分为3456万元)不享有抵押权这一点,已违背最高额抵押设定的本意且可能损害债权人之利益。毕竟,各具体之债均属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彼此均应得到同等的抵押担保,仅依据后判决而剥夺其抵押担保,实在于法无据。而在实际执行中,如果对先判决确认受抵押物担保的41544万元债权,债权人以处分抵押物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清偿,那么在抵押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债权人却有3456万元债权仅因后判决而不受抵押物担保,则更是无端的损失。可见,类似处理实际上仍混淆了具体之债与“债之余额”的区别,导致可能不正当地剥夺部分具体之债的抵押担保,从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当事人只主张部分具体之债,而法院主动审查全部具体之债,是否有违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笔者认为不存在这问题。首先,依据法律规定,最高额抵押权实现之前提在于特定主债并决算确定“债之余额”,因此,在当事人主张最高额抵押权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审查实际发生的全部具体之债以正确认定“债之余额”,正是依当事人请求依法查明事实,不存在无“告”的问题;其次,人民法院综合审查全部具体之债,并不等同于必须判决确认全部具体之债,在判决中,人民法院仍以当事人的请求为限依法确认主债权,只是在确认最高额抵押权时以查明的“债之余额”作为实现抵押权的限制条件而已。如上述案例中,假设原告只起诉已到期的两笔债权1.3亿元本金及利息,而没有起诉主张其他六笔未到期借贷之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仍应审查最高额抵押期间所发生的全部八笔债权以确定余额,并判决:1、被告偿还原告1.3亿元及利息;2、原告对上项债权及其余六笔债权的总额在41544万元内对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此判决中,该“其余六笔债权”只是一案件事实(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当事人名称),并无可据以直接执行的强制力,故并不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
以上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人民法院在审理主张最高额抵押权案件中在实体上应综合审查全部具体之债以正确确认“债之余额”,那么,与此相关的程序处理是:对于当事人请求确认同一最高额抵押权而人民法院已按不同具体之债分别立案受理的案件(如上述案例即作八个相互独立案件立案受理),则不论有关案件是否为同一人民法院所受理,均以按照“民诉法”有关规定解决管辖问题并合并审理、裁判为宜。这是因为:1、相关案件均有确认最高额抵押权的诉讼请求,这些诉讼请求实质上依据的是相同当事人之间同一抵押担保关系,此是合并审理的程序基础;2、如前所述,审理主张最高额抵押权案件应综合审查全部具体之债,此是合并审理的实体基础。当然,不合并审理仍然也可审理、裁判,只要综合审查全部具体之债以确定“债之余额”,并参照前述原告只请求部分具体债权的处理下判即可。如上述案例也可分别作如下八个判决:1、被告偿还原告1亿元(6000万元、3000万元、等等)及利息;2、原告对上项债权及其余七笔债权的总额在41544万元内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只是,如此处理,未免烦琐;3、维护裁判的统一与权威,是合并审理的现实考虑。由于确认最高额抵押权以认定“债之余额”为基础,而“债之余额”的认定本身属事实认定之范畴,其涉及单个案件当事人所主张的具体之债以外的其他具体之债,由于举证差异以及不同法官对相同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存在不同“心证”等原因,对同一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特定“债之余额”,不同的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的不同合议庭均完全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对同一事实存在不同认定,从法律诉讼的视角考虑并不奇怪,但现实中必将引起混乱且损害法律的严肃与权威。综上,对此类案件,应依法合并审理为宜。
二、当事人起诉主张最高额抵押权应作为决算的法定事由
确认最高额抵押权的前提是主债特定并决算其“债之余额”。由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是“一定期间连续发生”之债,故约定的“一定期间”届满,即决算期限届至,无疑是决算之事由;推而广之,如当事人约定有决算条件的,则条件之成就,无疑也应是决算之事由。同时,依据《解释》第八十一条之规定,抵押物因财产保全或执行程序被查封以及债务人、抵押人破产则是决算之法定事由。除此之外,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再有其他决算事由之规定。
然而,现实中,由于当事人约定的决算期限较长,而担保期间内发生的具体之债的履行期限相对较短,故往往出现债权人在约定决算期限届至前,起诉请求债务人承担某笔具体之债的违约责任并同时主张最高额抵押权的情况。如上述案例中,最高额抵押期间依约是1999年4月22日至2004年4月22日,即决算期为2004年4月22日,而抵押期间已实际发生的贷款在此前均已到期未偿还,原告在此种情况下起诉主张了最高额抵押权。因该案不存在《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的法定决算事由,故原告确认最高额抵押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将取决于其起诉主张最高额抵押权这一事实能否作为决算之事由:如果可以,则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可依法得到支持;反之,则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只能被驳回,因在未经决算之情况下,主债无法特定,相应“债之余额”也不能确定,最高额抵押权当然不存在确认的基础。
可见,上述问题的认定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是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⑵。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问题的认定在实践中未免有些两难:如果认定可作决算事由,则一经决算,主债必然特定,故从起诉后至2004年4月22日新发生的借贷关系(如果有的话)将不再在本案最高额抵押的担保范围内,这实质上变更了当事人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期间。那么,如此变更的依据何在?是否违背民事关系“意思自治”的原则?甚至是否可能与《解释》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冲突?但如果认定不可作决算事由,则当事人必须等到2004年4月22日之后再决算“债之余额”并主张抵押权,这对当事人是否公平合理?对充分利用抵押物价值是否有利?
对此,有人认为在类似情况下应驳回原告主张抵押权的诉讼请求,即是不将起诉的事实认定为决算之事由(3)。笔者则持相反意见。依据是:1、最高额抵押设立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本在于简化手续、充分利用抵押物之价值,为连续发生的交易作担保。因此,各国法律多明确将“相关连续交易不可能再发生”规定为最高额抵押决算之事由;我国目前法律上虽无此明文规定,但理论界也多认同此观点(4)。而实践中,当事人在存在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仍起诉主张相关债权,往往是因特殊事由已破坏双方合作交易的信任基础,实际上相关交易已经不太有继续发生之空间。在此情况下,机械要求当事人须等待至决算期届至才能决算、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既不利于债权人早日实现债权、回收资金,也不利于抵押人充分利用抵押物之剩余价值,从而大大降低了最高额抵押制度存在之意义。因此,在法官向当事人充分阐明“确认最高额抵押权将意味此后新发生交易不再受担保”的前提下,应将主张最高额抵押权的起诉事实视为“连续交易不可能再发生”的情况之一,认定为决算事由,从而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2、将当事人起诉主张最高额抵押权作为决算之事由,并不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反而更是尊重“意思自治”原则之体现。这与最高额抵押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最高额抵押并不从属于具体之债,其担保的是“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因此,有人认为最高额抵押所从属的是这些“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所据以发生的基础关系(5)。此观点应当说是较客观的。然而,应当指出,由于该基础关系在“一定期间”内何时发生、发生多少交易上并不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约定,故该基础关系本身并不是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无任何约束力,当事人依据该基础关系在抵押期间内可以发生交易,也可以不发生交易,对此法律完全无法干涉。而作为与决算密切相关的“一定期间”,其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当事人对发生连续交易期间的预期,故如当事人因特殊原因改变其商业决定,不愿意继续进行交易并在“一定期间”内起诉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权,因法律并无法依据基础关系强制当事人在剩余之“一定期间”里继续发生交易,故再机械地坚持“一定期间”,未免教条,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好处,更不利于物之充分利用。因此,允许以起诉主张最高额抵押权的事实作为决算事由从而实质变更“一定期间”,其实是更加体现“意思自治”之原则,只不过基于债权、债务双方的意思均应对等,故不仅应允许债权人起诉请求决算,也应允许主债务人起诉请求决算。
当然,以上观点毕竟只是学理上的理解,在立法对此问题予以明确之前,人民法院的任何相关处理均可能引起争议。目前其他国家已有将“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权”规定为决算之法定事由的立法,这值得我国借鉴。最起码,立法应明确以“所担保的连续债权不可能再发生”作为决算之法定事由,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留下依法自主裁量空间。
三、最高额抵押主合同债权的转让问题
《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移”,该法律规定之本意在于维护最高额抵押关系之完整性。但现实中,尤其在金融信贷领域,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我国四大商业银行大量将其债权转让给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中,不乏涉及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情况。因此,应如何理解、适用《担保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对涉及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1、对于主债权已特定并决算的,依据《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应视为普通抵押权,而普通抵押权并不存在禁止主债权转移之问题,故此种情况显然不应适用《担保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而应适用《担保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认定主合同债权部分或全部转移的,抵押权随之部分或全部转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对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原债权银行转让主债权,可以认定转让债权的行为有效”,肯定了这一观点。2、对于主债权虽未特定,但整个基础关系发生转移的(如当事人发生合并、分立;或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将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也不应适用《担保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这是因为:该法律规定立法之本意在于确保最高额抵押关系之完整性,而作为基础关系的整体转移,并不妨碍抵押关系之完整性,与立法之本意并无妨碍;同时,从《担保法》的条文表述分析,所谓“主合同债权”,在整部法律中显然是指担保期间实际发生的具体之债,并不包括具体之债据以发生的基础关系;综上,应认为此种情况并不受该条款限制。3、对于主债权尚未特定且当事人协议转移在担保期间已实际发生的部分或全部具体之债的,无疑应适用《担保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然而,应如何理解该法律条款之规定,是否应据其认定相关债权转移无效?对此,理论界普遍认为不应当限制具体之债的转移,因为这实质上违背了民事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当事人自主处分其权利的原则(6),但有人同时也指出,司法解释已将《担保法》第六十一条限制解释为只适用“决算前的债权转让”,则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只能作出“决算前转让主合同债权的,转让无效”的结论(7)。笔者认为,维护最高额抵押关系的完整性不能以牺牲民事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当事人自主处分其权利的基本原则为代价,而基于最高额抵押在从属性上的特点,以上两个目标实际上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由于最高额抵押并不从属于具体之债,抵押权不随具体之债转移而转移,故完全可认定决算前转移具体之债的,转移有效,但不受《担保法》第五十一条之限制,即相关的具体之债不再受最高额抵押担保,同时在此后最高额抵押权决算中也相应排除该具体之债。据此,对《担保法》第六十一条,仍可进一步限制解释为“决算前转移的主合同债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8)。但在此问题上,应当予以区别的情况是:如果在具体之债转移后,当事人明确达成协议以同一抵押物担保该具体之债并依法进行登记的,应认为是新达成的普通抵押权,并依法予以确认。此与“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移”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
以上是最高额抵押因在从属性方面不同于普通抵押的特点所引起的若干实践问题。由于我国在最高额抵押方面的实践积累相对较少,法律规定相对简单且缺乏严谨、完善的制度设计;而最高额抵押除从属性方面外,还有其他不同于一般抵押的特点,即使是因从属性方面的特点,所引发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本文所提及的;因此,本文在此作粗浅之探讨,希望在相关问题上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以促使作为“担保之王”的抵押制度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种形式能更加完善。
注:
(1)参见《论最高额抵押》,房绍坤、吴兆祥、郝倩著,原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转载中国民商法网。
(2)本文所引案例在判决中通过解释合同,将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推定为提前决算条件,从而以约定条件成就判处提前决算,实际上回避了这一问题;然而,大多数类似案件恐怕并不容易回避--笔者按。
(3)《中国担保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第265-266页,曹士兵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4)同(3),第266-268页;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96-298页,李国光、奚晓明、金剑峰、曹士兵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转引自《最高限额抵押权之意义与特性》,谢在全(
台湾)著,载中国民商法网。
(6)同(3),第271-272页;又《担保法例解与适用》,第421-422页,孔祥俊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7)同(3),第272页。
(8)类似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同一部法律的解释中,已有先例:《解释》第五十一条即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以同样的思路对《担保法》第三十五条作出限制解释的--笔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