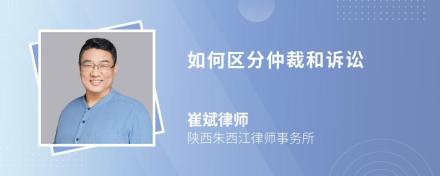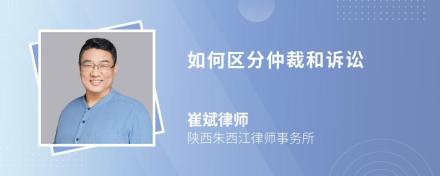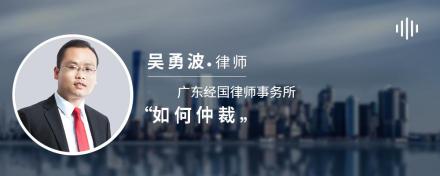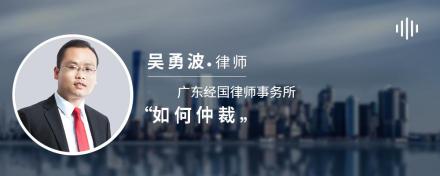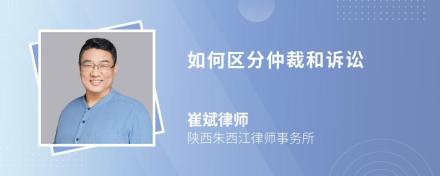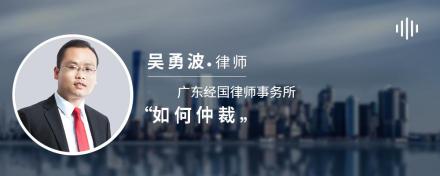[译者注:禁诉令是英国为保护协议管辖(包括诉讼管辖和仲裁管辖)而实施的一项专门法律制度。该制度对我国的海事诉讼也开始产生影响。最近,我国的海事法院已经遇到一起英国法院向我国案件当事人签发禁诉令的案件。 随着我国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增多和影响的扩大,肯定还会遇到更多的此类案件。为应对这种情况,我国应对该制度的基本内容、实施情况以及其他国家对此的态度等有所了解。为此译者翻译了英国法官皮特﹒格劳斯(Sir Peter Gross)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本文主要介绍了英国禁诉令制度的起源、英国司法界的观点、外国法院(主要是欧盟法院)的态度,作者同时也阐述了本人的观点。]
作为对付当事一方违反仲裁义务或以此相威胁的一种武器——禁诉令(the anti-suit injunction),它是由普通法发展起来的,而且一直发展顺利,对此,(英国人)没有什么歉疚的。在布鲁塞尔公约及其修订的第44/2001号欧盟规则(以下简称欧盟规则)的框架内,有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英国的)禁诉令制度与欧盟“信赖他国法律制度”的理念是否相符?该制度是否属于欧盟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欧盟规则不适用于仲裁,就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用禁诉令限制违反仲裁协议的行为,毫不影响该规则。即使禁诉令限制的对象为欧盟成员国的当事人,而且是在欧盟成员国提起的外国诉讼(foreign proceedings),也是如此。英国有权保护伦敦仲裁。假若通过禁诉令强制一方当事人履行仲裁协议的做法不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救济措施。可以这样说,仅仅要求人们遵守诚信,并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当普通法与大陆法因制定公约而发生融合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法律难题。本文讨论的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难题之一。
引言
不管是司法界还是在学术界,对禁诉令问题已经争议许多年了。之所以专门谈这个问题,是由于欧盟法院(ECJ) 最近审理了两个案件,即Turner v. Grovit(2004)案 和Grasser v. MISAT(2004)案 。对这两个案件,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有关签发禁诉令限制一方当事人违反英国仲裁的条款在外国提起诉讼的问题。禁诉令常常令人难堪,它强制一方当事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允许一方当事人违反管辖条款。对禁诉令的这些内容,本文不作深入地探讨。本文将从历史分析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并对欧盟法院的上述两个判例进行研究,以便利用禁诉令来保护英国的仲裁管辖权。
简而言之,禁诉令就是限制(restrain)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提起诉讼或寻求在外国诉讼的命令。这种禁令可以在诉讼结束时做出,也可以在诉讼中做出。一般说来,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除非有重大问题需要审理,而且还要便利解决纠纷(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否则,在诉讼中不能签发禁诉令。现在,不管是诉讼中签发的禁诉令(interim),还是诉讼结束时签发的禁诉令(final),都要求慎重。还要注意,禁诉令既是一种临时性(the provisional nature)的措施,但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finality)的措施。
禁诉令的历史背景及英国法的分析
英国法院签发禁诉令的法律依据是《1981年最高法院法》(the Supreme Court of Act 1981)第37条。该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法院认为公正而且做起来方便,高等法院得以命令…..的形式,签发禁令…..”。但是,这种泛泛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一系列判例的制约。 在英国,禁诉令已具有很长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的19世纪,甚至还要早。 它起源于英国过去的大法官法院(the English Court of Chancery)签发的禁令。 当时该法院签发这种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限制(一方当事人)向英国的普通法院提起诉讼。由此确立了衡平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后来这种禁令又用于限制(英国当事人)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其他法院进行诉讼。Scrutton大法官在审理Ellerman Lines Ltd 诉 Read(1928)一案 中,对签发禁诉令的理由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英国法院…..当然不能签发禁令限制外国法院的诉讼,它们也无权那样做。但是,英国法院可以通过签发禁令限制欺诈违约的英国公民,因为他们是在英国法院诉讼的当事方之一,正是他们通过向外国法院诉讼可以获得欺诈违约的好处。……因此,英国法院显然有权禁止(restrain) 受英国法院管辖的人以违约和欺诈的方式向外国法院提起诉讼。”Hobhouse大法官在审理Turner v. Grovit(2001)一案 时提出的观点,一般认为是英国这方面的权威观点。(他认为:)禁诉令并不是基于“向国外扩张审判权….”,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法院对受限的一方当事人具有对人的管辖权(the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Hobhouse大法官批判了有关禁诉令的几种错误观念,尤其是把这种禁令称之为“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s)。他觉得这个术语容易使人误解。他认为,“这个术语使人误解,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这种禁令是发给其他法院并约束该法院的。使人觉得外国法院是签发的对象,令人感到它是一种要求外国法院停止行使本国管辖权的命令。这两种理解都是错误的。当英国法院发布一项禁令时,其命令的对象只是英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并不指向任何外国法院。……该命令仅仅约束对人诉讼的当事人,而且仅仅在该方当事人有义务接受英国管辖时才有效,这样可以对其强制执行。”
Hobhouse大法官还强调,签发禁诉令的权力是以一方当事人存在可以被限制的过错行为为基础,而且申请人对该行为有权起诉并具有预防受损的合法利益(例如,根据伦敦仲裁条款,不在外国法院受诉的合同权利)。英国法曾高度重视国际礼让,在签发禁诉令时也是如此,并且深知这种禁诉令可能会干涉外国法院的诉讼,尽管这种干涉是间接的。但是,Hobhouse大法官认为,如果认为是否签发禁诉令依赖于外国法院拒绝管辖或抢先管辖,则大错特错。禁诉令并不涉及外国法院管辖问题,而是对一方当事人寻求外国法院管辖的行为的评价问题。
用禁诉令限制违反仲裁协议
自禁诉令出现后,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关于限制违反仲裁协议的禁诉令判例。最重要的判例是The Angelic Grace(1995)一案 。该案的事实非常典型。纠纷发生在船东和租船人之间。船东在英国法院提起诉讼,并且认为,有关事故引起的本诉和反诉在伦敦仲裁是恰当、公平的。因此,要求英国法院阻止租船人(就该次事故引起的)任何索赔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其进行仲裁。此后,船东提起了仲裁。英国法院的诉讼文书送达给意大利的租船人后,租船人在意大利法院提起了诉讼。租船人为了确定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也接受了英国法院的管辖,其要求英国法院裁决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本诉和反诉都要仲裁?英国法院认为,所有的本诉和反诉都应适用仲裁条款。该裁决生效后,意大利的租船人明确表示将在意大利法院继续进行诉讼。这种诉讼行为是违反合同的,而且该租船人对这种行为的正当性从未作过说明。在这种情况下,Rix法官签发了禁诉令。此后,Pregerim Simon律师向法院提交了拒绝接受意见书(rejection a memorable submission )。该意见书认为,法院应当“严格限制”这种行为。上诉法院维持了Rix法官的裁决。
按Leggatt大法官的话说,就是租船人赤裸裸地想再找一次胜诉的机会,其国内法院有可能不理智地判他们胜诉。这个案件需要尽快签发禁诉令。Leggat大法官指出,“与Bumble先生的观点相反,法律通常并不愚蠢 ,国际礼让并不要求一成不变(comity does not require it to behave like one)” ;按照Rix法官的观点,租船人继续在意大利诉讼是无理缠讼。他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其利用自由裁量权签发禁诉令的做法无可指责。
但事情尚未就此结束。在审理该案中,Millett大法官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而且他的观点得到了Neill大法官的支持。因此,Millett大法官的观点成为(上诉法院)判决这起案件的主流观点。他认为:“……(过去人们认为)管辖权只能有节制地、谨慎地行使。现在是废止这种陈腐观念的时候了。有许多的权威提出过警告,注意避免明显地不当干涉外国法院的诉讼;(当一方当事人)不是以违约为由,而是以不方便诉讼或以缠讼胁迫为由寻求禁令时,(英国法院)应当更多关注外国法院的感受。这种观点也曾受到广泛的赞扬。但是,我认为,签发禁令限制(被告)在外国法院起诉时,(法院)没有理由胆怯。道理很简单——被告已经承诺过不提起这种诉讼。”
作为当时船东的诉讼代理人,在评价The Angelic Grace一案时,尽管有义务披露与该案的利害关系,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根据该案的事实签发禁诉令的行为,值得赞扬。因为其他的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首先,意大利法院当时面临着船东也向意大利法院起诉的风险。如果意大利法院拒绝管辖,当事人再进行其他诉讼将既费时又费财;如果意大利法院进行管辖,该法院在判决时也有风险——该判决有可能与仲裁裁决发生冲突。此外,如果意大利法院的判决在英国得不到承认和执行,势必还要重复诉讼。这不仅增加了不便,而且还会增加诉讼费用;如果意大利法院的判决在英国得到了承认和执行而且英国法院没有签发禁诉令,那么,对租船人的违约行为(即违反仲裁协议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的救济措施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对布鲁塞尔公约缔约国的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进行诉讼的行为是否可以签发禁诉令这个问题,法院在审理The Angelic Grace案件中做出的判决是否正确,现尚未构成定论。英国司法界也有两种观点,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将该公约或欧盟规则解决管辖冲突的模式与普通法的解决模式做一比较。
欧盟规则处理模式与普通法处理模式的比较
对这种比较的性质,Goff of Chieveley 大法官在审理Airbus Industrie GIE v. Patel(1999)一案 中曾作过阐释。他指出,由于“独特的法律历史和某些文化的差异”产生了两种处理模式。欧洲大陆法国家的处理模式(尤其是布鲁塞尔公约早期的处理模式)是避免在欧共体成员国之间产生(管辖权)冲突。因此,它对管辖权的分配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从布鲁塞尔公约和欧盟规则可以看出这一点。Goff大法官指出:“这种制度也可以达到其目的,但却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僵死、呆板。僵死和呆板将导致不公,……处理的结果往往也不会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该公约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在欧共体成员国之间不产生管辖上的冲突。”
与此相反,在普通法中,按Goff大法官的话说就是有一个“管辖丛”(a jungle of jurisdictions) ,为了保证客观公正而又避免管辖权过多,普通法有两件武器:一个是以不方便管辖为由的诉讼中止令(ordinance of a stay),另一个是禁诉令(the anti-suit injunction)。 这两种武器各有所用。中止诉讼由有关的国家自愿采用,而禁诉令则基于对国际礼让原则的尊重。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有必要简述一下“国际礼让原则”(comity)的适用范围和作用。对这两个问题,Dicey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他的《冲突法》(Conflict of Laws)一书第一版(1896年版) 中,他指出,国际礼让原则是“一个因语言含混造成的思想混乱的怪物”。英国法院之所以适用法国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公正,并不是为了讨好法兰西共和国;英国法院适用法国法,也不是为了鼓励法国法院在有关的案件中也适用英国法。但是,正如Dicey和Morris先生合著的《冲突法》最新版本(2000年版) 所解释的那样,国际礼让的概念并不用于解释冲突法制度,而是“作为适用冲突法或重塑冲突法的一种工具”。
目前,在依自由裁量权签发禁诉令限制在外国法院诉讼时,英国法院常常用国际礼让原则来说明其持慎重态度的正当性。然而,向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缔约国的当事人签发禁诉令时,英国法院不可能不知道或不可能意识不到会冒犯该缔约国。
英国的两种不同观点
尽管Millett大法官在审理The Angelic Grace(1995)一案中已表明了观点,但英国法院对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的缔约国居民签发禁诉令时,仍然持慎重的态度,即使涉及伦敦仲裁时也是如此。有两个著名的判例可以表明这一点。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一种慎重的趋势”(a cautious tendency)。
Phillip Alexander Futures & Securities Ltd. 诉 Bamberger(1996)一案 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判例。该案对签发禁诉令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布鲁塞尔公约的缔约国提起诉讼持保留态度。这个案件是由Leggett大法官做出的判决。在他代表上诉法院的判决中指出:“英国法院签发禁诉令限制向另一国法院起诉的做法,根据本案的事实,值得重新检讨。便利诉讼论者认为,禁令只适用于对人诉讼,而且英国法院签发禁令不干涉且永远不会干涉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当被告居住在英国或者在英国有财产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该禁令可以得到执行,防止当事人违约向外国法院起诉。但是,当被告不居住在英国而且在英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时,除非外国法院承认并执行该禁令,否则,该禁令不可能得到执行。如果外国法院拒绝承认或执行该禁令,本法院(即英国法院)势必也拒绝承认该外国法院做出的裁决。在本案中,德国法院认为(英国的)禁令侵犯了其主权,并拒绝在德国送达该禁令。此外,他们还对该案的实体问题作出了裁决……”。
另一个判例是Toepfer 诉 Cargill(1998)一案 。该案的案情是这样的:(禁诉令的)申请人将一批大豆销售给(禁诉令的)被申请人,销售合同采用了GAFTA格式合同的许多条款,其中包括伦敦仲裁条款。由于货物出现问题引起了双方的纠纷。被申请人在法国法院提起了诉讼。申请人引用GAFTA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认为被申请人在法国法院起诉的行为违反了仲裁条款。于是,申请人在英国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英国法院宣布被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仲裁协议,并向该法院申请签发禁诉令,限制被申请人在法国法院继续诉讼或限制被申请人在法国诉讼中采取进一步措施。同时,还要求被申请人停止在法国法院的诉讼。被申请人则认为,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英国法院不应支持其请求。被申请人还认为,英国法院的诉因与法国法院的诉因完全相同,而且法国法院首先受理了此案。申请人则抗辩称,根据(布鲁塞尔公约规定的)“仲裁例外”,英国法院的诉讼不适用布鲁塞尔公约,因此,不能适用该公约的第二十一条规定。
该案一审由Colman法官审理,申请人胜诉。在上诉审中,由Phillips大法官审理。在判决中,Phillips大法官指出:“若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提起诉讼时,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的纽约公约第二条第三款(art. II.3)要求缔约国法院指示当事人去仲裁。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根据国际礼让原则和为了简便诉讼程序,如果有人不顾仲裁协议在另一缔约国提起不当诉讼,该被告可以申请有关国家的法院中止诉讼。但是,英国仲裁条款的当事人似乎并不相信外国法院会根据该公约中止诉讼,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寻求英国法院的禁诉令。本案就是这种情况。……” Phillips大法官还提到了The Angelic Grace(1995)一案,并引述了本文前面提到的Millett大法官所述的那段话。对那段话,Phillips大法官说,“尽管我们并不希望有人认为我们是在感情用事,……”。这表明他对那种观点(的正确性)并不那么信心十足。但根据他的判决,该法院应当认为,Colman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签发禁诉令并没有错误。该法院还认为,先诉法院(the court first seised)的被告未对先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就向第二个法院提起诉讼,以此对抗先诉法院的管辖权,这似乎与布鲁塞尔公约根本制度不符(fundamental conflict)。该法院向欧盟法院提出了下列问题,要求其给与裁决:
“1、布鲁塞尔公约第1条第4款(art. 1.4)规定的例外是否适用于向英国法院提起的下列诉讼?(1)申请宣告(一方当事人)在法国法院进行诉讼已构成违反仲裁协议;(2)以违反仲裁协议为由,申请签发禁令限制上诉人继续在法国诉讼。2、英国的这种诉讼与法国基于相同仲裁协议进行的诉讼是否构成相同的诉因,是否构成对法国管辖权的挑战,因而可以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要求英国法院中止诉讼?”
由于诉讼费用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双方当事人没有等到欧盟法院作出裁决便和解解决了纠纷。Toepfer诉Cargill(1998)一案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原因有两个:第一,该案争议的问题很明显;第二,在签发禁令时,法院的附随理由(the court’s dicta)标明更倾向于审慎签发禁诉令。
审慎并不表明英国法院对违反仲裁协议的行为不再签发禁诉令,仅仅表明法院对签发禁诉令的要求更高了。关于禁诉令,特别是希望在布鲁塞尔公约框架内确立禁诉令制度问题,已成为学术界一再争论的问题。
欧盟法院的最新判例
对有关禁诉令制度的希望与恐惧,已充分体现在欧盟法院的两个最新判例中。
一个是Gasser诉MISAT(2004)一案 。这是一起因买卖合同引起纠纷的案件。买方在(意大利)罗马法院提起诉讼,此后,买方则在奥地利法院提起诉讼。卖方认为,买卖合同中含有奥地利法院专属管辖条款,(在奥地利法院起诉)符合布鲁塞尔公约第17条的规定。卖方则对奥地利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奥地利法院向欧盟法院提出了几个问题,要求给与裁决。其中有些问题是这样的:
“2、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17条的协议管辖规定,如果后诉法院(the second court)享有专属管辖权,除该公约第21条规定的先诉法院可以审查其管辖权外,其他法院是否也可以对先诉法院的管辖权进行审查?或者说,即使有管辖协议,协议管辖的法院也必须要遵守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的规定?3、如果在某缔约国法院诉讼花费的时间过长(并不是当事双方的原因引起的),除了第21条规定的先诉法院外,根据该条的规定,是否允许在其他法院进行诉讼?”
欧盟法院对公约的解释具有判例的性质。该法院认为,第21条的效力优于第17条的效力。英国法院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商业实践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欧盟法院未接受这种观点。该法院认为:1、后诉法院的管辖权是由该公约第17条规定赋予的,在先诉法院就管辖问题确定之前,(后诉法院)必须中止诉讼,而且,如果先诉法院认定其具有管辖权,后诉法院应当拒绝管辖,以便先诉法院管辖;2、为慎重起见,如果甲法院是先诉法院,乙法院是协议管辖的法院,那么,应当由甲法院对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做出有利于乙法院的裁决。具体说,如果意大利法院是先诉法院,应由意大利法院对(合同中的)英国法院管辖条款的效力做出裁决;3、欧盟法院的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这样分配管辖权(对认定管辖)比较明确(certainty);第二,可以避免双重诉讼(parallel proceedings);第三,后诉法院在认定管辖权的问题上,“永远不会”比先诉法院更优先的地位;第四,英国法院提出的可能产生“拖延战术风险”的理由,欧盟法院似乎并未认可。此外,欧盟法院还认为,不管先诉法院的诉讼是否过分拖延,第21条永远优先适用,即使先诉法院的诉讼时间过长,也不允许违反第21条的规定;该公约的基础是,对各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缔约国之间应当相互信任。
这个判决的影响是深远的。若与英国上诉法院早先审理的Continental Bank诉Aeakos Compania Naviera(1994)一案 时提出的观点相比,这种影响则更加显而易见。在那个案件中,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尽管希腊法院是先诉法院,但是,由于合同中具有专属管辖权条款,英国法院具有管辖权。英国法院因此签发了禁诉令,限制希腊当事人在希腊法院提起诉讼。Steyn大法官以强硬的措辞,驳斥了(希腊当事人提出的)第21条优先于第17条适用的观点。他认为,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一方当事人可能会不顾专属管辖协议到另一个缔约国法院提起诉讼,而双方当事人选定的法院不得不拒绝管辖或中止诉讼。他还认为, “那样的话,违反合同的一方可能会把专属管辖权协议视同儿戏,而这种管辖协议是当事双方协商的结果……”, “ Kloeckner & Co. AG诉Gatoil Overseas Inc.(1990)一案 的判决也是这样的结论。在这个案件中,Hirst法官还提出了一个政策性因素,即在布鲁塞尔公约的框架内,决定专属管辖权效力的最佳法院是双方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选定的法院。” 除此之外,Steyn大法官还引用了Saville法官在审理Filiatra Legacy(1994)一案 中提出的观点。在该案中,Saville 法官把与此相反的观点表述为“荒谬可笑”(ludicrous)。Steyn大法官最后指出, “更重要的是,英国法院签发禁诉令以保证履行专属管辖协议,并不违反布鲁塞尔公约的任何规定。”
对英国的律师来说,英国上诉法院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且商业实践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英国的律师也乐于接受相反的意见,很容易理解,欧盟法院审理的Gasser(2004)一案 的判决效力要高于(英国法院审理的)Continental Bank诉Aeakos Compania Naviera(1994)一案的效力。至少在协议管辖方面,英国要受到Gasser(2004)这一判例的约束。但问题还不止于此。
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下欧盟法院审理的Turner 诉Grovit(2004)一案 。该案的事实可以作简要的概述。Turner先生以不公正和错误的解雇为由,将Grovit先生和其他人告到了英国的雇佣法庭。被告提出管辖异议,被法庭驳回。被告认为,他与Turner先生终止雇佣关系时,其雇佣的地点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英国,因此,英国法庭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于是,被告向雇佣法庭的上诉法庭(即英国的The Employment Appeal Tribunal)提出上诉。后来也败诉。该管辖权问题解决之后,尽管仍可以再上诉,但是,雇佣法庭还是根据Turner先生的实体请求,做出了裁决,裁决由被告给予损害赔偿。于是,被告在西班牙法院又提起了诉讼,认为Turner先生没有适当履行其职责。被告在西班牙法院的诉讼请求数额超过了Turner先生在英国法院提出的索赔额。Turner先生拒绝接受西班牙法院的诉讼文书,且对西班牙马德里法院的管辖权提出抗议,并拒不参加诉讼。Turner先生以被告滥用诉讼程序在西班牙提起诉讼为由,申请(英国)法院对该被告签发禁诉令。法院根据其单方的申请,签发了禁诉令,但不久法官撤销了该禁令。于是Turner先生向英国上诉法院上诉,并获得了上诉法院的支持。上诉法院的理由是,被告在西班牙的诉讼已构成滥用诉讼程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即英国法院是先诉法院,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的规定,它对被告在西班牙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排它的管辖权。于是被告上诉到英国的上议院。英国上议院的判决由Hobhouse大法官做出。该判决清楚的表明,假如需要判决的问题只有一个,上诉法院的判决应当维持。 但是,上议院决定将下面的问题提交欧盟法院裁决:
“若被告为了挫败或阻止在英国提起的正当诉讼,而以恶意向另一个缔约国法院提起诉讼或以提起该诉讼相威胁时,英国法院向该被告签发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s)是否违反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
由于受“Ruiz Jarabo Colomber总顾问的意见”(the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Ruiz Jarabo Colomber) 影响,欧盟法院的答复称,该公约不允许签发这样的禁令,由某缔约国法院禁止其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向其他缔约国法院提起诉讼或禁止其继续进行该诉讼。即使该当事人为了挫败对方的诉讼而进行恶诉,也是如此。从下面引述的关键段落,可以看出欧盟法院的理由:
“24、……该公约应当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各缔约国应当尊重其他缔约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正是这种互信才确立了强制管辖制度……;25、在该公约的适用范围内,该公约确立的管辖原则对所有缔约国都适用。解释和适用该管辖原则,对每个缔约国的法院都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是互信原则的必然要求。……26、同样,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该公约不允许一个缔约国法院审查另一个缔约国法院的管辖权,……27、但是,一个法院以惩罚作后盾,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另一个缔约国法院提起诉讼或限制其继续诉讼的行为,危害了其他缔约国法院解决争议的管辖权。禁止索赔人提起此种诉讼的任何禁令,都应当视为干涉了外国法院的管辖权,不符合该公约的规定;28、尽管向本院(欧盟法院)提出该问题的法院(即英国法院)已经做出了解释,认为,这种干涉是间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告在国外滥用诉讼程序,法院所做出的判决也仅仅是对被告在外国起诉的正当性进行评价,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这种干涉的正当性。法院的这种评价,违反了互信原则和禁止一国法院审查其他缔约国法院管辖权的原则。互信是该公约存在的基础;29、即使禁令仅仅为保护其诉讼程序的完整性而采取的一种程序性措施,且其本身属于内国法,但也需要注意:即使是适用国内程序法的规定,也不允许损害布鲁塞尔公约的效力;30、有人认为,签发禁诉令有助于实现该公约的目的,即减少相互矛盾的判决、避免重复诉讼。这种理由也不能成立。第一,在解决某些未决案件(lis alibi pendens)时,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使该公约确立的某些制度丧失作用;第二,容易引起某些冲突,而对这些冲突,该公约并没有相应的解决机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使缔约国签发了禁诉令,另一个缔约国法院还会做出裁决。同样,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即两个缔约国法院都签发了禁诉令,这两个禁诉令之间也可能相互冲突。”
对(英国)上议院提出的理由,(欧盟法院)完全不予接受,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至于谁对谁错,暂且不论。总的来说,根据布鲁塞尔公约处理(管辖纠纷)案件,欧盟法院看来是反对实施禁诉令。审理因恶诉或违反管辖条款而引起的诉讼,有关管辖问题应当由受理诉讼的法院去解决。就Turner 诉Grovit一案而言,西班牙法院进行的诉讼到底是否构成滥用诉讼程序?英国法院虽已在先受理,但西班牙是否应当中止诉讼或拒绝行使管辖权问题,应当由西班牙法院去解决。此外,英国法院不能凌驾于其他国家法院之上。再则,如果有多个法院可以签发这种禁诉令,这种禁令之间很可能相互冲突。根据该公约这样进行推理,显然是这个道理。
至于欧盟法院对Turner 诉Grovith和 Gasser诉 MISAT两个案件的裁决是否达到了最佳的公正效果,现在还很难说。 法官们还没有机会对这些生效的判例进行评论。因此,我们还是回到保护仲裁管辖的禁诉令这个问题上来,以便忠实地遵守欧盟法院在适用该公约时所确立的原则。
仲裁与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
现在,肯定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保护仲裁管辖的禁诉令与保护法院管辖的禁诉令相比,二者有何区别?向英国法院申请禁诉令以强制欧盟国家的当事人履行伦敦仲裁协议的行为,是否属于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调整的范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表面上来看,Turner诉Grovit和Grasser两案判例的原则是可以适用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若从表面上来看,两案的原则不能适用,尽管从感情上说,这两起判例更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在采取这种预先救济措施时,应当慎重。
首先看一下该公约或欧盟规则本身的规定。第一条是适用范围和仲裁除外(arbitration exclusion)的规定。布鲁塞尔公约的仲裁除外条款是该公约的第1条第4款,而现行的欧盟规则的仲裁除外条款是第1条第1款和第1条第2(d)款。该规则规定:
“1.1 本规则适用于民事和商事(纠纷),而不管法院或裁判庭的性质。
1.2 本规则不适用于:…… (d) 仲裁”
在The Atlantic Emperor(1992)一案 中,有关法官对“仲裁除外”的含义曾做过探讨。该案的被告Impitanti公司将一批石油以FOB的价格条款卖给原告Marc Rich公司。货物装船后,Marc Rich公司声称货物污染,要求对方赔偿巨额的经济损失,Impitanti公司否认自己有责任。1988年2月18日,Impitanti公司向意大利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告他们对Marc Rich公司的损失不负有赔偿责任。起诉状于2月29日送达给Marc Rich公司。就在这一天,Marc Rich公司在伦敦提起仲裁。Impitanti公司未指定仲裁员。后来,Marc Rich公司申请英国法院代表Impitanti公司指定仲裁员。法院准许该公司将该申请书送达给域外的意大利Impitanti公司。Impitanti公司随后申请(英国法院)撤销其域外送达令。该公司认为,合同中根本不存在仲裁条款,而且也从未达成过仲裁协议。因此,该公司认为,双方之间的争议应当适用布鲁塞尔公约,英国法院没有管辖权。Marc Rich公司则认为,双方的争议不应适用布鲁塞尔公约第1条第4款的规定。由于这个原因,该案成了一件马拉松式的官司,并因此而出了名。Marc Rich公司后来(在英国的一审中)完全胜诉 。案件上诉到英国上诉法院。该上诉法院向欧盟法院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该院给与预先裁决。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该公约第1条第4款中的除外规定,(1)是否适用于任何诉讼或判决?(2)当事先有仲裁协议时,是否也适用于该诉讼或判决?”
欧盟法院认为,该公约不适用于仲裁,因为其他的国际公约特别是纽约仲裁公约对仲裁已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塞尔公约的缔约国制定公约时,其目的是整个公约都不适用于仲裁,包括(因仲裁问题)向内国法院提起的诉讼。该法院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本案存在仲裁协议或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该公约是否是适用?该法院以这样的措辞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项争议是否属于公约调整的范围,只能看争议的内容(subject-matter)。如果双方争议的内容(比如指定仲裁员)不属于该公约调整的范围,那么,法院为解决该争议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preliminary issue)也不能适用该公约,不管这种前提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欧盟法院对The Atlantic Emperor一案所作的判决到底倾向于哪一种观点。我们再看一下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最新判例:The Ivan Zagubanski(2002)一案 。
在这个案件中,货物装上The Ivan Zagubanski轮后,(船长)签发了含有仲裁条款的提单。该船舶在航行中发生爆炸,货方(cargo interests)接着提出了货物灭失损害的索赔。一些布鲁塞尔公约缔约国的货主在法国马赛提起了诉讼。申请人船东申请英国法院宣告仲裁条款有效,并要求签发禁诉令以限制被申请人货方在马赛或其它法院提起诉讼。货方认为,船东的申请属于布鲁塞尔公约调整的范围,因此,只能在其居所地向船东提起诉讼。同时,他们还对英国法院向该公约的缔约国当事人签发禁诉令的制度提出了异议。
Aikens法官(英国法官)认为:1、为宣布仲裁协议效力和申请签发禁诉令而在英国提起的诉讼,不属布鲁塞尔公约调整的范围。这些诉讼的“核心内容”(essential subject-matters)和争议的焦点应当属于布鲁塞尔公约第1条第4款规定的“仲裁除外”;2、只要居于欧盟成员国的当事人违反(仲裁)合同义务,英国法院就有权行使管辖权并对该当事人签发禁诉令,限制其在其它缔约国法院提起诉讼。
违反仲裁协议而签发的禁诉令不属于该公约的调整范围。对这一论断,Aikens法官提出了如下理由:
1、如果某缔约国法院或裁决机构做出的裁决是针对“仲裁”的,那么,这种诉讼或裁决不受该公约的调整。该公约无意对缔约国的当事人就仲裁问题提供任何“法律保护”,因为,仲裁问题不属于该公约的调整范围。
2、从有关的报告可知,在The Atlantic Emperor(1991)一案 中,首席大律师Darmon先生认为,因仲裁协议引起的纠纷不受该公约调整。此外,该大律师还表明了这样的观点:适用布鲁塞尔公约确定(仲裁)管辖权会有损害于国际仲裁;尽管在仲裁的时候偶尔需要法院的协助,但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法院(对仲裁纠纷)无管辖权。Aikens法官认为,该大律师的观点“不仅系统,而且令人信服” 。正如该法官所说,“其论点和结论是,法院以仲裁问题为争议焦点所进行的诉讼或所作的判决,不是布鲁塞尔公约调整的对象。”
3、尽管The Atlantic Emperor(1992)一案的裁决,仅涉及指定仲裁员是否受该公约调整这个问题,但该法院采纳了“仲裁除外”这一普遍认可的观点,而且在其裁决中并没有任何语句表明该法院不接受该大律师的观点。
4、自The Atlantic Emperor(1992)一案作出判决后,英国法院仅仅作出过一次与此有关的判决,即Diamond法官在审理The Heidberg(1994)案件 所作的判决,且该判决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 。对于该判决,Aikens法官根据欧盟法院对The Atlantic Emperor一案的判决要旨 、有关的案情报告以及欧盟法院对Van Uden Maritime BV诉Kommaditgesellschaft in Firma Deco-Line(1999)案 所作的裁决,提出了不同意见。
5、Aikens法官的结论是,“禁诉令的请求标的(the object of claim)是通过英国法院行使签发禁诉令的权力,迫使被告履行伦敦仲裁协议。该请求的主要焦点(principal focus)和核心内容也是仲裁,因为,其请求的内容是通过法院的救济措施来履行仲裁协议。正如欧盟法院在审理Marc Rich和Van Uden 两案所述的那样,如果“依照该公约第1条第(4)款项,该公约当时的意图是完全不适用于仲裁,包括向内国法院提起的诉讼”,那么我认为,当事人申请禁诉令以便强制履行仲裁协议,也肯定属于第1条第(4)款规定的内容。”
欧盟法院在审理Turner诉Grovit(2004)一案 时,货方提出,不管这个问题是否适用该公约,英国法院原则上应当拒绝签发禁诉令,因为,签发这种禁诉令不符合布鲁塞尔公约的法律制度;英国法院的出发点应当是遵循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解决管辖冲突的模式是,由先诉法院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他们还认为,英国上诉法院对签发这样的禁诉令已不再像The Angelic Grace(1992)判例 做出时那样热心。为此,他们还引用了英国的Philip Alexander Futures & Securities Ltd诉Bamberger(1996) 和Toepfer诉Cargill (1998)两个判例。Aikens法官认为,后来审理的这两个案件,并未确立“任何新的原则”,他仍应遵循Continental Bank诉Aeakos(1994) 这一判例。
Aikens法官的上述观点也许还值得探讨。如上所述,在布鲁塞尔公约的框架内,很难协调Continental Bank诉Aeakos(1994)、Gasser诉MISAT(2004)和Turner诉Grovit(2004)三个判例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Aikens法官的第一个结论的理由成立,那么,申请强制履行仲裁协议的禁诉令就不应受布鲁塞尔公约的调整,因为,从公约的本身来看,还没有直接的规定。但现在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欧盟法院在The Ivan Zagubanski(2002) 案件时,又支持了货方的观点。看来这场争论又得从头开始。解决这场争论的任务还得交给英国法院。当然,现在就预测以后的判决结果也许并不恰当。英国法院很可能根据英国法律自主解决这个问题,但肯定会顾及我们欧盟同伴国的感受和他们的法律制度。对这一点,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
其它解决方案
在对本文进行归纳总结之前,有必要在探讨一下其它的解决方案。一方当事人之所以敢于冒险违反合同义务,就是因为他们坚信,在本国法院诉讼要比去外国仲裁有利得多,至少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不幸的是,现实情况确实如此。一般说来,不管对这种行为是否可以签发禁诉令,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而且现有的解决方案还没有一个比禁诉令更方便。那么,是否还有其它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相信外国的法院会中止诉讼。毫无疑问,这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对大陆法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但问题是,当法学理论和欧盟规则所推崇的互信理念一旦遭到破坏,还根本没有应对的解决办法。不得破坏信用的理念,解决不了现实存在的问题。
第二种方案:不承认违法的判决(offending judgment)。同样,这也是一种理想的方案。总的来说,英国法院会执行伦敦的仲裁裁决,而对外国法院应当中止诉讼进行仲裁而未中止所作出的判决,英国法院将拒绝承认或执行。但是,这种方案会产生一些令人迷惑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这里不再详述。总之,(英国)《1982年民事管辖与判决法》第32条(1)(a)款规定,如果“外国法院的诉讼违反了当事双方不是在该国法院解决纠纷的协议”(如某国法院不顾伦敦仲裁协议所做出的裁决),英国不承认或执行该外国法院做出的裁决。但是,除了该条规定外,该法第32条第(4)(a)款还规定,“本条第(1)款的规定,不影响英国承认或执行(根据布鲁塞尔公约)应当承认或执行的裁决。”这样,马上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若英国人认为存在伦敦仲裁协议,某缔约国法院不顾该仲裁协议做出了裁决,根据该公约的规定,这种裁决是否应当承认或执行?如果不承认或不执行,似乎也符合(英国)《1982年民事管辖与裁决法》第32条第(1)(a)款的规定;如果承认或执行的话,则该法第32条第(1)(a)款的规定必须让位于该法第32条第(4)(a)款。如果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根据该公约第27条的规定,以“承认该裁决有违承认国的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呢?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英国法院已经进行了诉讼(假定该诉讼内容为宣告仲裁协议的效力),而且英国法院已经做出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裁决,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第(3)款的规定拒绝执行该外国法院的裁决呢?这些问题已足以说明采用这一方案的复杂性。
第三种方案:对违反仲裁协议的行为,按损害赔偿予以救济。已经有过这样的判例,比如Mantovani诉Carapelli SpA(1980)一案 。信赖损失(reliance loss)的计算比较简单,也就是(对方)违反合同后而必须花费或支出的费用。但是,预期损失(expectation loss)怎么计算?如果采用损害赔偿这种方案,一方面本国法院可能会不接受外国法院的计算方法,另一方面,“无辜的受害方”也可能根本得不到对方的任何赔偿。这些问题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此外,对布鲁塞尔公约有关未决案件(lis alibi pendens)的规定,还要下一番功夫去理解。欧盟规则虽然是最近才制定的,但对其第30条的规定如何理解也不那么容易。此外,英国实行损害赔偿诉讼是否符合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第22条(欧盟规则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也不无疑问。对这种方案,这里只要说一下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也就足够了。
谈到上述解决方案,还令人想到了两点:第一,尽管这里探讨的都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人纠纷,但仍有必要站得更高些来看待这些问题。所有欧盟国家(包括英国)对管辖制度的构建都具有合法利益(a legitimate interest)。英国还有一层利益,这就是要保护伦敦仲裁,因为,伦敦是解决国际纠纷的中心。显然,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研究解决问题也很重要。要知道,缔约国个体的利益也是合法的。现在要做的是,在信赖公约或欧盟规则与维护国内合法利益之间要取得一种平衡。
第二,在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框架内,因禁诉令引起学术界的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禁令可能视为是对缔约国间秩序的一种威胁。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即使没有这种禁诉令,现实面临的问题就因学术有争议而不存在吗?通过禁诉令程序做出缺席裁决几乎一点也不费事,而如何处理对禁诉令的有关异议,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它看起来简单,有人说,它与处理管辖权异议没有什么区别。许多国家将案件实体诉讼与管辖异议合并审理。他们的实践表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常常将这个问题一直拖下去,一直拖到当地法院对是否中止诉讼问题作出裁决。如果这种拖延的时间过长,商业诉讼的意义也就变味了,最后只能根据实力,由当事双方自行和解。但是,欧盟法院并不允许过分拖延诉讼。对实践中遇到的上述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几篇文章做过专门的论述。合乎逻辑与实践经验不一定总是相依相符。
综述
对以上讨论的禁诉令问题,下面做一综述:
1、如果不考虑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对付违反仲裁协议的人或对付以此相威胁的人(即禁诉令的对象),普通法中的禁诉令可以说是一件非常有力的武器,其效能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对这种武器的使用和发展,普通法没有什么好歉疚的。我们能够并且也应当向其他法律制度学习,但不能对我们自己固有的良好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信心。
2、武器的作用就是用来对付精心挑选的目标。对付违约行为,禁诉令是一种需慎重使用并由法官自由裁量的救济措施。英国法律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禁诉令只能用于对人诉讼。如上所述,我们无需要求其他国家支持这种作法。尽管我们有必要预防有人通过悬赏来搜罗反对者,但对Leggatt法官在审理Philip Alexander Securities & Futures Ltd.诉Bamberger(1997)一案 中充满睿智的探讨也深表尊重。他强调,对禁诉令的对象,法院要有合法的管辖权。如果有合法的管辖权,法院可以充分使用禁诉令;如果没有,法院在签发禁诉令时,应当三思而后行。
3、对不涉及欧盟当事人的案件以及不在欧盟成员国法院起诉的案件,(英国法院)可以继续使用禁诉令以维护仲裁协议。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
4、在布鲁塞尔公约或欧盟规则框架内,(签发禁诉令)还应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在欧盟内,有一股这样的力量,他们认为,签发禁诉令不符合欧盟规则;因违反仲裁协议而造成的损失,可以间接的通过执行损害赔偿判决获得补偿;最重要的是要信任其他欧盟国家的法律制度,而这种信任与欧盟规则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5、即使禁诉令的对象居于欧盟成员国,而且是在其他欧盟国家的法院提起的诉讼,签发禁诉令以限制违反仲裁协议的做法,仍具有明显的诱惑力。欧盟规则有可能适用于仲裁,也可能不适用。如果该规则不适用于仲裁,正如Aikens法官在审理The Ivan Zagubanski一案时所分析的那样,签发禁诉令并不影响欧盟规则,个人感情因素对法律政策的形成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站在伦敦的位置考虑问题,也并非不恰当,因为伦敦是国际纠纷的解决中心,英国有权维护其伦敦仲裁的合法利益。
6、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欧盟其他国家不再接受为强制履行仲裁协议而签发禁诉令的做法,那么对违约的当事人,人们还得发展其他的应对方式。很显然,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并不仅仅是不承认违法判决或对这种违约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问题。毫无疑问,普通法的适应能力在制定新的救济措施以填补该项空白的过程中,将会充分发挥作用。此外,建议当事人也要适应欧盟规则,确保其选择的法院为先诉法院。
7、当普通法与大陆法因制定公约而发生融合的时候,会遇到许多困难。本文讨论的仅是其中的一个。由此也提醒我们,要达成这样的国际协议,需要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要保护我国的利益和我国的法律制度,同时要时刻牢记,任何公约的形
成都是(各缔约方)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的结果。互信是欧盟规则的基石。为了以后加强互信,若现在就提出我们的法律或外交议案,强调维护公平竞争平台的重要性,也许为时并不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