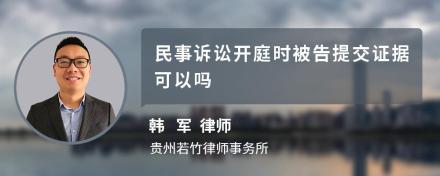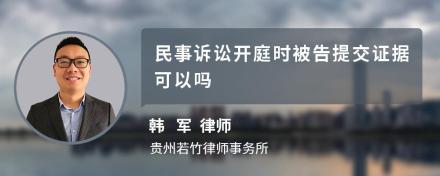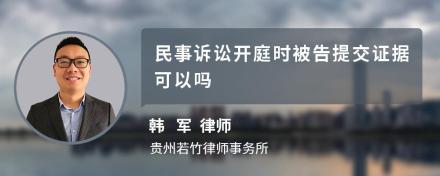一、案情和背景
200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等12个州、3个城市和一些环保组织向美国联邦环保局(EPA)提起诉讼,声称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已经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美国联邦环保局应当按照《清洁空气法》第202(a)(1)条之规定,制定规章,对新车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事项进行管制。被告认为,原告所声称的遭受到的健康和利益损害和美国联邦环保署拒绝制定对新机动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进行管制,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原告所声称遭受到的损害,并不会因为环保署制定一个满足原告请求的规章就可以得到救济。2007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票对4票的比例通过对于该案的判决,认定:(1)二氧化碳也属于空气污染物;(2)除非美国联邦环保局能证明二氧化碳与全球变暖问题无关,否则就得予以监管;(3)美国联邦环保署没能够提供合理解释,来说明拒绝管制新汽车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排放的原因。[1]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声称其无权限管制新汽车和货车的废气排放并不正确,政府必须管制汽车废气的排放。
法院多数意见支持了马萨诸塞州和其他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且认定马萨诸塞州等原告符合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三个要件(the three—part standing test):第一,马萨诸塞州面临重大的“伤害”。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了一系列环境的变化,例如地球上海平面的上升,将会摧毁马萨诸塞州大部分的海岸财产。第二,因为联邦环保署拒绝对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管制,加速了马萨诸塞州的“伤害”,所以汽车向空气中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废气。事实上,仅仅就从交通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而言,美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二氧化碳排放国。第三,虽然管制汽车的废气排放,但却不会消除全球变暖现象,它只会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Chief Justice Roberts)对于多数意见认定的马萨诸塞州享有原告资格的意见不予认同。尽管他清晰地指出他的结论不是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存在与否。他声称马萨诸塞州不符合原告诉讼资格的三要件法则(the three—part standing test):第一,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问题,它改变了全世界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单独、惟一地改变了马萨诸塞州的空气质量。他说,如果要说马萨诸塞州将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而失去海岸土地,这是一个“纯粹的关联”(pure conjecture)。[2]第二,关于多数意见所说的从新的汽车中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将会影响150年的全球气候,仅仅代表了温室气体的微小的一部分,由此只会减少马萨诸塞州失去海岸土地的机会。第三,因为80%的温室气体产生于美国本土之外,那么就是说仅仅减少美国本土的新的汽车废气的排放,对于马萨诸塞州所声称的“损害”的救济(redress)微不足道。例如,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无疑会抵消美国本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因此,多数意见主张认定马萨诸塞州等具有原告资格是错误的。下面我们就“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案中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马萨诸塞州作为一个州,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能否作为一个原告出现,换言之,它是否享有诉权?
二、马萨诸塞州在该案中是否享有诉权?
美国法院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认定,与我国等其他一些国家存在一些差异。尤其在“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案件中,提起诉讼的有若干个人和团体:美国的12个州、若干环境和公民团体、哥伦比亚特区、美国萨摩亚群岛(南太平洋)政府、纽约市和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城市)的市长和市议会。法庭对于原告资格的分析,集中在了马萨诸塞州政府身上。令我们感到有趣的是,法院在本案中的分析,不是首先开始于如何适用1992年审理的“鲁汉诉国家野生动物联盟”案[3](以下简称鲁汉案)的原告资格条件——事实上的损害(injury—in—fact)、因果关系(causation)和可救济性(redressability),而是首先注意到马萨诸塞州作为一个州政府所具有的“特殊位置和利益”的特殊性。法院将马萨诸塞州的利益类比为Georgia v.Tennessee Cooper Co.案[4]中的“准主权利益”。然后,法院分析了马萨诸塞州如何适用鲁汉案中的原告资格的三要件。那么我们来看看法院是如何论证马萨诸塞州享有诉权的。法院区分了一个主权者潜在具有的利益,将其分为三类:(1)所有者利益(proprietary interests);(2)准主权利益(quasi—sovereign interests);(3)主权利益(sovereign interests)。这三类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州政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享有的利益。
(一)所有者利益
第一类是所有者利益(Proprietary Interests),这种利益好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一块土地所享有的所有权或投资公司而形成的股权。因为州政府所声称具有的所有者利益,就像一个私人声称享有某种利益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州政府的利益与私人的利益进行人为的区分,两种利益其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州政府提起诉讼就像一个私人提起私人诉讼一样,无可厚非地享有诉讼资格。[5]
(二)准主权者利益
第二类是准主权者利益(Quasi—Sovereign Interests),虽然法院从来没有详细地定义这种利益,但是却对什么是准主权利益提出过指导性的意见。它们通常包括一系列利益,这些利益体现在州政府对于它的人民的健康和安宁所具有的利益上。例如,这些利益包括了州政府禁止公共侵扰等环境污染方面,体现了政府在保护公民的健康和安宁方面所具有的利益;或者州政府在保护公民在参与联邦法律制度中所享受的利益。州政府提起诉讼的利益的基石,是在于它的准主权利益——它提起诉讼来捍卫它的公民——历史上曾经体现为“国王的特权”(royal prerogative),体现了国王保护人民的权利或责任,尤其是那些由于精神上或身体上的障碍而不能自我照顾的公民。现代的“国王特权”的版本,被我们称之为“君权诉讼资格”(parens patriae standing),但是国家主权者提起“君权诉讼”的能力,不再要求国家代表那些不能自我代表的公民;相反,今天为了使得国家享有“君权诉讼”原告资格,主权者必须声称准主权利益遭受到了“损害”,即有关居民健康利益的损害。
正如托马斯‘梅若里(Thomas Merrill)教授解释的那样,建立在准主权利益基础上的诉讼,例如公共侵扰诉讼。当公共官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的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不应该像私人提起诉讼时那样严格。[6]这是因为这些诉讼是公益诉讼,类似于刑事控诉一样,法庭从来没有要求主权者来满足“鲁汉案”的原告资格条件的要求。相反,当一个州政府在它的主权之外的法庭上提起诉讼,那么建立在准主权者利益之上的诉讼资格,就像康尼迪各州,在联邦法庭中,对于若干电力公司提起公共侵扰诉讼,寻求气候变化损害的损害赔偿。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州是否满足“鲁汉案”的要求。我们看到了两个可能性:
第一,当一个州政府声称准主权者利益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它不可能符合起诉资格的要求。这个观点得到了好几个联邦案件的支持,例如Georgia v.Tennessee Copper Co.案件,尽管缺乏任何明显的考虑,当州政府提起诉讼的时候,这从来没有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鲁汉案件出现之前的50年内,几乎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正如梅若里教授建议的那样,一个州政府在联邦法庭中提起诉讼,来声称具有准主权者利益,应当被归结到适用于打抱不平的公民提起诉讼的宪法第三条(Article III)和谨慎的起诉资格限制上。[7]这个宪法第三条要求,能够被表明“州政府本身遭受到了的损害”或“州政府有能力来代表那些受害的公民,它们遭受到了损害”这两个条件之一就可以满足起诉资格的要求。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是,“当一个州政府提起“君权”(parens patriae)诉讼的时候,州政府是否具有起诉资格?”因为,一个州的政府准主权者利益建立在“保护它的居民的健康”上。好象似乎一个州不应当被允许来作为“君权”(parens patriae)进行起诉联邦政府,因为联邦政府不仅仅担负同样的义务来保护它的居民,而且它也要比州政府在保护人民方面更强大。在这个方面,法庭援引了Massachusetts v.Mellon案,指出当提到保护公民权利的时候,“它应当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州,代表人民作为君权。”[8]
(三)主权者利益
第三类是主权者利益(Sovereign Interests),它是这样一种利益,包括了“制定和实施一项法典的权力,包括民法和刑法典”和“要求其他主权者承认的权力”。这个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刑事控诉,如梅若里解释道:“一个美国的检察官,经过法律的授权,提起一场联邦刑事控诉,从来没有或者应该被要求证明美利坚合众国遭受了事实上的损害、犯罪引发了损害、一项判决会对于损害进行救济或一项犯罪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冤屈。”[9]
明显的是,我们长期存在的司法实践证明,当一个州政府声称主权者利益,至少在它的法庭上,它并不需要满足“鲁汉案”的要求。当一个州政府不在它的辖区的法庭上,起诉联邦政府的时候,问题是是否一个Mellon—type式的律师会阻止这场诉讼,如果不是的话,是否这个州必须满足“鲁汉案”的要求。芝加哥大学环境政策教授巴瑞·莱伯(Barry Rabe)认为:“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对全球气候变暖越来越关心,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同联邦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地方州在许多领域非常积极,如有22个州规定,在它们生产的能源中,必须有一定的比例是可再生能源;另外,在美国东北的十个州,为减少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了《区域温室气体动议(RGGI)》,这是一个大趋势。”[10]莱伯却认为地方政府的参予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美国是世界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地头号大国,有些州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大的惊人。比如在1999年,居美国温室排放量之首的德克萨斯州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赶英超法,加州的排放量超过了整个的巴西。当然,反对加州的声音也存在。气候政策中心(Climate Policy Center)主任李·莱恩(Lee Lane)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地方州的行为非常荒唐(preposterous),”他认为气候变暖问题是全球问题,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而加州的控制温室效应气体的单方面努力不见得能有明显的成效。
三、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重要先例
(一)鲁汉诉国家野生动物联盟案件
1992年审结的“鲁汉诉国家野生动物联盟”(Lujan v.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案。美国《濒危物种法》(ESA)第7条要求每个部门都应就其行为是否会危及濒危和受威胁的物种的生存及其栖息地咨询相关部门的意见。内务部长发布了一个对《濒危物种法》第7条的新解释,只要求发生在美国和公海上的行为才需要咨询。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其他环保组织对内务部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内务部错误地解释了《濒危物种法》第7条的适用地域范围,并强制要求内务部发布一个新的解释以取代现有的解释。为了证明其起诉资格,原告的两名成员宣称曾经到海外几个可能受到影响的地区观看和研究濒危物种,并且他们有计划再回去。法院认为原告未能制定一个具体的旅行安排(因为这些地区正处于战乱),其成员所宣称的损害不是紧迫的,纯粹只是普通公众的一般化的抱怨,不符合事实上的损害(iniury—in—fact)的要求。例如其中一个成员声称她曾到埃及去旅行,在那里她观察到了濒临灭绝的尼罗河鳄鱼传统的生活习性,她声称她再也不能去观察了,因为联邦政府参与的一项计划危害到了动物的生活习性。另外一个成员声称曾去斯里兰卡,在那里她观测了濒临灭绝的生物如亚洲象和美洲豹的生活习性。她声称她将会从联邦政府的一项潜在地威胁这些生物生存的计划中遭致损害。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请求不具有可救济性,因为损害发生在海外,即使法院做出一个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也不能救济原告的损害。因而做出原告不具有起诉资格的判决。
在考虑这些成员的诉讼资格问题上,法院归纳出了一个标准,成为了后来环境诉讼资格问题的奠基石。大法官斯卡利亚(Justice Scalia)进行了如下的表述:“第一,原告必须承受了一种事实上的损害(injury—in—fact),即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侵犯,而该利益属于:(a)具体的和特定化的(concrete and particularized);(b)真实的或迫近的(actual or imminent),而非关联的(conjectural)或假设的(hypothetical);第二,必须在损害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即损害可以合理地追溯到被告的行为,同时并非属于案件当事人的独立的第三人的行为结果。第三,法院下达的支持性的判决对于损害的救济而言,它必须是具有“可能性”的,而不是仅仅是“臆想性”的(speculative)。[11]
(二)地球之友诉兰得洛环境服务公司
关于环境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地球之友诉兰得洛环境服务公司”案(Fiends of the Earth v.Laidlaw Envtl.Setvs.)(以下称兰得洛案)也是个比较著名的案件。[12]1986年兰得洛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购人一套有毒废物焚烧装置,不久该州给兰得洛公司发放了一份国家污染排放削减项目许可证,允许它向北泰格河排放废水,并对其特定的污染物实行排放限制。在1987至1995年间,兰得洛违反许可证几乎达到500次。[13]一个名叫“地球之友”(Frlends of the Earth)的环保组织向法院提起了公民诉讼。为了支持原告享有起诉资格,“地球之友”依据他的一些成员遭受到了损害的事实,例如一个成员声称他住在离兰得洛公司厂房和北泰格河半英里之外的地方,河流看起来和闻起来像受过污染。他说他喜欢在河岸和河里娱乐如游泳,但是他担心的是河水的污染会阻止他去娱乐。另外一个成员提出了一个近似的声称,她说她住在离污染源两英里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她曾经进行许多娱乐活动,例如观察鸟儿和散步,然而,她由于担心污染造成对她身体健康的伤害,她停止了以前的行动。[14]
在该案中法院根据“鲁汉案”的原告资格三要件理论,认为“地球之友”具有原告资格。大法官金斯伯格(Justice Ginsburg)书写了多数意见,认定原告们已经证明他们由于污染物的排放而遭受了“事实上的损害”,而且被告的违反许可证的排污行为直接地影响了“地球之友”成员的“娱乐、审美和经济利益”。另外,最高法院重点审查了民事罚款对原告的损害能否提供救济。多数法官的意见认为,只有当被告切实遵守了许可证或者关闭了其设施,使得违反许可证的行为绝对不会再发生的情况下诉讼才可能结束,而本案中这些问题是有争议的,所以第四巡回法院认定本案已经结束不合适。民事罚款的威慑作用可以防止将来违法的发生,所以,原告因被告的排放行为对他们的休闲、审美和经济利益的损害可以获得救济。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地球之友”一案对环境公民诉讼有重要影响。它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解释更接近议会建立公民诉讼的意图。有关“事实上的损害”的认定问题,与以前的案例相比,本案对议会就损害的认定给予实质的尊重。从本质上讲,只要被告违反了一个具体的法律,法院就可以认定构成损害,原告可以从这个违法行为中合理地证明自己所关注的利益的损害。法院不聚焦于被告的行为是否引起环境自身的损害,也不讨论污染程度。这明显放宽了诉讼资格的要求。关于“可救济性”问题,针对钢铁公司案中认为民事罚款是支付给国库因而不能救济私人损害的解释,[15]本案认为应该区分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违法和仍在进行的违法。对于起诉后仍在进行而且将来还可能发生的违法,民事罚款的威慑作用可以救济私人的损害。本案对“可救性”的解释使议会建立公民诉讼制度、通过纠正公共损害行为来救济私人利益的意图得到进一步的尊重。
(三)地球之友诉加斯顿铜再生公司
在随后的“地球之友诉加斯顿铜再生公司”(Friends of the Earth,Inc.v.G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案中,[16]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加斯顿铜再生公司(“GCRC”)购买了不含铁的金属熔炼设备。1992年根据《清洁水法》,地球之友起诉加斯顿铜再生公司,声称加斯顿铜再生公司违反了NPDES许可。第四巡回法庭首先认定,原告没有满足“事实上的损害”这样一个条件要求,认定:“证据没有能够证明原告所声称的供其娱乐的水,在事实上、迫近地遭受了污染。”[17]同时认为其中一个原告声称的对于其孙子畅游水中的时间限制,是基于“仅仅是设想”中的水的污染。法庭进而认定原告也没有证明被告的行为,是可以被追溯到其所声称的损害上的。这个方面的判决是依赖于原告没有能够提出任何科学的证据,来证明Shealy湖包含了任何来自于加斯顿铜再生公司化学物的排放。法庭认为从排放地点到原告所声称的损害地点之间的距离是“太远不足以推断出因果关系”。[18]最后,法庭认定原告应当通过提供水样或专家的证据,来证明相当的可追溯性的诉权因素。
可以看出,法院并没有遵循“兰得洛案”中的严格态度,认为起诉者无须证明其原告资格的存在,在审前就举证证明被告是否确实超过被许可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质。该法院认为,在起诉者证明其享有原告资格的阶段,他只需证明可能的损害存在即可。至于被告是否确实超过被许可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质,应留待于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再加以证明。
四、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告诉讼资格要件分析
(一)事实上的损害
对于事实上的损害而言,全球气候变暖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潜在的威胁,这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原告证明的是,原告具有一种“特定的利益”而非一般普通人群“普遍的利益”。[19]这种分析框架的一个实际的作用,是使得法院可以从一大堆类似和无意义的诉讼请求中解脱出来。既然在全球气候变暖案件中适用“鲁汉案”的原告诉讼资格三要件,那么第一个要件是要原告证明存在“事实上的损害”(injury—in—fact),原告必须证明两个关于损害的问题——损害的性质和损害的时间。首先关于损害的性质,原告必须证明他所遭受的损害是“具体的”和“特定化的”。[20]其次关于损害的时间,原告必须证明他遭受的损害或者属于“真实的”或者属于损害将会在“迫近的将来”(imminent future)发生。[21]这个要件集中分析以下四个组成部分:(1)具体的损害;(2)特定化的损害;(3)真实的损害;(4)迫近的损害。
1.具体的损害
原告必须证明存在一种具体的损害(concrete injury)。我们可以来看看先例“鲁汉案”的原告资格要件的阐述,原告必须能够证明他所遭受到的损害,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具体的利益。一个具体利益往往由经济、娱乐或审美构成。[22]因此,除了证明损害与金钱有关外,原告可以声称“他使用或者频繁地使用了一块被企业污染的土地,而且他的审美或娱乐利益遭受到了损害。”[23]以卡特里飓风给新奥尔良居民(美国港口城市)带来的损害为例,新奥尔良的居民在飓风中失去了他们的家园,遭受到了经济损失。再如,一个居民声称他将不再在密西西比河中享受划船或钓鱼的乐趣,他因此遭受了娱乐的损害。[24]新奥尔良市的另外一个居民或者一个游客,声称他不再能够欣赏到新奥尔良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美景,也可以声称他遭受到了审美上的损害。当然,对于声称全球气候变暖而遭受损害的原告而言,这个要件的满足的证明不是什么问题。
2.特定化的损害
其次,原告要证明的是,他们遭受了特定化的损害(particularized injury)。依据“鲁汉案”的要求,损害不仅仅是具体的,而且是特定化的。换言之,原告必须表明一个公司或联邦机构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实施了促进的工作,从而使得损害变得针对特定人。[25]这个要求禁止那些仅仅遭受一般化的伤害的(generalized grievances)的人提起诉讼,来主张他们对于公众而言普遍具有的利益。[26]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居民喜欢北极熊,与它们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经常在动物园观察它们,其可能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北极海平面的上升,威胁到了北极熊的生存。他声称对于他对北极熊的审美而言,他遭受了一种特定化的损害。[27]因为,他说他能够直接观察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熊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北极熊变得虚弱甚至濒临死亡,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因此受到损害。他遭受了一种旨在针对“个人化的”的损害,[28]而不是“大众化的”损害,所以其环境诉讼资格很容易立足。
在“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的巡回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的败诉在于没有紧紧抓住“损害特定化”这样一个概念,[29]而错误在于原告声称将这种损害描述为普及于公众的损害。在协同意见书中,法官(Judge Sentelle)总结说:“原告们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诉求,理由是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危害全人类的。”[30]一旦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了普遍的大众,类似这样的声称之所以会导致败诉,因为它表达的是代表了公众共同福利的“一般化的抱怨”(generalized grievance),它无法构成特定化的损害,因此无法满足在“鲁汉案”和“兰得洛案”中建立的标准。
3.真实的损害和迫近的损害
当原告证明了他所遭受的损害是具体的和特定化的之后,他还要证明的是他所遭受的损害,处于合适的“时间框架”(time frame)之中,即损害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原告没有能够证明他所遭受的损害属于“真实的”或“迫近的”损害,因为它们不能证明被告尾气排放最终的结果——全球气候变暖——产生或将要产生他们所声称的损害。当然,这个部分的分析与因果关系的分析容易产生混淆。有人认为这样的分析,包含了两个因果关系的探求:第一,是否全球气候变暖本身,即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副产品,会导致或将要导致原告所声称的损害;第二,是否被告的排放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以至于创造了自然的灾难因而导致了原告所声称的损害。
4.迫近的损害
法院希望原告能够证明他所遭受的损害,很有可能发生。法院拒绝裁判那些仅仅关于学术性的具有创造才能的设想,法院因此关注于“时间构成”——迫近的未来(imminent future)。[31]在“鲁汉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提供了一种实质性的限制,把这种“时间构成”描绘为“的确迫近”(certainly impending)。[32]“迫近”一词的确是一个具有弹性的词汇,它旨在保证声称的损害并非是设想性的。全球气候变暖案件中,原告没有能够证明“迫近的损害”将要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全球气候变暖的损害可以概括为“盖然性的损害”(probabilistic injuries)。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可能来临的损害威胁能够支持诉讼资格。然而,传统的诉讼资格理论要求损害必须是“实质上可能的”(substantially probable),联邦最高法院已经认同了这种标准,要求原告必须展示一种“由于被告的行为而发生的现实性的持续损害”。全球气候变暖中的原告们不能将“迫近的损害”从“想象的范畴”(speculative category)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的声称是完全建立在关联、复杂的气候模型上的。当然这些模型对于预测大气的状况,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何让法官们相信科学家们对于借助这些模型得出的结论呢?在大气研究国家中心研究了数年的一位人类学家,在他写的一篇论文中,承认气候模型学家们也不确定他们的发现成果。[33]
(二)因果关系
法院要求原告必须展示他所遭受到的具体的、特定化的损害,无论是真实的或迫近的,都是可以追溯到被告行为的,即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34]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在原告所声称的损害和被告的致害行为之间具有联系。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原告们没有能够证明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因果关系链条被许多其它的多重因素所削弱,而这些因素均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换言之,原告必须证明存在一种“实质性可能”,如果当污染企业减少排放废气的话、或者彻底不排放,那么他们的损害将不会发生。全球气候变暖诉讼因果关系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气候是庞大的、复杂的和难以理解的系统”,[35]因果关系链条开始于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关于大气如何对于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反应,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36]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而言,因果关系的证明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里存在着许多多重的、自然的和人工的诸多因素,这些都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而这些原因都会产生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灾害。然而,这些因素可能在因果关系链条上扮演着被附加的角色,被告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助于气温的升高,但是耕作和畜牧业对空气的损害的行为也有可能造成更高气温的升高。再如,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影响了温度,但是有可能城市的铺路和建筑,对于产生温度升高而言更具有影响。[37]另外,无法排除的太阳的活动也是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被告关于气候变暖的科学考察,不能让法院认定特定的被告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惟一原因。法院也不可能说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被告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环境灾害发生的原因。这样一种声称对于法院案件的审判而言,不符合“审判的成熟性”(ripe for adjudication)条件,因为它要视一系列因素而定,太具有想象性了。[38]
在一些环境污染案件中,特别是在清洁水法案件中,法院会将原告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离污染物质中心比较近的受污染者(zone of a polluter),另外一类是离污染物质比较远的受污染者,后者的损害不能清楚地追溯到污染物排放者那里。这样一种地理上的接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与法院在“鲁汉案”中的审判理念是一样的,否定了关联性理论(nexus theory),即认为距离会对损害造成妨碍。[39]这样的审判理念会对全球气候变暖案件中的原告们不利,因为他们认为来自数千里距离之外的污染也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例如,在Watson案件中的一个原告声称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引发了云杉树皮甲虫的爆发,造成了她所居住的安克雷奇(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港口城市)的森林的破坏。问题是她所说的排放温室气体的三家企业,分别位于非洲中北部的乍得湖(在乍得、尼日尔、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接界处)、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和东南亚岛国印尼。[40]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诉讼中,“污染质中心”检验法则(The zone of the polluter test)也不适用。当污染者将毒素排放到河流中,仅仅那些处于一个相对合理范围内的居民们会受到污染物质排放的影响。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居民不会因乔治亚州的河流受到了汞的污染而受到影响。然而,我们却可以这样合理地说,一个项目排放出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进入到了南美北部的委内瑞拉国家的空气中,将会加速全球的气候变暖,由此会影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换言之,“污染质中心”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而言,就没有中心可言了。由此,原告不需要证明被告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单独地引发了损害。
当然,缺乏地理上的接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不会阻止原告们对于来自遥远地方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企业提起诉讼,科学目前尚无法为法院在判断到底由哪里的居民来提起诉讼更为适宜提供论证。美国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似乎并没有想让整个问题的解决变成一个科学的论证,但是原告们起码需要证明他遭受到了被告行为的不利影响。在Gaston Copper案件中,如果法院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原告遭受损害的一个原因,那么他需要另外证明损害的多种来源的责任分担问题。整个责任的负担似乎已经超出了原告资格要件的问题。[41]目前,科学尚无法为原告证明企业排放温室气体而展示这样一种“实质上可能性”,影响了原告的具体的、特定化的利益。
(三)可补偿性
“鲁汉案”和“兰得洛案”两个案件包括了可补偿性(redressability)作为诉讼资格构成三要件的组成部分,这部分要件要求法院来认定是否法院的判决能够对原告们的损害进行救济。[42]只有当原告向法院证明被告引发或将要引发他所说的损害,法院才会对其救济,该救济会对原告的损害“以一种切实的方式”进行。[43]全球气候变暖案件中的原告们对于证明该项证据不存在问题。例如,法律的赔偿可能会补偿新奥尔良居民在卡特里娜飓风中的损失,包括房屋、汽车和商业,提供他们所失去的财产的价值。一个禁令(injunction)可能补偿一个新奥尔良的居民,他声称公司的废气排放对于另外一场飓风的来临施加了威胁。这个禁令将会终止、或至少减少被告的废气排放,这样一来减缓了公司废气排放造成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和飓风来临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一系列针对排放废气的公司的诉讼而言,尤其具有意义。就达到的效果而言,一项禁令起码会“本质上减少原告们对于公司排放温室气体带来的危险的合理的关注”。[44]民事赔偿金(civil penahies)也可能会提供补偿,因为民事赔偿金会阻止未来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了造成灾害天气的可能性,而后者往往会引起飓风的发生。根据“兰得洛案”的宽泛的语言,任何“有效地缓和一个特定行为的发生和防止该行为发生反复的制裁都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救济。”[45]禁令或其它形式的衡平法救济,可能会有助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由此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
注释: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1]Massachusetts v.EPA,127 S.Ct.1438.at 1452—63(2007).
[2]Massachusetts v.EPA,127 S.CL 1438,at 1467(2007).
[3]Luian v.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555(1992).
[4]Georgia v.Tennessee Copper Company,206 U.S.230(1907)
[5]Cf.Ann Woolhandler&Michael G.Collins,State Standing,81 va.L.Rev.387,506(1995)(suggesting that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analyze state stand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common—law in—terests in propelty and liberty under a modified Lujan test).
[6]See Thomas W.Merrill,Global Warming as a Public Nuisance,30 Colum.J.Envtl.L.293,at 304(2005).
[7]See Thomas W.Merrill,Global Warming as a Public Nuisance,30 Colum.J.Envtl.L.293,304,at 305(2005).
[8]See Kathryn A.Watts&Amy J.Wildermuth,Massachusetts v.EPA:Breaking New Ground on Issues Other Than Global Warming,102 Nw.U.L.Rev.Colloquy J,at 6(2007).
[9]See Thomas W.Mereill,Global Warming as a Public Nuisance,30 Colum.J.Envtl.L.293、304,at 300—01(2005).
[10]See Barry G.Rabe,Mikael Romdn,&Arthur N.Dobelis,State Competition as a Source Driving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14 N.Y.U.Envtl.L.J.1,29(2005).
[11]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555,at 560—61(1992).
[12]Friends of the Earth v.Laidlaw Envtl.Servs.,528 u.S.167(2000).
[13]Friends of the Earth v.Laidlaw Envtl.Servs.,528 U.S.167,al 175—76(2000)
[14]Friends of the Earth v.Laidlaw Envtl.Servs.,528 U.s.167,at 181—82(2000)
[15]Friends of the Earth v.Laidlaw Envtl.Servs.,528 U.S.167,at 185(2000).
[16]Friends of the Earth,Inc.v.G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204 F.3d 149(4(th上标)Cir.2000).
[17]niens of the Earth,Inc.v.G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204 F.3d 149,at 113(4(th上标)Cir.2000).
[18]Friends of the Earth,Inc.v.C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204 F.3d 149,at 115(4(th上标)Cir.2000).
[19]Friends ofthe Earth v.G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204 F.3d 149,156(4(th上标)Cir.2000).
[20]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fe,504 U.S.555,563(1992).
[21]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555,563(1992).
[22]Friends of the Earth v.Laidlaw Envtl.Servs.,528 U.S.167,184(2000).It even appears that some courts consider a spiritual interest a concrete interest.In Defenders of Wildlife v.EnviromerUal Protection Agency,the plaintiffs liked to watch and take pictures of different animal species,as well as hike and camp in their habitats.420 F.3d 946,956(9(th上标)Cir.2005).
[23]Sierra Club v.Tenn.Valley Auth.,430 F.3d 1337,1344(11(th上标)Cir.2005);see also Laidlaw,528 U.S.at184.
[24]See Sierra Club,430 F.3d at 1345.
[25]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i,504 U.S.555,575 n.1(1992).
[26]Friends of the Earth v.G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204 F.3d 149,156(4(th上标)Cir.2000);see also Fed.Election Comm’n v.Akins,524 U.S.11,34—35(1998)(stating that those with generalized grievances should pursue those claims in the political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not within the judieiary).
[27]Animal Legal Def.Fund v.Glickman,154 F.3d 426,432—33(D.c.cir.1998)
[28]Animal Legal Def.Fund v.Glickman,154 F.3d 426,432—33(D.c.cir.1998)
[29]Massachusetts v.EPA,415 F.3d 50,59—60(D.C.Cir.2005).
[30]Massachusetts v.EPA,415 F.3d 50,60(D.C.Cir.2005).
[31]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555,560—61(1992).
[32]Lujan,504 U.S.at 564 n.2.
[33]See Holman W.Jenkins,Jr.,A Global Warming Worksheet,Wall St.J.,Feb.1,2006,at A15.
[34]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555,560(1992).
[35]See Holman W.Jenkins,Jr.,A Global Wanning Worksheet,Wall St .J.,Feb.1,2006,at A15.
[36]Mark LaRochelle&Peter Spencer,“Global Warming”Science:Fact vs.Fiction.Consumers’Res.Mag.,July 2001.at 5.
[37]See Sallie Baliunas,Full of Hot Air:A Climate Alarmist Takes on“Criminals Against Humanitv,”Reason,Oct.2005,at 64.
[38]Texas v.United States,523 U.S.296,300—01(1998).
[39]Lujan v.Defenders of Witdlife,584 U.S.555,567 n.3(1992).
[40]Declaration of Melanie Duchin at 2,niends of the Earth,Inc.v.Watson,No.C 02—4106(JSW),2005 WL 2035596(N.D.Cal.Aug.23,2005).
[41]Friends of the Earth,Inc.v.Gaston Copper Recycling Corp.,204 F.3d 149 at 162.(4(th上标)Cir.2000).
[42]Lujan v.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555,at 560(1992).
[43]Warth v.Seldin,422 u.s.490,508(1975).A plaintiffmust show that“the practical consequence”of a favorable Idecision would result in“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plaintiff would obtain relief that direcfly redresses the injury suffered.”Utah v.Evans,.536 u.S.452,464(2002).
[44]Interfaith Cmty.Org.v.Honeywell Int'l,Inc.,399 F.3d 248,257(3d Cir.2005).
[45]See Laidlaw,528 U.S.at 185—86.Justice Scalia found the Court’s treatment of redressability to be just as “cavalier”as its treatment of injury—in—fact.Id.at 202(Scalia,J.,dissenting).
《中外法学》

 01:30
人已看
01:30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