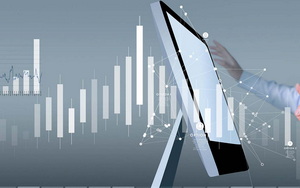相关知识推荐
-
定金合同范本
定金是指当事人双方为了保证债务的履行,约定由当事人方先行支付给对方一定数额的货币作为担保。定金合同要
合同纠纷人看过
-
抚养费标准多少
 01:35
人已看
01:35
人已看 -
自由心证主义的现代意义
其他论文人看过
-
相关主义
法理学论文人看过
-
抚养费标准的法律依据有什么
 01:33
人已看
01:33
人已看 -
宪政主义
宪法论文人看过
-
教师承担教育法律责任的条件是
教师承担教育法律责任的条件是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法律论文人看过
-
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什么
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立法的目的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
法律论文人看过
-
规定隐私权的意义
规定隐私权的意义是:保护隐私是对人性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宪法人权
法律论文人看过
-
隐私权的名词解释
隐私权的名词解释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是隐私权。自然
法律论文人看过
-
自甘风险的概念
自甘冒险的概念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
法律论文人看过
-
立功的效果是什么
立功的效果是:1、在法院判决之前立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法律论文人看过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