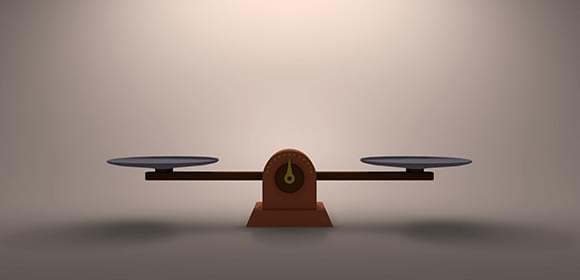(三)讼费负担实例分析
1.如果当事人试图穷尽起诉、诉前保全、反诉、上诉、申请强制执行等程序救济手段,他必须事先准备一笔案件受理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越大、争取全额赔偿的愿望越强烈,他为胜诉而预先支付的费用越高。我们不妨通过实例说明这一问题。
设:甲起诉乙,索要逾期未付的货款101万元; 乙反诉甲交付不合约定质地的货物而索赔101万元;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后, 甲申请保全乙价值101万元的财产。一审判决之后,甲、乙分别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令乙返还货物,甲无权获得货款,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各自负担诉讼费。二审判决生效之后,乙拒不返还货物,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上述案件,法院至少收取以下几笔诉讼费:(1 )甲在一审案件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5059. 87 元。 (2 )乙在一审案件交纳的反诉费15059.87元。(3)甲在一审案件交纳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570元。(4)甲交纳的二审案件上诉费15059.87元。(5 )乙交纳的二审案件上诉费15059.87元。(6)甲交纳的执行申请费3010元。
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中消耗的金钱至少是68819元。 这是假定法院完全遵守收费标准,没有“乱收费”,而强制执行又没有经过评估和拍卖的、最为理想的情况下的讼费负担。鉴于法院判决的结果是合同无效和恢复原状,除了法院之外,诉讼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
2.“gd公司”1997—1998年提起诉讼的13个一审案件和诉讼费(注:作者的信息来自“gd公司”一位职员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谨表谢意。)
“gd公司”是一个国有金融机构。在1997、1998两年,公司先后对20个债务人提起诉讼,笔者得到了其中13个案件的一审讼费记录。在这13个案件中,有8个是追讨借款本息, 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对债务的存在及本金、利息数额和还款期限都没有争议,因此,这8 个案件本来是可以申请支付令的非讼案件,完全不必交纳诉讼费而启动诉讼程序。该公司也曾经试图说服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法院不同意。假如公司通过申请“支付令”而主张债权,这8个案件的诉讼费可以节约99%。
表1.1997—1998年度“gd公司”在13个一审案件中预交的诉讼费
受案法院
索赔金额[1000元]
案件受理费[元]
诉讼保全费[元]
执行费[元]
某市一中院
28 217
151 100
164 450
486 500
某市一中院
5 148 usd
223 670
某市一中院
834 usd
44 640
35 160
某市一中院
58 338
301 710
292 220
某市一中院
21 485
117 440
107 950
某市一中院
2 840
24 210
14 720
某市一中院
12 299
75 510
某市一中院
6 746
43 740
34 250
某市一中院
5 061
35 320
某市一中院
14 856
84 300
74 810
某市二中院
2 965
24 839
某市西城区法院
649
11 510
某市市中院
18 176
100 892
合计
1 238 881
723 560
486 560
上表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和执行费三项总额2 449 001元
(三)讼费负担实例分析
1.如果当事人试图穷尽起诉、诉前保全、反诉、上诉、申请强制执行等程序救济手段,他必须事先准备一笔案件受理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越大、争取全额赔偿的愿望越强烈,他为胜诉而预先支付的费用越高。我们不妨通过实例说明这一问题。
设:甲起诉乙,索要逾期未付的货款101万元; 乙反诉甲交付不合约定质地的货物而索赔101万元;一审法院受理案件之后, 甲申请保全乙价值101万元的财产。一审判决之后,甲、乙分别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令乙返还货物,甲无权获得货款,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各自负担诉讼费。二审判决生效之后,乙拒不返还货物,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在上述案件,法院至少收取以下几笔诉讼费:(1 )甲在一审案件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5059. 87 元。 (2 )乙在一审案件交纳的反诉费15059.87元。(3)甲在一审案件交纳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570元。(4)甲交纳的二审案件上诉费15059.87元。(5 )乙交纳的二审案件上诉费15059.87元。(6)甲交纳的执行申请费3010元。
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中消耗的金钱至少是68819元。 这是假定法院完全遵守收费标准,没有“乱收费”,而强制执行又没有经过评估和拍卖的、最为理想的情况下的讼费负担。鉴于法院判决的结果是合同无效和恢复原状,除了法院之外,诉讼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
2.“gd公司”1997—1998年提起诉讼的13个一审案件和诉讼费(注:作者的信息来自“gd公司”一位职员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谨表谢意。)
“gd公司”是一个国有金融机构。在1997、1998两年,公司先后对20个债务人提起诉讼,笔者得到了其中13个案件的一审讼费记录。在这13个案件中,有8个是追讨借款本息, 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对债务的存在及本金、利息数额和还款期限都没有争议,因此,这8 个案件本来是可以申请支付令的非讼案件,完全不必交纳诉讼费而启动诉讼程序。该公司也曾经试图说服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法院不同意。假如公司通过申请“支付令”而主张债权,这8个案件的诉讼费可以节约99%。
表1.1997—1998年度“gd公司”在13个一审案件中预交的诉讼费
受案法院
索赔金额[1000元]
案件受理费[元]
某市一中院
28 217
151 100
同上
5 148 usd
223 670
gd公司为这13个案件支付的全部费用要远远超过表1 显示的总金额。该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与表1第三栏的“案件受理费”大致相当。 如果上诉,它需要向二审法院支付大致相当的“案件受理费”。此外,法官到外地处理涉案事务的一切费用,都是gd公司预先支付,法官凭开支发票销账,笔者无从考证这一部分费用的数量。
表1中有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事实,是第一个案件中的执行费。 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之后,法院认为债务人的财产需要按照法定规则评估,于是向gd公司“预收”了486560元“执行费”。据公司职员介绍,法院用这笔“执行费”聘请“资产评估机构”,而“资产评估机构”是按照财产评估价格的0.8%收取评估费。如果财产最终拍卖, 评估费将从拍卖所得中扣除。但是到1999年1月,该项财产仍未找到买主。 公司职员认为:如果无人购买债务人的财产,法院也“不可能退还”执行费。
在所有的借款案件中gd公司都是胜诉方,但是该公司通过申请强制执行而满足债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借款人都是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可以变现的财产。在本文完稿时,表1中案件1—5、8、12等7个判决已经强制执行完毕,申请强制执行的总金额是17170 万元,gd公司为这7个案件支付的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总额是1380310元,而真正被强制执行的财产只有43万元。如果公司放弃诉讼,至少可以避免增加950310元损失。gd公司起诉的主要动因与其说是实现债权,不如说是获得一种合法性证明:公司需要将法院判决和强制执行申请作为合法冲销坏账的证明,需要用法院判决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勤勉,而不在意判决是否能够得到执行。如果gd公司是私人企业,业主一定舍不得为一纸合法性证明而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
如今,随着“争议金额”而增长的高额诉讼费甚至超过了一些大公司可以承受的限度(注:90年代,诉讼费总额达到数十万、上百万的案件并不是个别情况,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编辑的案例汇编显示,民事诉讼实为耗费巨资的博弈:1.在《海南省海秀总公司因购销房屋纠纷提起上诉案》,仅仅见诸判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和二审案件受理费三项诉讼费支出就高达60万元。如果考虑到律师费、差旅费和其他开支,该案件的诉讼消耗估计要超过150万元;2. 在《联合租赁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提起上诉案》,两次判决的诉讼费支出是57万元,其中反诉费一项高达241059元;3.《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因代理发行债券纠纷提起上诉案》是一个并不需要消耗大量司法智慧的、情节相当简单的案件,当事人存在争议的债务总额是2700万元左右,诉讼费开支总共为999440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二审再审经济纠纷案例选编》,第331—335、433页。)。 高额讼费隐含的问题是:在按照“争议金额”计算诉讼费的制度下,成本较低的非讼程序是否已经消失?在强制执行不可能奏效或者没有经济价值的情况下,诉讼究竟是扩大还是减少损失?
(四)当事人如何挑战法院收取讼费的决定?
讼费负担是法院判决必备内容(注:《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但是,不服讼费负担判决的当事人,不得就此“单独提起上诉”(注:《‘89诉讼收费办法》,第29条。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民事诉讼法,都限制讼费负担的上诉,要求讼费负担必须和本案一并上诉。其理由是:“诉讼费用之裁判,乃本案裁判之结果,并无独立之性质,若许其独立而申述不服,则恐诉讼费用之裁判,与本案之裁判不符”(参见《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林纪东等编,1988年修订版,第477页)。然而, 这一规则的正当性理由是存在疑问的:如果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本案判决并无不服,仅仅不服讼费负担判决,他为何被剥夺上诉权?既然讼费负担是一个可能脱离本案判决而单独存在的错误,为什么法律禁止当事人通过上诉而纠正错误?);不服讼费“计算”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复核,法院经复核而认定收费“计算确有错误”,得裁定更正(注:《’89诉讼收费办法》,第32条。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民事诉讼法,都限制讼费负担的上诉,要求讼费负担必须和本案一并上诉。其理由是:“诉讼费用之裁判,乃本案裁判之结果,并无独立之性质,若许其独立而申述不服,则恐诉讼费用之裁判,与本案之裁判不符”(参见《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林纪东等编,1988年修订版,第477页)。然而, 这一规则的正当性理由是存在疑问的:如果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本案判决并无不服,仅仅不服讼费负担判决,他为何被剥夺上诉权?既然讼费负担是一个可能脱离本案判决而单独存在的错误,为什么法律禁止当事人通过上诉而纠正错误?)。在交纳讼费之前,当事人对讼费“计算”持异议,得申请同一法院“复核”-由可能错误计算讼费的法院自行裁定是否存在“计算”方面的错误,而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定不可提起上诉;在交纳讼费之后,除非当事人对讼费负担之外的本案判决一并提起上诉,并且交纳与一审案件受理费数额相同的上诉费,讼费负担判决不受二审法院审查,或者说,讼费负担判决是二审终审的一个例外。因此,与讼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挑战法院收取讼费的决定。
1997年, 济南三株药业公司对韩成刚提起侵害名誉权诉讼, 索赔5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韩败诉,赔偿原告1万元,案件受理费10460元由韩负担(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 )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韩就一审判决的讼费负担向上级法院提出异议:(1)法院收取名誉权案件的受理费最多是每案100元,法院按照“财产案件”向原告收取10460元案件受理费没有法定依据;(2)即使法院可以按照“财产案件”收取名誉权案受理费,法院收取的诉讼费也超过了法定标准;(3)即使法院收取10460元案件受理费没有超过标准,法院判决败诉被告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也是不公正的,因为法院判决原告赔偿的金额只是被告索赔金额的2%(注:韩成刚1998年10月8日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信,作者经韩本人同意而引用。)。虽然韩成刚后来错过了通过上诉而挑战讼费负担判决的机会,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是否存在其他选择:诉讼费和仲裁费的比较
仲裁费由“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两部分构成(注:国务院办公厅:《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1995)》,第2条。)。
案件受理费是仲裁机构的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政府要求仲裁机构“逐步做到自收自支”(注:国务院办公厅:《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1995)》,第4条。), 仲裁机构收取案件受理费的理由是“正常运转的必要开支”(注:国务院办公厅:《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1995)》,第3条。)。因此, 仲裁机构对案件受理费的关注程度决不亚于法院。
“案件受理费”由仲裁申请人按照“争议金额”预交(注:国务院办公厅的“收费办法”规定了仲裁案件受理费征收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一个“争议金额”为101万元的仲裁案件, 仲裁申请人应当交纳的最高数额的案件受理费为18600元。)。与法院不同的是, 仲裁机构是在收取“案件受理费”之前受理仲裁申请(注:国务院办公厅:《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1995)》,第4条。), 申请人在收到受理通知之后15日内未能交纳案件受理费,视为自动撤销申请。仲裁机构通常不会在收到申请费之前组织仲裁庭。
“案件处理费”覆盖仲裁发生的一切实际费用,“案件处理费”也是按照“争议金额”征收(注:按照北京仲裁委员会“案件处理费”征收标准(1996),一个“争议金额”为101万元的仲裁案件, 仲裁申请人应当预交的“案件处理费”为18550元。), 申请人至少需要预先交纳部分“案件处理费”(注:国务院办公厅:《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1995)》,第7条。)。在北京市, 仲裁委在受理案件时预收全部处理费,结案后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注:按照北京仲裁委员会“案件处理费”征收标准(1996),一个“争议金额”为101 万元的仲裁案件,仲裁申请人应当预交的“案件处理费”为18550元。 ):“案件处理费”的征收标准由北京市的物价局和财政局规定。
一个“争议金额”为101万元的案件, 当事人预交的仲裁“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之和为37150元, 相当于同一案件法院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之和的1.2倍, 仲裁案件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裁决,还需要另外交纳“执行申请费”。因此,仲裁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比诉讼便宜。
二、困扰中国一个世纪的形而上学问题-诉讼标的
法院就民事案件收费,这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制度。在古代中国,衙门审理案件历来没有法定规费。这不仅因为当时没有民案、刑案之分,而且因为皇帝和号称“为民父母”的官员公然向那些申诉冤屈、吁请公道的庶民收取裁判费,会被认为有失体面(注:有一种说法,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收取民事讼费:当事人各交纳一百枝箭作为讼费;若不交纳,则视为服输(参见冯卓慧、胡留元《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但是,西周根本不存在区分民事、 刑事诉讼的理念,何以会有专门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收费办法?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制度,为何仅见于“周礼”、“国语”而不见于其他历史文献?为何这种制度在西周之后就完全消失?笔者以为,如果西周真有纳箭听讼的制度,那么恐怕是古代盛行的“誓审”方式之一,纳箭听讼或许是以箭为誓,表明据实陈述的意思。)。当然,古代中国的诉讼绝不是免费游戏。“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民众批评衙门为金钱左右,是指衙门和官吏索取法外规费。例如在1907年之前,清律从来没有就诉讼征收任何规费或者印花税的规定,但是,衙门、书吏和差役向当事人收取名目繁多的法外规费则是不争之事实(注: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4、63页。从该书可以发现两个重要事实:(1)清律并不承认讼费合法性, 故讼费多寡是与成文制度无关的吏治问题,“官清则规费名目少,官浊则规费名目多”;(2)清政府不给“胥吏”发放工资或者津贴, 胥吏只能“在山靠山,在水靠水”,当事人成为“胥吏”任意盘剥、敲诈的对象,无规费之弊甚于有之。衙门和官吏的勒索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每一个诉讼环节,当时的法外规费有:“戳记费、挂号费、传呈费、取保费、纸笔费、出结费、和息费、买批费、出票费、升堂费、坐堂费、衙门费等”,“命案检验费、踏勘费、鞋袜费、车马费、舟车费、酒食费、解绳费、解锁费、到案费、带案费、铺堂费、铺班费、班房费、进监礼、保释礼、和息费、结案费、招解费等”。)。
1905年,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派遣董康等赴日本考察审判和监狱制度(注:沈家本:《日本裁判所构成法序》。)。1907年,译出《日本法规大全》;同年,清政府模仿日本法律,推出《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以下简称:《试办章程》),试图将司法机构从行政官僚体系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推行讼费征收制度(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07)》第六节“讼费”,载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1—23页。)。 《试办章程》无疑是中国讼费征收制度的起点。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国民政府沿用《试办章程》(注:1914年《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规定:“讼费准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84条至第96条。”《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07)》第六节“讼费”,载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第3 辑),第27页。),直至1922年颁布《诉讼费用规则》。该规则几经修改而为中国台湾现行之“民事诉讼费用法”(注:《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第585—587页。)。
纵览1907年到1989年出台的各种讼费征收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诉讼标的之金额”作为收费依据的原理一直相沿不变,尽管称谓常常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以“诉讼标的”理论作为构建基础并支持其正当性的制度。
表2 “诉讼标的之金额”与中国讼费规则沿革:1907—1999
法令之所出和颁布时间
法令名称
讼费计算依据
清政府,1907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
“诉讼物之价值”
国民政府,1922
民事诉讼费用法(原或名;诉讼费用规则)
“诉讼标的之金额价额”
苏中第二行政区,1943
征收诉讼费用暂行办法
“诉讼标的价额或金额”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6
各级法院状纸与讼费暂行办法
“诉讼标的之金额或价额”
上海市人民政府,1954
受理民事诉讼及非讼案件征收费用暂行办法
“诉讼价额”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80
审理经济案件收取诉讼费用暂行办法
“诉讼争议标的额”
最高人民法院,1984
民事诉讼收费办法
“争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
最高人民法院,1989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
“争议价额或金额”、“争议金额”
中国最初从日本引进讼费制度,而日本的讼费制度又来自德国。“诉讼标的”是贯穿德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的一个关键术语:它是可以折合为金钱的一种诉讼请求,是确定法院管辖的依据之一,是起诉的必备要件和诉状的必备内容,当事人与同一“诉讼标的”存在利害关系是共同诉讼的必备条件(注:德国《民事诉讼法》,谢怀@①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53、59条。)。当然, “诉讼标的”在德国又是法院征收讼费的依据(注: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原告在诉状中“必须准确地提出求偿价额,不过在人身伤害案件,(原告)所提出的诉讼价额只是最低赔偿额。求偿价额至关重要,它决定诉讼价额、诉讼标的、 法院收费和律师收费的数额。 ”参见stephen o‘malleyand alexander layton,european civil practice (1989),p.1298.)。
德国的“诉讼标的”规则是按照一种令人费解的理论构建的,这个理论包括一组互相缠绕的抽象概念。按照德国的学说,债的内容为“给付”,债的实质是“请求权”,“债”、“给付”和“请求权”都有与之对应的“标的”,诉讼请求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对应,故诉讼标的是随着诉讼而延伸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注:参见陈荣宗《民事诉讼程序与诉讼标的理论》(1977),第326—449页;石子泉、杨志华《民事诉讼法释义》(1987),第3—4页;史尚宽《债法总论》(1978 ), 第223页。)。
民国时期的法律全盘继受了“债的标的”和“诉讼标的”理论(注:1929年国民政府《民法典》以“债的标的”作为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名称。按照该民法典草案,债之标的就是概括称为“给付”的债务人作为或者不作为。按照学界理解,债的标的即为德国民法上“债的内容”(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1930 年, 国民政府《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又规定,“诉讼标的”为诉状必备之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1949年废除了国民政府的一切法律,但是并没有生成足以替代或者同化德国法学的方法和理论-在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背后,法学思维的基本模式仍然与德国法学一脉同宗。
然而何为“诉讼标的”,在法律解释上歧见纷纭,实为“剪不断,理还乱”的难解之结。其一,当事人诉讼请求有无民法上的请求权作为支撑,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审查的问题,而不是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二,诉讼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给付请求权不能涵盖所有的诉讼形态。例如:确认之诉通常是要求法院确认物权或者身份权,形成之诉通常是主张民法上的形成权,而不是主张给付;其三,一项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可以产生多种诉讼法上的请求权,从而出现请求权竟合的现象。例如,原告因手表为被告盗窃而产生的请求权有四种: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所有权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基于债法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基于占有人身份的回复占有请求权。原告因手表被盗而产生的请求权是否在诉讼法上构成四个诉讼标的(四个请求权)?原告能否就同一事实,先后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法院是否应当针对同一事实进行四重判决?所以,诉讼法学认为:诉讼标的与债的标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注:陈荣宗:《民事诉讼程序与诉讼标的理论》,第326—449页。)。
形而上学是一种自我膨胀的学说。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总是衍生出更多形而上学的问题。走出形而上学困境的一个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陷入这些问题之前,用一分钟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如果缺少债的标的、诉讼标的,民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是因此崩溃,还是因此摆脱一个消耗大量智力的误区?如果是前者,那么继续讨论;如果是后者,那么忘掉什么是债的标的和诉讼标的。
三、结论
(一)法律移植的批判
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1980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讼费制度中,可以辨察出一脉相承的轨迹:1907年之后,按照“诉讼标的之争议金额”收取讼费的规则迭经政局的巨变而依然故我。为什么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迥然不同的政府都接纳了清政府最先从日本引进的讼费制度?
在本世纪初,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华法系危在旦夕,清政府匆匆忙忙推出了规模宏大的法律移植工程,试图通过汉化一批外国法律而迅速修复本国的法律断层。结果,中国法律在脱离固有法的封闭体系之后,立即步入了外来法-一个陌生的、更难用本地经验对之改良和批判的封闭体系,从而自我限制了发展空间。
清末法律移植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来法律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效应。近一百年来,中国重大的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一定范围的法律移植。从清朝末年的维新变法到民国的典章制度,从1949年之后引进苏联模式的行政法律体系,到80年代之后形成的那些试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法律,尽管历次变革的内容并不相同,但是求助于法律移植来实现雄心勃勃的社会变革目标,却是相沿不易的思路。法律移植的深层理念是:传统秩序难以容纳社会进步,必须引进外国法律以推陈出新。然而,最近亚洲开发银行考察了中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从1960年到1995年期间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19世纪末移植了西方法律,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西方引进的法律一直被束之高阁,它们仅仅是在纸面上生效而没有实际效用;在亚洲经济起飞过程中,扮演主角的不是移植而来的法律, 而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注:k.pistor,p.a.wellons,the role of law and legal institution in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1960—1995(1997)。)。可见,声称法律移植(特别是体系化的法律移植)能够产生正面效应的说法,是一个经过100多年实验还没有被证实的假设。
清末法律移植之后,中国法学始终围绕着引进、临摹、诠释和传播原地踏步,缺乏吸纳、批判和改良外来法律所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思维,故本世纪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律、法学和方法始终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某规则所以如此,因为它来自大陆法系,中国属大陆法系,故不得不如此。”这成了中国法律界的一个口头禅,它可以用来放弃思考、阻断讨论和漫不经心地回答一切质疑。实际上,中国法律界一直满足于“中国是大陆法系”的万能解释,而不再费心思考:中国真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真的可以作为一种传统而移植到中国?真的存在一个恒定的、一元化的大陆法系?美国法学家弗兰克(jerome frank)在本世纪3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法律能否从幼稚到成熟,取决于法学家能够摆脱教条而产生丰富的想像力,就此而言,美国只有霍尔姆斯大法官一人是已经“成年”的法学家(注:转引自richard polenberg, the world ofbenjamin cardozo(1997),p.159.)。当中国成为法律继受国家之后,法学从幼稚到成熟的途径就更加艰难,语言本身构成了接近第一手理论、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的障碍,更不用说产生创造性思维了。我想,只有当中国法律界摆脱对大陆法系类似“恋母情结”的依赖之后,中国自己的经验、智慧和创造精神才能进入法律。
(二)讼费征收和法律的虚设与增生
弗里德曼教授认为:法律由文本到制度运行的过程,犹如水流经过布满洞眼的浇花水管,漏水本身是一种平衡(注:弗里得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05页。)。
然而在中国,比“漏水”更能说明法律文本和制度运行之差异的事实来自两个极端:法律的虚设和增生。山西运城地区的“渗灌池”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法律虚设的例子:90年代,当地政府命令农民建造“渗灌池”-一种可以代替浇灌的技术,像民法一样,这也是一门来自德国的学问。农民明白当地的降水量、土质都不适宜运用“渗灌池”,但是他们又不敢违抗政府的命令,于是就用最低成本在田间构建了一些供官员参观的水池:没有用水泥封闭池底,没有敷设地下水管,因此这些水池既没有蓄水功能,也没有灌溉功能,它们唯一的功效就是维持一个假象,使参观者产生错觉,似乎这里真的发生了值得称道的变化。有一些法律确实就像这种“渗灌池”,它们只是在纸面上存在而从来没有付诸实施,从而根本不会出现弗里德曼所说的“漏水”现象。
弗里德曼忽略了法律由文本到制度运行的另一个极端:法律在运行过程中,也可能呈现一种类似细胞异常增生的法律扩张。法律的异常增生突破了自身的正当性而变成了限制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中国的现实可以提示许多法律增生现象:设立名目繁多的收费,编制捕捉“无效合同”的法网、实行无所不至的证券、评估、拍卖、商标、专利业务许可制度,都是自上而下层层加码,愈演愈烈的法律增生。这里,讼费征收只是法律增生的一个小小的构成部分。当我们抱怨“有法不依”的时候,常常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事实即法律增生。法律增生和“有法不依”是一对孪生兄弟。
就文本规则而言,讼费征收从移植到本地化的主要变异是:非讼程序萎缩、讼费救助弱化,而按“诉讼标的”收取讼费的范围则大大扩张。就法律实践而言,收取讼费的规则从来没有出现“执行难”,而是执行过火:法院“超标准、超范围”收取讼费成为1998年整肃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全国法院总共“清退超标准、超范围收费827 万元”(注:肖扬:《坚决清除司法人员腐败,努力维护司法公正》,1999 年1月30日《人民法院报》。)。究竟有多少“超标准、超范围收费”,这恐怕是一座永远不会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
(三)讼费征收和政策判断
讼费征收是一个与“诉讼标的”理论完全无关的政策判断问题。除了政策判断,没有任何原理可以支持或者否定讼费征收规则的正当性。因此,评价《‘89诉讼收费办法》,探讨改善途径,只能以政策判断而不是以某种理论作为基础。
政策判断之一:讼费征收和诉讼成本的合理分担
《‘89诉讼收费办法》为时10年的实践证明:让法院收取讼费而补贴预算不足是不恰当地转移了国家本来应当承担的“审理成本”。其代价不仅是诉讼当事人承担过高的诉讼成本,而且是损害司法公正。因为,随着司法机关产生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随着司法权力被用于追求商业利益,司法公正必然被扭曲。
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即使一个政权决心不惜代价地实现司法正义,它将这种决心变成现实的能力仍然受到资源限制:法官、法庭是有限的,维持或者增加法官、法庭的财政预算也是有限的。
《‘89诉讼收费办法》无意识地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审理成本”和诉讼成本的分配:其一,本来应当由国家承担的“审理成本”部分地转移给当事人,特别是“争议金额”大的当事人;其二,诉讼成本从“非财产案件”转移到“争议金额”大的“财产案件”,换言之,“争议金额”大的“财产案件”的当事人在向“非财产案件”的当事人提供补贴,而“争议金额”大的当事人多是企业和事业单位,“非财产案件”的当事人多是个人。
即使从审判中获得较多经济利益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较多的“审理成本”,按照“争议金额”征收讼费也未必合理:其一,“争议金额”只是一种诉讼请求,当事人从判决获得的利益未必与“争议金额”相当,而按“争议金额”预交讼费只能是阻遏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诉讼请求。其二,“争议金额”大的案件未必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法官的关注不应当为“争议金额”大小所左右。其三,“争议金额”较大的案件通常涉及企业,讼费列入企业成本,企业负担的讼费越多、纳税越少;诉讼成本向企业转移得越多,企业的竞争实力越差。其四,讼费最终是败诉方承担,而真正从诉讼获益的胜诉方恰恰没有分担“审理成本”。
可以选择的改善措施是:对于起诉、反诉和上诉,象征性地预交少量讼费;在法院最终裁定赔偿金额时,调整败诉方负担的讼费;对于从最终判决获得一定数额经济利益(如50万元以上)的胜诉当事人课以一定比例的税费。
政策判断之二:讼费征收和救助贫困当事人
向贫困当事人提供救助是司法公正应有之意。当然,国家没有义务为一切贫困当事人提供免费的诉讼,但是在特定情形下,诉讼成为当事人解决争议的唯一途径或者为穷尽一切非讼途径之后的选择,那么拒绝为贫困当事人提供审判服务就背离了平等保护的宗旨。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有胜诉希望而无力交纳讼费,法院恐怕不能因为没有收到讼费而拒绝审判。向贫困当事人提供讼费救助是司法职能的内涵之一,当然,法院也应当有灵活选择讼费救助措施的余地,诸如减免、缓交、分期交付和由第三人提供担保等等。《民事诉讼法》和《‘89诉讼收费办法》欠缺任何可行的讼费救助规则,欠缺允许当事人就讼费救助问题进行争议的程序,这是值得反省和有待改善的。
在美国,讼费救助甚至成为一个宪法问题。一个贫困当事人对康涅狄克州提起违宪诉讼,声称:州法院就民事案件收取50美元受理费,自己无力交纳,因而无法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故州政府剥夺了他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哈兰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当诉讼成为解决争议的唯一合法途径时,因为当事人无力交纳讼费而拒绝审判是违反正当程序的。“法院垄断了解除婚姻关系的途径,离婚当事人必须求助于法院,故宪法正当程序禁止法院仅仅因为当事人无力支付案件受理费而拒绝解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注:boddie v.connecticut,401 u.s.371(1971)。 )在另一个原告诉州政府违宪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如果亲子鉴定是原告对抗州政府的主要证据,那么,原告因没有支付能力而丧失通过亲子鉴定获得证据的机会是违反正当程序的(注:little v.streater,452 u.s.1(1981)。)。
政策判断之三:讼费征收和司法资源的有效使用
滥讼无端消耗司法资源而陷他人于讼累。但是,“非财产案件”每案收费30—100 元和索取赔偿按“争议金额”加征讼费的规则恰恰是同时走到了放任滥讼和遏止正当诉讼两个极端。一方面“非财产案件”的低额收费根本不能督促人们在起诉前三思而行,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恶意的诉讼毫无障碍地涌向法院。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希望通过诉讼而获得赔偿的当事人或者畏于高额讼费,或者畏于低额法定赔偿金(例如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医疗事故的最高损害赔偿分别是6千元和4千元(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1990),第26条;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1989),第30条。))而放弃诉讼,与此同时,法官也失去了通过审判而表达社会关注的机会。
讼费只是对滥讼构成一道较低的门槛,让人入门之前略微留意脚下。比事前防范更有效的措施也许是事后制约,例如:将恶意诉讼作为诉请民事损害赔偿的理由,判令恶意挑讼一方承担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和其他损失;确定胜诉原告承担讼费-假如被告承认债务或提出与判决大体一致的和解建议,原告仍提起不必要的诉讼。
在中国现有体制之下,法院的实际能力相当有限。夸张审判的作用,期待法院处理力所不及的事务,只能是徒生无益诉讼而浪费司法资源。在责备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抱怨法院判决成为无法兑现的“白条”时,可能也需要考虑:法院在现有体制下能否生成公正审判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哪些困难是法院本身无法克服的?在转型时期,许多争议(如破产、银行债务、企业兼并)牵动的不仅仅是诉讼当事人,而且是整个制度性结构。美国的富勒教授曾经指出:法院难以审理“多极”争议。“我们不妨把这种情形想象为一个蜘蛛网。碰触任何一根蜘蛛丝,所产生的张力都会通过一个复杂的传导模式而扩散到整个蜘蛛网;再次碰触同一根蜘蛛丝,不是重复产生原有的张力,而可能产生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张力。”(注:lon l.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adjudication (审判的形式与局限),92harv.l.rev.353,1978.富勒教授试图运用以下实例说明法院审理“多极”问题面临的困境。一名妇女对她收藏的大量油画留下遗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平分”油画。但她没有指明任何一幅油画的确切归属。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幅油画本身无法“平分”,而“平分”全部油画牵涉每一幅油画的归属, 确定任何一幅油画的归属又牵动全部油画的“平分”。 在这种情形下,富勒认为:“任何一位审理本案的法官,只能求助于调解,或者古典的遗产争议处理办法:让长子平分财产,让次子首先挑选财产。”)将那些本来只能通过行政裁决、当事人调解和协商处理的案件推向法院,只能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和“审理成本”。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政府机构主持的独占性仲裁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修改一些程序性规则,扩大法院的权力,将大大节约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和审理成本。例如:抵押权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抵押物而不必经过诉讼;法院可以采取包括强制拍卖在内的执行措施,而不必委托拍卖行;法院可以根据鼓励和解、遏止恶意诉讼、避免不必要诉讼的原则而裁定讼费、律师费负担。
北京大学法学院·方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