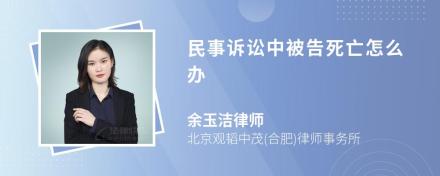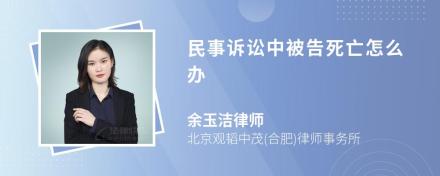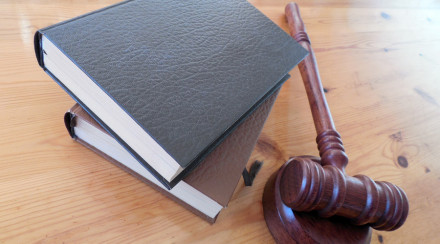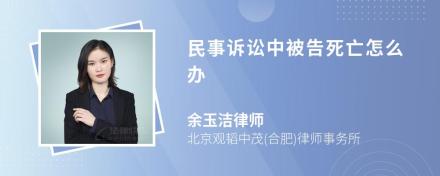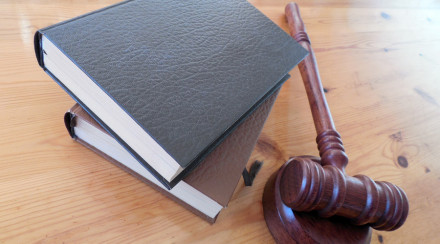摘要:《证据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心证公开制度,但文章认为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心证公开是自由心证的客观化机制;二心证公开是辩论主义的补充并与阐明制度、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相连接。《证据规定》规定的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在内容上还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证据规定》确立的阐明制度尚不彻底。文章认为要实现心证公开制度的制度功能,必须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定》中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和阐明制度。
关键词:心证公开 判决理由的论证 阐明权 举证时限
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否定,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而言,它能够充分调动裁判者司法认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和司法正义的实现,故此,为多数西方国家所认可。当然,自由心证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实现了由传统自由心证向现代自由心证的嬗变。传统自由心证过分强调裁判者的主观能动性,背离了自由心证之促进发现真实的目标,并一定程度地导致了司法擅断;现代自由心证以实现裁判者心证的客观化为己任,在尊重裁判者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强调对裁判者心证的制约。
法治之路开始较晚的中国,无须重蹈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曲折,可以直接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法律制度,为我所用。确实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自由心证的制约机制。心证公开就是这样的制约机制之一。本文拟对《证据规定》中的心证公开进行分析,并力图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心证公开机制的合理建议。
一 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
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是立法者设立心证公开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证公开制度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以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为切入点,可以透视、分析心证公开与其他民事诉讼制度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性地分析心证公开制度,促使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的实现。事实上对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的不同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心证公开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和心证公开制度的基本内容。心证公开程序价值一元论者,只能在与其他某一个具体民事诉讼制度联系的基础上,一维地研究心证公开,不可能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心证公开制度运行的诉讼机制。在笔者看来,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心证公开是自由心证客观化的机制。心证公开能够为学者和立法认定为自由心证的客观化机制的重要原因在于:
(1)公开是监督国家权力行使的重要方式。任何权力在其天性上都有不受约束的特点,都有一直行使到其最后的界限为止的倾向。公开是监督国家权力行使的有效方式,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建立都是和公开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公开和公正是一对孪生兄弟,离开了公开,公正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和多大的范围内存在,彼成疑问。事实上,审判公开制度已被我国民事诉讼确定为基本的民事诉讼制度。从心证公开包括的内容来看,心证公开与审判公开有一定的对应性。当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最初设置审判公开制度的目的在于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教育和震慑,并籍此实现扩大诉讼功能、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随着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深入,人们逐渐赋予审判公开制度其本来应有的内容和含义。
(2)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心证过程的公开能够促进认识的客观与正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识活动不是按照原子论的模式进行的,认识过程与整体论之间有一定的契合性。认识因素与认识结果之间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具体明确的。“促使人们对证据作出反应的因素对认知者而言并不十分透彻,甚或不易以命题表达。在证据和结论之间似乎存在着宛如跳跃一般的中断。”[1]判决理由的论证是心证公开的重要方式,通过判决理由的论证,证据与裁判者司法认识结果之间的联系变得具体、清晰起来,证据与结论之间的空隙得以填平。同时在这样的论证过程中,裁判者也有可能修正已经形成的司法认识结论,并使司法认识的结果更加客观。“即使是最经验丰富的法官,在试图清楚、准确地表达作出某种判断的原因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改变自己的想法。”[2]
值得注意的是判决理由的论证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英美法系法官对判决的论证涉及的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涉及事实认定和对证据证明力的评价问题。关于证据的证明能力、证明责任的分配、推定及其效力均是法官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作为判决论证的内容。事实认定专属于陪审团,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无须给出具体的理由。在论证的主体方面,英美国家的判决论证不是以审判庭的名义进行论证,而是各个法官根据自己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理解,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论证。同时判决理由的论证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有不同的意义。初审法院也有论证判决理由的义务,但上级法院判决论证在整个司法制度中的意义更加深远。初审法院裁判论证的主要目的是约束裁判权的行使,保证个案正义的实现。而上级法院对裁判的论证具有超出实现个案正义的意义和价值,上级法院就判决理由的论证可以作为法律的渊源,并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产生直接适用的效力。这种情况根源于英美国家的判例制度。
第二 心证公开是辩论主义的补充,并因此与辩论主义发生联系。[①]由民事诉讼的对象决定,现代各国一般都把辩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3]我国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的完善,实际上以西方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作为基本的参照,并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对辩论主义的移植。为保证辩论主义在实质上不平等当事人的之间实现,各国民事诉讼法,尤其是未采律师强制代理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都把阐明权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补充因素予以规定。其立法的基本原因是:没有阐明权民事诉讼制度包括辩论主义便不能按照他们预定的目的运行。[②]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中,阐明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1)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充分时,使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变得充分;(2)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适当时,法院促使当事人作适当的声明和陈述;(3)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4]阐明权虽然是法院的一项职权,但它和其他的国家权力不同,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没有任何强制意义。阐明权行使的根本目的是法院将其司法认识的信息告知当事人,以便于当事人在充分了解案件信息的情况下,平衡自己的民事程序利益和民事实体利益,理智地实施诉讼行为。同时这样的信息告知,也使当事人预知法院司法认知的结果,防止法院对当事人的突袭裁判,增加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信任。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有学者不直接称其为阐明权,而是称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争点整理。可以看出,法院对当事人的信息告知实际上是其就司法认识诸环节的心证向当事人所作的公开。具体包括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当事人应主张的案件事实、应提供的证据、裁判者当下就争议事实的心证程度、哪些证据可以影响裁判者的心证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阐明权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具有不同的意义。英美法系国家不太注重所谓的阐明问题,民事诉讼理论中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在英美国家当事人获取案件充分信息依赖的不是法院的职权,而是对方当事人,使用的手段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略有差异。在诉答阶段当事人通过明确诉答内容的动议(Motions to Clarify Pleadings)获取完整的案件信息;在审前阶段通过Discovery程序获取充分的案件信息;在审判阶段主要通过对抗制的交叉询问实现对方当事人的信息获取。[5]但英美国家的当事人在裁决作出之前的审理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手段以获取与裁判者心证内容有关的信息。制度差异的深层原因是对抗制和对抗制之下的个人主义文化,英美国家的文化中更多地强调的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努力,依赖国家和政府在英美国家的人看来是耻辱的。[6]同时相对于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而言,英美国家的诉讼具有更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神秘主义的体现之一就是陪审制。陪审团就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不需要说理的,陪审团裁判的正当性不是来自其理性、逻辑,而是来自其自身。
二 《证据规定》确立的判决理由的论证与公开
《证据规定》第79条和第64条最后一句涉及的是判决理由的论证与公开制度。学者们一般认为《证据规定》确立的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就是心证公开制度,而且心证公开制度与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可以在相互置换的意义上理解。“各国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判决理由的说明制度,即心证公开,以保证裁判的客观性。”[7]在笔者看来,心证公开以其涉及的内容为标准,可以分为心证理由的公开和心证结果的公开;以其公开的时间为标准,可以分为心证过程中的公开和心证形成后的公开;以其针对的对象为标准,可以分为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论证主要针对的是裁判者心形成的原因,其发生于心证已经最终形成后的时间阶段。这样,判决理由的论证与心证公开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判决理由的论证属于心证公开的一种方式,是心证公开的下位概念。
判决理由论证制度确立的时代背景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司法背景是司法人员对待判决书的态度,还没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判决书的写作仍然受计划经济观念的支配,其表现形式就是“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当事人质证与法官采纳证据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以及据以采纳证据的理由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直接对案件事实加以认定,对于作为判决的理由,更不作具体、详实的分析、阐释”。[8]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信赖和接受,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度。公信度的降低伴随着上诉案件、再审案件、执行案件的增加,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加大了司法资源的短缺与案件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
适应时代转变的需要,《证据规定》确立了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但从判决理由的论证与心证公开相联系的角度看,《证据规定》确立的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尚有进一步完善必要。具体表现在:
第一,判决理由论证的内容还不完整。《证据规定》第79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在证据法当中反映证据是否采纳的范畴是证明能力和证据资格。《证据规定》第64条最后一句针对的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但司法裁判的作出必然包括以下几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和内容:法律规范的选择、要件事实的确定、证据资格的认定、证据证明能力的判断、争议事实的判定、法律规范的适用、裁判结论的形成。以上任何一个环节中出现裁判者的任性或者偏见,都会导致裁判合理性的丧失。判决理由的论证作为心证过程的再现形式和赋予心证结果以正当性、合理性的手段,理应包含以上诸环节。
同时《证据规定》第79条第2款规定,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证据资格问题的论证范围受当事人的制约,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不仅可以直接确认其证明能力,而且可以不再裁判文书中表述。我们认为《证据规定》的上述精神不符合现代民事诉讼法理。诚如前文所述辩论主义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采用的基本原则,但辩论主义也有其明确的范围限制。一般说来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不能采用辩论主义,而只能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在一般案件中,辩论主义也不是对所有的案件事实有一体适用性。下列事实即不能适用辩论主义,而需要采职权探知主义,由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并予以调查:(1)程序事实;(2)间接事实;(3)辅助事实或者补充事实。辅助事实是指与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有关的事实。这样依据辩论主义关于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调查与确定,法院不受当事人主张与否、争议与否的限制和约束。即是说,不管当事人的态度如何法院都应当依职权予以审查。对于证据的证明能力的审查各国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不对证据资格问题预先规定,而交由法官自由采量;英美国家的法律对证据资格预先作出强制规定,并由法官先行审查。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采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法律仅仅对少数、特定情况下的证据的证明能力予以限制或者剥夺,大多数证据的证明能力均由法官自主采量。对于证据的证明力现代各国均采取由事实裁判者自主采量的方法,我国也不例外。裁判者对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审查时,在法律由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时,则应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作出判断。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自由采量,裁判者的审查与判断均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关。
第二 缺乏保证判决理由论证实现的诉讼机制。《证据规定》第79条和64条把判决理由的论证设定为法院的义务,使用的概念是“应当”。但《证据规定》没有设置违背该法定义务的相应的制裁措施,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立法习惯造成的。法治历史较短的中国社会治理中,一直比较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不重视也不愿意采用法律规制的手段。在中国特别是前法治时代的中国,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模糊,法律规定中充斥着大量道德信条。法与情不分、法与礼不分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特点。法律可能为人们设定许多具体的义务,但大多数情况下,又忽略了规定违反法律义务的制裁措施,法律义务的履行寄托于人们的道德自觉。对违法者的制裁与其说是依靠的法律,不如说是依靠的情、礼和道德,中国古代的判词中的主要内容不是法律,而是情理与道德。[9]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模糊在程序法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民事诉讼法为法院或者法官规定了很多职责,但对法官违背职责的制裁措施却鲜有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也未规定违反说理义务的制裁措施,但台湾地区的学者却对违反判决论证义务的制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这种学理研究对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台湾学者认为判决理由不备不仅可以作为当事人上诉的理由,上级法院也可以据此废弃原来的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10]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将判决理由不备作为发回重审的基本事由。首先这一做法与《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3项的规定具有一致的立法精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3项的规定,二审法院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不清不仅包括事实认定结论的模糊,也应当包括判决理由的缺乏。其次,将判决理由不备的案件直接发回原法院重审,比上级法院直接改判,更能强化审判法官的责任心和义务意识。最后,发回重审和错案追究制相结合,能进一步提高对审判法官的约束力,促进判决理由论证义务的履行。
另外,在我们国家还不存在如英美国家的激励裁判者对判决理由论证的激励机制。在英美国家激励法官认真论证和撰写判决理由的激励机制主要有:(1)判例制度。英美国家法官在法律理由中提出的法律意见对以后的案件有约束力,论证充分、有力的判决也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被引用,甚至会成为上级法院审判案件的重要参考。判决书的撰写者也会因为其判决的论证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证判决对法官们有较大的诱惑力;(2)判决书的署名制度。英美国家法官不仅就多数意见可以撰写判决书,而且少数意见的持有者也可以就自己的观点撰写判决书。在多数意见的持有者当中,如果其法律理由不同,则他们可分别撰写判决书。判决书都是以法官个人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以审判集体的名义,更不是以法院的名义作出。(3)判决书的发表制度。英美国家的法官撰写的判决书一般都能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中发表,容易发表的原因不在于法官的水平高低,而是因为人们对法院的判例和判决书的重视。在这些国家法院的判决是法律研习人员学习的基本素材,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11]
在我国不存在激励法官认真撰写判决书和判决理由论证的宏观社会背景是制定法的法律体系,法院的判决书也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判决书的基本意义和价值表现为仅仅在于它是法院案卷材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合议制的具体运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法官论证判决理由的热情和激情,心证公开与合议制并不矛盾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少数人的意见不仅不能作为裁判的意见,而且不能公开,其最大的意义是记入合议庭评议笔录。这样,合议庭少数意见的持有者的观点,不仅不能公之于众,也无法为当事人知悉。此时,这些少数意见的持有者还能有论证判决理由、撰写判决书的热情吗?其次,我国判决书采用的审判组织集体署名并加盖法院印章的制度,而实际判决理由的具体论证和判决书的撰写,只能由某一具体的法官来完成。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心证可能是多数裁判者的心证,[③]但将这种心证形成过程和心证结果付诸文字却不可能依靠多数人的合力来完成。来自司法实践方面的考察也能够证实这一结论。这样判决理由的论证、判决书的撰写就与判决书的署名一定地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使得论证判决的法官并不比其他法官得到更多的回报。
在判例制度难以建立,不能强制社会、公众重视法院判决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改革司法的内部环境,一定地建立判决理由论证的激励机制。主要的做法就是改变合议制的运行方法,许可少数意见公开;同时改革判决书的署名制度,采取判决意见的享有者与判决书著作权的享有者分离的做法。具体运行时注意两点:一是判决书必须详细地说明合议庭各组成人员的观点和合议庭的裁判结果,以此回应判决理由的论证是心证过程再现的法理,并体现对合议庭组成人员工作的尊重。二是裁判文书的尾部著明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名单,并加盖法院的印章,以此回应审判的职务行为性质,并体现法院裁判的权威。三是在裁判文书的尾部著明判决书撰写者,以此体现对撰写判决书的法官的创造性劳动的尊重。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性地建立判决书的汇编制度。判决书由高级别的法院编辑出版,法官撰写的、为高级别法院编辑、采用的判决书,可以与法官在其他学术报刊上发表的科研文章同等对待,并作为以后工作评定的重要参考内容。
三 心证形成过程中的公开
心证形成后的公开,作为心证过程的再现和裁判获得正当性资源的手段,实际上也是法院对当事人的一种信息告知形式。通过这样的信息告知,当事人不仅能够了解法院裁判的结果,还能够洞悉法院裁判的原因。裁判结果正确、论证合理充分的判决,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但这种信息告知是一种事后告知,发生在审判程序终结时。当事人在对法院的心证结果或者心证原因有异议的情况下,无法在当下的程序中提出这种异议,只能寄希望于上诉程序或者再审程序,采取事后救济的方式。这种情况在减损判决理由论证的促进当事人信赖之功能的同时,也无助于司法成本的减少和司法资源的节约。而裁判者的事先告知却能够克服以上弊端,并能够使当事人在了解充分的案件信息的基础上,平衡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及时实施诉讼行为。可以说,相对于信息的事后告知而言,事先告知和程序中的告知更加重要。为此大陆法系各国均十分重视心证过程中的公开,并赋予其诸多程序价值和程序意义。大陆法系的学者普遍认为,裁判者过程中的心证公开首先能够防止法院对当事人的突袭裁判,增加当事人对裁判的信赖。“充实言词辩论之程序内容,俾能提高当事人对裁判内容之预测可能性,并经由说服当事人且使当事人对裁判表示信服之过程,赢得当事人对法院之信赖。”[12]其次,能够促进案件事实的发现。通过法院的信息告知,当事人能够及时了解裁判者的心证程度,在此基础上可以不失时机地收集、提供能够影响裁判者心证的证据,促使裁判者的心证结果更加客观。当然此种情况下的真实不同于一般的客观真实,当事人在平衡其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基础上,自主地决定是否提出证据以及提出何种证据。因此该真实是存在于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调和点上的真实,是兼顾防止突袭裁判之目的的真实。
《证据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证据规定》第35条规定:可以说《证据规定》一定程度地建立了心证形成过程中的公开制度,学者们一般是从阐明权的视觉理解心证过程中的公开。但《证据规定》确立的心证公开还仅仅局限于诉讼的开始阶段,没有贯彻于诉讼的全过程,特别是游离于法庭审理过程之外。心证的公开没有也不可能包含裁判者心证的全部内容,无法全面践行防止突袭裁判之功能。按照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邱联恭的理解,法院对当事人的突袭主要包括:(1)认定事实的突袭。未使当事人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充分认识、预测法院所要认定之事实或该事实之具体内容,致当事人在未能就不利于己之事实为充分攻击与防御之情况下,受法院之裁判。(2)推理过程的突袭。未在言词辩论终结前,使当事人充分预测法院就某事实之判断过程,致当事人在未能适时提出充分之资料或陈述必要之意见等情况下,受法院之裁判。(3)促进诉讼的突袭。未适时使当事人预测法院之裁判内容或判断过程,致当事人在不及提出资料或意见,以避免程序造成劳力、时间、费用之不必要支出或不该有之节省等情况下,受法院之裁判。[13]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证据规定》中的信息告知实际上限制在法律适用的范围内。人民法院就法律关系或者法律行为的效力向当事人为的告知,是民事实体法律规范的告知。人民法院就举证责任向当事人为的告知实际上是证明责任规范的告知。在我国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规范实际上一种法律规范,并属于民事实体法的范畴。[14]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信息告知并未涉及裁判者所要认定的事实,也没有涉及裁判者的心证程度,与防止法院突袭裁判的要求相去甚远。
完善心证形成过程中的心证公开制度,就应使心证公开全面体现于审判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法庭审理阶段。笔者认为在将来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明确增加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信息公开义务。同时为保证这样的义务能够全面实现其防止裁判突袭,促进人民对司法信赖的功能,应进一步健全举证时限制度。《证据规定》将举证时限制度确立为审前程序的一个内容,这样即使法庭审理阶段裁判者公开其认定的事实以及对争议事实的心证程度,当事人也无从提出新的攻击与防御方法。信息公开的促进发现真实,防止突袭裁判的功能不能充分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和英美国家在举证时限方面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在英美国家,举证时限是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个附随内容,并存在于证据开示制度中。因此举证时限在英美国家的民事诉讼中属于民事庭前程序的组成部分。采用这种制度的背景是英美国家采用陪审制和集中审理的制度,陪审制和集中审理要求双方在庭前必须对对方的攻击与防御方法有充分的了解,并不允许任何一方在法庭审理阶段突袭对方。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一般把举证时限规定在言词辩论终结时。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2条(1)规定:当事人各方都应该在言词辩论中,按照诉讼的程度和程序上的要求,在为进行诉讼所必要的与适当的时候,提出他的攻击与防御方法,特别是各种主张、否认、异议、抗辩、证据方法和证据抗辩。同法第2款规定:声明以及攻击和防御方法,如果当事人不预先了解就无从对之有所陈述时,应该在言词辩论前,以准备书状通知对方当事人,使对方当事人能得到必要的了解。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举证时限制度与我国的诉讼法律文化以及其他的诉讼制度有天然的亲和力,故此,在借鉴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阐明权制度的同时,也应当一并采用大陆法系的举证时限制度。如果采大陆法系的阐明制度,却使用英美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必然导致法律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并最终影响法律制度功能的实现。
--------------------------------------------------------------------------------
* 作者简介:赵信会 山东经济学院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①] 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心证公开是对辩论主义的限制,是辩论主义的例外。参见[日]兼子一等。条解民事诉讼法[M].东京:弘文堂。1986.3.10.
[②] 当然关于阐明权的根据在国外有不同的观点,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有:(1)谋求纠纷的妥当解决说,该说认为通过法官的阐明可以使当事人充分举证、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纠纷的妥当和正当解决。其主要的倡导者为日本的石渡哲。参见石渡哲。诉讼程序形成中法院与当事人的作用[A].新堂幸司讲座民事诉讼法(四)[M].东京:弘文堂。1985.125(2)程序保障说。该说认为阐明权的根据只能是保障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机会,实现程序保障。代表人物是日本的吉野正三郎,参见吉野正三郎。诉讼审理中法官的权限与责任[J].立命馆法学。1988.1.(3)防止突袭说,该说认为阐明权最根本的依据在于防止法院对当事人的突袭,赋予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机会只能防止当事人之间的突袭。参见沈冠伶。论民事诉讼法修正条文中法官阐明义务与当事人之案件解明义务[J].万国法律。2000.6.除此以外还有确保实质的当事人平等说和辩论主义补充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阐明权的根据首先是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其次是程序保障和防止法院突袭裁判。参见熊跃敏。民事诉讼中的法院释明:法理、规则与判例[J].比较法研究。2004.6.71.
[③] 当然司法实践中采取的主审法官制度,也在实际上冲击多数裁判者的心证形成,并使合议制流于形式。尽管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但由于司法资源与纠纷数量不断提高的趋势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且目前我国的替代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完善、发育还充分,合议制形式化还会在相当长的史时期内存在。
--------------------------------------------------------------------------------
参考文献
[1] [美]米尔建 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李学军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8.
[2] [澳大利亚]斯贝格尔曼。人权 法治与判决书推理[N].人民法院报。2003.11.24.
[3] 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4] 张卫平。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J].法学论坛。2004.5.15.
[5] Jack H. Frideenthal, Mary Kay Kane,Arthur R. Miller, Civil Procedure, West Publishing CO.1996.
[6] 赵信会 李雁。美国文化与比较民事诉讼程序[J].陈刚。比较民事诉讼法(2003年卷)[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李祖军。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J].现代法学。2004.4.106.
[8] 毕玉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514.
[9] 梁治平。寻找自然秩序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0] 参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研究会。民事诉讼法研讨(四)[A].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
[11] 苏力。判决书的背后[J].法学研究。2001.3.5——10.
[12] 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15.
[13] 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7.
[14] 陈刚。证明责任法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On the Publicity of the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in Civil Action
Zhao Xinhu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
Abstract: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Evidence for Civil Action primarily establishes our system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but the writer think the procedural value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at the publicity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is the objective mechanism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the other is that the publicity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is the supplement of adversary system and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explanation system and the argumentation system of grounds of decision. So ,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the publicity of the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 we must further improve the argumentation system of grounds of decision and explanation system in Provis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Evidence for Civil Action .
Key Words: Publicity of Discretionary Evaluation Argumentation of Grounds of Decision Right of Explanation Time Limit of Proof
原载于《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 司法制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山东经济学院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赵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