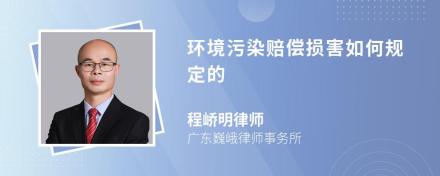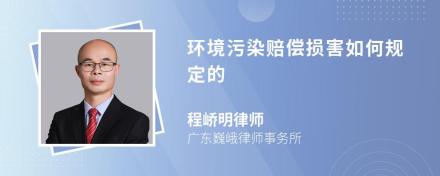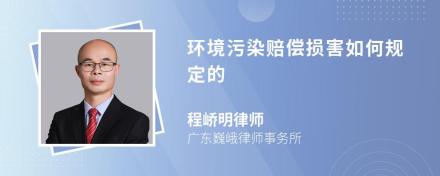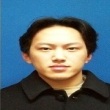关键词: 石油污染/海洋环境损害/海洋生态保护
内容提要: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完备的油污损害应对与事后赔偿机制,实践中对国际公约的适用、索赔主体、责任主体、油污责任限额、环境损害的认定标准等领域还存在许多争议。在油污损害赔偿类型方面,财产损害是传统侵权法律所规范的主要范围,也是争议最少的赔偿客体,对油污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认定目前则有不同看法。通过对环境要素的法理分析,可以认为海洋环境是一个含义最为广泛的概念,海洋环境侧重于整体,海洋资源是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资源体现了自然的经济属性,环境体现了自然的生态属性。如果以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外部条件的判断标准,海洋自然资源损害是海洋环境损害的基本要素,而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是对海洋环境的整体损害。对海洋自然资源的任何破坏都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但并非所有的破坏都会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所以,自然资源损害与生态系统损害是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两个方面。
理论上,环境损害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损害既包括由于对环境损害而引起的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害,也包括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狭义的损害仅指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是传统侵权法所规范的主要范畴,实践中争议甚少。本文探讨的环境损害是指对环境本身的损害。
一、海洋环境损害范围问题的提出背景
海洋石油污染按石油输入类型,可分为突发性输入和慢性长期输入。“突发性输入”包括油轮事故和海上石油开采的泄漏与井喷事故;“慢性长期输入”则有港口和船舶的作业含油污水排放、天然海底渗漏、含油沉积岩遭侵蚀后渗出、工业民用废水排放、含油废气沉降等。
作为中国近海常见的重要环境灾害之一,海洋溢油事故在过去几十年中未曾停歇。据统计,中国沿海地区平均每四天发生一起溢油事故。仅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管辖的海域就发生了733起船舶污染事故。[1]国家海洋局2009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中国全海域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依然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2]石油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有所不同,一旦污染水域,对海洋环境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后果。
现行有关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公约主要是由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并管理的一系列民事责任条约体系,主要由1976年、1984年及1992年附加议定书修订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油污损害公约》)与1971年《设立油污类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公约》(以下简称《基金公约》)及其1976年、1984年、1992年附加议定书组成。1969年《油污损害公约》第1条第6款规定,“污染损害”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不论这种溢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在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预防措施”是指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而由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由于该定义过于宽泛,对海洋环境自身损害的赔偿范围比较模糊,1984年,《油污损害公约》和《基金公约》各缔约方在该定义的基础上,明确“对损害环境的赔偿除这种损害造成的盈利损失外,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但该定义旨在因给个人、其财产以及因损害环境而给环境状况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做出赔偿,没有明确“环境损害”的概念,也不考虑其他形式的环境损害赔偿。各缔约方在1992年制定了《油污损害公约》和《基金公约》两项议定书,其中列入了1984年“污染损害”定义。
上述条约只是提出“污染损害”的概念,没有明确规定油污造成海洋环境损害的含义及其范围。一般认为“污染”是个含义广泛的词语,它通常被用来表述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由于人为的因素导致对自然界的改变;第二,表明具有法律含义的“损害”或“干扰”的界限。[3]在法律责任的认定中“,污染”和“环境损害”在概念上不能替换使用。“污染”一定是引起“环境损害”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污染”都能构成在法律上追究责任的“环境损害”。[4]对此,1993年欧洲理事会《关于对环境危险活动所致损害的民事责任的公约》明确说明“环境损害”和“污染”的区别,“如果危险活动的当事者能够证明‘损害’是由根据当地情况而可以容忍的‘污染’引起的,当事者可以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5]
为了使公约的缔约国在处理船舶油污污染赔偿时能有一个统一标准尺度和参考,1994年10月,国际海事委员会通过了《油污损害指南》。《油污损害指南》对污染损害的范围作了较为完整的解释,将赔偿范围规定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经济损失”(EconomicLoss),包括“必然经济损失”(Consequential Loss)和“纯经济损失”(Pure EconomicLoss)。“必然经济损失”是指索赔人因油类污染造成有形的财产灭失或者损害而遭受的资金损失;“纯经济损失”是指索赔人遭受的并非由于上述有形的财产灭失或者损害引起的资金损失,受害者主要分布在渔业及其相关产业、旅游及其相关产业,还有少量与港口和航运相关地产业。“财产”是指索赔人依据所有权或者占有权而具有法律上认可的任何利益。在实践中“,必然经济损失”可以受偿“,纯经济损失”是否可以赔偿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只有是油污染本身造成的损失才可以得到赔偿,仅证明在损失与引起油污染的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另一部分为预防措施、清除及恢复费用。对于预防措施及清除费用的赔偿遵循的原则是:只要采取预防措施(包括清除和处理)和支付的费用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预防措施的费用应该得到赔偿。对于恢复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的赔偿原则是:环境损害赔偿(利润损失除外)应限制在实际采取的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此外,国际油污赔偿基金制定的《索赔手册》(Fund Claims Manual)也对赔偿范围作了细致的规定,可以接受的索赔有清洁费用和财产损失,必然经济损失和纯经济损失,以及环境资源的损失、咨询费用等。上述两个文件不是国际公约,仅可以理解为对《油污损害公约》及其议定书损害赔偿范围的专家解释,国际油污赔偿基金在其赔偿实践中也没有明确对环境损害加以赔偿的案例,因而在国际油污损害公约体系内,因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害是环境损害的主要赔偿范畴。
目前中国有关海洋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主要是1992年《油污损害公约》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诸多国内法。《海商法》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没有规定。《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95条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一)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六)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上述法律规定可以作为海洋环境损害索赔的原则性依据,但缺乏对海洋环境的含义及具体赔偿范围的界定。这种现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法规可依,对国际公约的适用、索赔主体、责任主体、油污责任限额、环境损害的认定标准、油污损害赔偿类型等领域还存在许多争议。
天津海事法院在2004年判决的马耳他籍“塔斯曼海号”溢油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该案中,大连海洋局提出的海洋沉积物恢复费用、潮滩生物环境恢复费用等海洋生态环境赔偿请求最终未获得大连海事法院的支持。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目前该案还在审理中。该案表面上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海洋生态价值的评估与证据问题,但实质上是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认定、损失估算标准等法律赔偿机制不完善所引起的困惑。所以,本文从环境要素的法理分析出发,探讨海洋环境损害范围的问题。
二、海洋环境、海洋自然资源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含义及关系
“环境”、“自然资源”、“生态”这三个概念在学术界及实践中是经常混淆使用的术语,“生态”时而指称“环境”“,环境”时而指称“资源”“,资源”又时而指称“环境”。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提出了“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环境”与“海洋资源”等概念,但没有对其明确定义。概念的混乱,会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惑,进而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范围产生误解。因此,明确了海洋环境的要素,也就明确了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
“环境”一词在英文中的表述是“environment”,它是由动词“environ”延伸而来。英文中的“environ”源于法语中的“environner”和“environ”。法语中的这两个词源于拉丁词语中的“in(en)”加“circle(viron)”。[6]这些词的含义都是“包围”、“环绕”的意思。《袖珍牛津英语词典》对环境一词的解释是“环绕任何事物的物体或区域”。[7]《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中“环境”一词的含义是“环绕的情况、物体和条件”。[8]可见“环境”一词是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围绕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世界。中心事物的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随之不同。就环绕中心事务的物质、物体、空间、状况和条件而言,环绕中心事务的,可以是物质或物体,如肉眼不可见的空气物质和可见物体;也可以是空间,如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原子空间;还可以是状况、条件、影响或势力,如生态状况和社会条件。在很多情况下,环绕中心事务的,往往是上述物质、物体、空间、条件、情况、影响或势力的交叉和混合。
正因为环境概念外延的丰富和广泛,其在不同的领域里就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学术界一般认为法学的环境概念则是以环境科学上的环境概念作为基础。在环境科学中,环境是指某一事务为中心的外界影响和条件,而这个中心一般是指人类。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一词一般是指“人群周围的境况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包括自然因素的各种物质、现象和过程及在人类历史中的社会、经济成分”。[9]《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则在“环境”的第二词义里,列举了a、b两项词义。a项词义是“作用于生物或生物社会并最终决定其形式和生存的物质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因素(如气候、土壤和生命体)”。b项词义是“影响个人或社会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总和”。[10]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权威性的著作都认识到环境包含自然因素和有关的社会因素,《中国大百科全书》更是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统一在环境的定义中。
法学范畴内的环境概念,在各国环境立法实践中,基本上都是根据本国的环境状况和特点,以法律形式将与本国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必须并且可能加以保护的环境要素以立法形式加以肯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形成“环境”的法学概念。[11]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该概念在对环境做出概括性规定的同时,又以列举方式明确了环境的具体要素。同时,考虑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范围必将日益扩大,法律所保护的自然客体也势必随之而扩大。列举性规定虽然可以使法律上环境的概念和范围更加明确和具体,但是不可能穷尽庞大而又复杂的人类环境的所有要素,因而在概括性表述之后的列举性规定中加上“等”,以表示法律对环境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这些列举的内容。
早在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自然资源的定义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的总称。[12]我国1987年发布的《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对自然资源的解释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都称为自然资源”。其中,对资源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在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为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而被利用的自然物质与能量,它们统称为资源。另一种是指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虽然知道它们的用途但人类还无力加以利用,或者虽然现在没有发现其用途,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这些又被称为“潜在资源”。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与环境在概念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然资源从形式上来说是构成环境的自然要素之一,但是自然资源的概念是从是否可以为人类提供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的,而环境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中与人类社会发生相互影响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从生态学的观念出发,环境与自然资源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环境是由各种生态系统组成,而自然资源是组成各种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并从中体现自己的物质形态。[13]
生态系统的概念出自生态学,是指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系统,其中各成员借助能流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系统”一词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由一些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其二,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规律组织在一起,使这个整体具备了统一的功能特征。[14]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的复合体。[15]与环境的概念相比,生态系统的内涵是以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等客观存在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生命的一部分。
比较上述三个概念的内涵,可以发现:当人类以一种静态的眼光来看待围绕人类存在的全部自然界这个整体时,就出现了环境的概念;当人类从是否对人类有用的角度看待自然界这个整体时,就出现了自然资源的概念;当人类从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自然界这个整体时,就出现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所以,如果以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外部条件的判断标准,那么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都是环境的组成部分。[16]
海洋是由作为海洋主体的海水、生活于其中的海洋生物、邻近海面的大气、围绕海洋周围的海岸和海洋底土组成的统一整体。从环境科学或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人们将海洋称为海洋环境,海洋环境并不是指海洋周围的环境,而是指海洋本身,正如将大气称为大气环境一样。[17]海洋环境是指地球上连成一片的海和洋的总水域,包括海水、溶解和悬浮于水中的物质、海底沉积物和生活于海洋中的生物。海洋自然资源是海洋中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总和。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变化。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在生态系统中,任何环境因子的变化都会影响生态系统,但并非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会必然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比较而言,海洋环境是一个含义最为广泛的概念,海洋环境侧重于整体,海洋资源是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资源体现了自然的经济属性,环境体现了自然的生态属性。如果以环境作为人类外部条件的判断标准,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系是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
三、自然资源损害与生态系统损害构成海洋环境损害范围的两个方面
从国内外相关立法和学者们所使用的措辞来看,“生态损害”(ecological damage)、“纯生态损害”(pure ecological damage)“、环境本身的损害”(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per se)、“环境损害”(environmental damage)、“纯环境损害”(pure environmentaldamage)、“环境损伤”(impairment of the environment)及“自然资源损害”(naturalresource damage)是经常被混合使用的术语。[18]但正如上文所言,环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自然资源侧重于环境要素中能够为人类提供经济利益的物质,这两者包含的范围是有所区分的。石油污染对海洋环境的损害首先体现在对海洋自然资源的破坏,这种破坏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但并非所有的破坏都会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损害。如果以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外部条件的判断标准,海洋自然资源损害是海洋环境损害的基本内容。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的总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是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资源法律关系客体的物的基本特点。与民法上的物的一般属性不同,作为环境资源法律关系客体的物具有双重属性:经济性和公共性。一方面,自然资源可以作为人类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为人类创造财富,自然资源的许多组成部分还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权利人由此得以获取并独占巨额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资源的自然要素与人类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19]在涉及自然资源的公共特征方面,哈丁的《公共地悲剧》通过叙述一个公共牧场的故事,阐述了自然资源的外部效应。也就是说,个体的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可能会给社会其他成员带来危害,但他自己不承担责任,不支付足够的成本应对危害。当这种危害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破坏自然资源的整体性,由个体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根据哈丁的上述观点,“公共地的悲剧”就在于所有权不明确,导致对其占有、收益及处分等派生权利的不明确,从而出现了环境外部性问题。为此,以罗纳德·科斯为代表的学者主张通过明晰自然资源权利的途径解决外部效应所引起的问题,实现自然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在私法领域,权利明晰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效益,但在自然资源领域,这一方式会导致“分割的悲剧”[20]。这种悲剧在于我们分割的是权利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资源因权利的分割而处于不同主体的管理和利用之下,而自然要素依然是一个相互关联和依存的整体,并不因为权利的分割而影响其整体性。
我国以往司法实践中,海洋自然资源损失习惯上被包括在渔业的长期损失中,这实际上是对自然资源公共性特点认识不清所形成的表述方式。所谓渔业损失主要指渔业海域受污染期间,渔民不能捕鱼或捕鱼量减少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该损失是一种纯经济损失,本质上是由于对环境的损害而造成的渔民财产损失,不是针对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
海洋生态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海洋生物生存条件、海洋生物及其群体与周围海洋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系统。石油进入海洋生态系统,对海洋生物有毒性作用,石油可以粘附在海洋生物甚至鸟类的身体表面,妨碍其正常的呼吸和运动。石油还可以在海洋生物特别是经济生物体内累积,进而影响到其食用价值。无机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浓度过高导致海水富营养化,其本身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危害不大,但高浓度的无机营养盐却给海水中赤潮生物特别是藻类赤潮生物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其大量生长则导致了世界性的海洋灾害——赤潮,而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异化,对原有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海洋生态系统损害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依赖的海洋环境的任何组成要素、或者其任何多个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的重大退化,而不是简单的某一单项或几项环境要素的衰退。所以,这种损害是对海洋环境的整体损害;海洋环境损害的范围应包括海洋自然资源损害与生态损害两方面。
将生态系统损害纳入海洋环境损害范围的价值在于体现环境法学中“生态保护”的立法理念。环境立法的宗旨已经从原来的解决日益严重的污染和资源、能源短缺的窘境,制定针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进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或为更持续利用而保护的法律规范,发展到为了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而保护自然界系统,重视整个生态系统的全面保护的法律规范。关注海洋生态系统是强调对海洋环境整体保护的必然结果,防治海洋生态损害才能最终保护海洋环境的安全。
四、结语
根据前文论述可知,海洋环境是一个含义最为广泛的概念。海洋环境侧重于整体,海洋资源是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资源体现了自然的经济属性,环境体现了自然的生态属性。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在生态系统中,任何环境因子的变化都会影响生态系统,但并非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会必然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如果以环境作为人类外部条件的判断标准,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环境的组成部分。海洋自然资源损害是海洋环境损害的基本要素,而生态系统损害是对海洋环境的整体损害。
对海洋环境损害的赔偿费用应从可恢复性与不可恢复性两方面考虑,估算范围以受损资源的恢复费用为主。环境资源不存在市场价值,对环境损害加以估算是非常困难的,而建立在抽象模型基础上的损害估算又很难为赔偿主体所接受,所以,将损害估算范围限于受损资源恢复费用能避免抽象估算方法所带来的操作困难和分歧。对于不可恢复的环境损害,如油污事故造成动植物的大规模毁灭,从技术和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些动植物的恢复是不可能的。这类损害的赔偿在实践中很难实现,但依然有学者认为我国未来油污损害赔偿法应对此提供赔偿救济,可以通过价值估算的方法来估算损害。[21]笔者赞同这种观点。虽然这种估算方法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但通过将其纳入赔偿范围,可以实现对这类资源损害的赔偿目的。
注释:
[1]《海洋溢油之痛》,《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30期。
[2]源自国家海洋局,http://www.soa.gov.cn/hyjww/hygb/hyhjzlgb/2010/06/1275549798468421.htm。
[3]Allen L.Springer:Towards a Meaningful Concerpt of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Law,edited by Paula M,Pevato,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2002,p.532.
[4]Philippe sands: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877.
[5]1993年欧洲理事会《关于对环境危险活动所致损害的民事责任的公约》第8条d款。
[6]王亿同主编译:《英汉辞海》,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749页。
[7]Compact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367.
[8]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Merriam-Webster 1987,p.416.
[9]《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0卷)》(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10]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Merriam-Webster 1987,p.416.
[11]蔡守秋:《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页。
[12]转引自刘天齐主编:《环境保护通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3]刘天齐主编:《环境保护通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4]《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9卷)》(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15]参考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
[16]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7]蔡守秋、何卫东:《当代海洋环境资源法》,煤炭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8]Edward H.P.BRANS:Liablity for Damage to Public Nature Resource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p.17.
[19]吴真:《自然资源法基本概念剖析》,《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20]Eric T.Freyfogle:“The tragedy of Fragmentation”,36 Val.U.L.Rev.307.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 om/result/default.wl?spa=eastcupl-2000&tf=12&fn=_top&scxt=WL&mt=269&rs=WLIN10.08&cite =36+Val.+U.L.+Rev.+307&findjuris=00001&cxt=DC&vr=2.0&sv=Full&cnt=DOC&ss=CNT&tc=1&rlt =CLID_FQRLT1237942722139&rp=/Find/default.wl&n=1&rlti=1&fmqv=c&service=Find
[21]徐国平:《论我国船舶油污造成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立法》,《中国航海》2008年3月。
《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