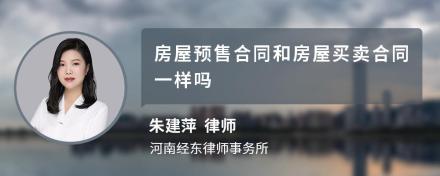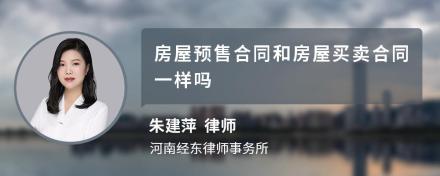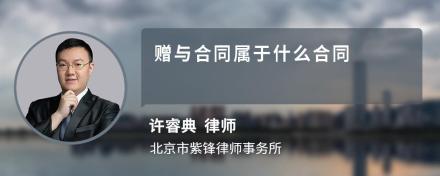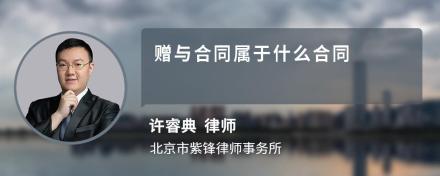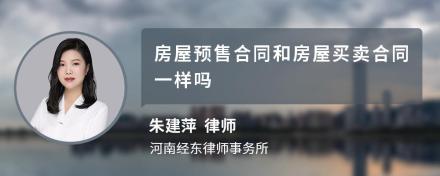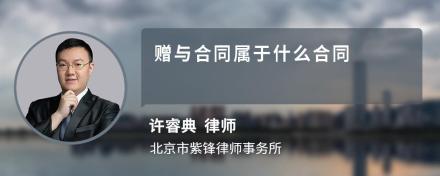导论:合同学术的代际转换
当我在大学讲授诚信履约原则的时候,我安排了两位著名的合同法学者——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史蒂文?伯顿(Steven Burton)——进行了一场交流,这就是人们后来所了解的“萨默斯——伯顿”的争论。 [1]这场争论非常有趣,不仅是因为其参与者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因为它代表了学术模式的代际转换。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像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合同法学者们也拒斥那种试图以一般性概念和规则来表述案例结果的所谓的“概念主义”或“形式主义”进路。那时,对实际商业实践复杂性的“现实主义”调查支配着整个合同学问,此种调查旨在确定法官在决案时实际考虑或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或事项。人们通常认为,在发生法律纠纷之前,我们不能也不应以某种方式对上述因素加以衡量或组织。因为将现实世界商业实践的巨大复杂性简化为某种文字公式的任何努力,都被拒斥为不受欢迎的“简化论者(reductionist)”或“简化主义(simplistic)”。
《牛津英语辞典》将“简化论者”定义为:“简化主义的提倡者;试图通过简化来分析或说明一个复杂的理论或现象的人。” [2]同时,该辞典将“简化主义”定义为:“具有(过分)简化的性质或特征。现在通常具有过分简化或引人误解的简化的内涵。” [3]1881年的一个关于该词用法的例子便抓住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本质,并最终俘获了法律学者的想像力:“自然和生活的事实往往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过分简化的理论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 [4]
萨默斯教授是师承“现实主义”先锋教授们的法律学院派一代——即将他们老师的形态和术语铭记于心的一代。例如,在其1968年题为《一般合同法和<统一商法典>买卖编中的“诚实信用”》的经典论文中, [5]为了解释诚信履行(合同)的默示义务,萨默斯向人们提出了一组六个不诚信履行(bad faith performance)*的种类:(1)规避交易之本旨,(2)懒惰而松懈,(3)只愿意进行“实质履行”,(4)滥用规定合同条款的权力,(5)滥用迫使对方顺从的权力,(6)干预对方当事人的履行或在对方履行时未能给予配合。 [6]在体现现实主义一代(和师承现实主义者的一代)精神的术语中,萨默斯明确否认关于诚实信用的一般性概念的有用性,甚或其可能性:
人们认为,即使排除诚信原则的最为空洞的一般性定义,关于诚实信用的其他任何界定仍将……不能覆盖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特定含义,而根据具体案例所确认的多种和各种不诚信(bad faith)的形式则是可以包括这些含义的……
……关于诚实信用的一般性定义要么体现了卡律布迪斯(Charybdis)女神所代表的空洞的一般性,要么反映了斯库拉女神(Scylla)所代表的受限的具体性。 [7]
他建议说,法官“不应该浪费精力来阐明自己关于诚实信用的简化主义定义。相反,他却应该用心去刻画他选择排除之不诚信的特别形式的特征……” [8]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关于学术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法律学术开始从现实主义模式向被称作“法律理论”的模式转变。跟其他领域一样,合同学术也被那些冒着被封为“简化论”和“简化主义”绰号的危险去寻找统一的法律学说和理论的学者所支配。基于我在其他地方也曾经阐释过的原因, [9]我最初将此种代际间的学术转换归功于法与经济学的兴起——直接回应现实主义者的结果论或“政策”关注——,也将其归功于试图超越功效理论家们(efficiency theorists)“保守”结论的规范法哲学随后的出现,因为在很多“进步的”法律学者看来,上述“保守的”结论实在不合口味。结果,以前那种由罗伯特?萨默斯列出多种现实主义因素、由法官们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加以考虑的学问,便开始给更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让路了。
此种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之一种便是由史蒂文?伯顿发展出来、在其1980年发表的《违约与诚信履约的普通法义务》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关于诚信履约的广泛理论。 [10]在伯顿看来,当合同赋予一方当事人一定程度的履约自由权,而该当事人随后利用该自由去取回先前缔约时的机会时,诚信履约的问题便会出现。因此,要判断一方当事人是否进行了非诚信地履约,就必须认定既存在一个先前的客观机会,又存在一个取回该机会的主观意图。
伯顿声称,如果没有“一个区分诚信履行和不诚信履行的操作性标准”, [11]《统一商法典》中对诚实信用的一般性要求 “似乎就会成为法官或陪审员践行其直觉的许可证,并且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和并不一致的法律适用结果。” [12]伯顿明确表示反对萨默斯的“因素列举(list of factors)”进路,该进路主张:“对于发展出足以解释这些种类所共有内涵的一个统一的理论,人们无能为力。实际上,人们不能也不应该这么做。” [13]与此相反,伯顿则反驳道:“然而,重复的普通法判决充实了诚信履行的概念,以至于人们现在可以表达并评价出一种关于诚信履行的操作性标准。” [14]伯顿的理论建基于“一个对法院明确提及诚信履行的400多个案例的调查,” [15]也依据一个基本的低技术效率分析。 [16]
面对这一挑战,萨默斯并没有保持沉默,他的回应既是方法性的,也是实质性的:
我的观点是,为了达到《统一商法典》205条的目的而给诚实信用下定义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是被误导所致。这些公式提供了很少真正定义上的指导(如果有的话)。而且,它们中的一些可能还限制性地扭曲了诚实信用总体要求的范围……最后,如果我是正确的话,我认为诚实信用这一观念,绝不是那种容易受到此种定义方法影响的观念。 [17]
实质上,萨默斯认为伯顿的上述主张对于判案没有什么帮助,他并没有把焦点集中在正确的事情上,而且也不够深入。 [18]
伯顿用一个深思熟虑而且有说服力的答复回应了萨默斯的批评,在回复中,伯顿突出了他们两人在方法论上的差别——我称这种差别是代际间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语言能引起我们对那些重要事实的注意——即那些合理地展现了与先例的相同点或重大区别的事实……我们想知道,哪些事实将会因为在法律上的重要性而更有价值。
语言能够在包括“实证定义”在内的很多方式上发挥其功能。萨默斯教授对“通常与定义相关的要素列举”的偏好支持了一种理论上可用的形式……然而,另一种可用的形式是一个总体描述或总体模式——对一项复杂事实的简单化陈述……与大多数要素列举不同,总体描述的技术鼓励我们将精力集中于各种事实的复杂关系网络上。 [19]
或者,用P.J.奥罗克(P.J. O, Rourke)的话来说:“谈论复杂性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当涉及到行动时,简单则往往更为有效。” [20]
在引起人们对不同学术模式之代际转换的注意时,我并不希望过分夸大它。并非每个人都试图去统一合同的理论。在这些不想去统一合同理论的学者中,最为著名的是那些与“威斯康星合同学派(Wisconsin Contracts Group)” [21]有所关联的学者和那些被关系合同理论 [22]深深吸引的学者。然而,这两种思想流派都是在斯图尔特?麦考利(Stewart Macaulay)和伊恩?麦克尼尔(Ian Macneil)两位学者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而麦考利和麦克尼尔也都出生于大萧条之初,与罗伯特?萨默斯出生时间相差都不到四年。 [23]
萨默斯对合同学术有相当的影响,而他对同时作为康奈尔法学院同事和自己案例书共同作者 [24]的罗伯特?希尔曼(Robert Hillman)教授,更是有着特别的影响。希尔曼本身就是康奈尔1972年的毕业生,并于1975年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开始其教学生涯。而就在两年后的1977年,史蒂文?伯顿也来到了爱荷华大学。希尔曼和伯顿在爱荷华大学一起共事五年。随后,在1983年的一次能完全代表希尔曼对自己学术模式选择的职业变动中,希尔曼离开爱荷华, [25]加入了康奈尔教员和他的导师罗伯特?萨默斯的行列。
一、希尔曼对合同理论的批评
在过去的25年里,希尔曼教授对合同法学术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 [26]但很早以前,他就表达了对所谓的“现代合同理论”的不安。在1988年,也就是他从爱荷华去往康奈尔后的第五年,他发表了《现代合同理论的危机》一文, [27]文中他对统一合同理论进行了总体性批评,而现在他已经将这篇文章扩展为一本名为《合同法的丰富性》的著作。
希尔曼著作的标题意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合同法要远比现代统一合同理论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和“丰富”:
合同法包括了债的规范方法与理论的丰富结合。它被不同种类合同的特殊规则分成几个部分,同时也包括了多种例外与相反原则。尽管存在多种维度,合同法还是对周边社会价值的一个可靠的反映(如果不是毫无缺点的话)。高度抽象的单一合同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合同法,但它却不能解释合同法的全部领域。〔p.6〕
合同法与合同理论包含了很多的矛盾与差异。由于存在多种不同的债之规范与理论,由于主体原则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例外,也由于它被适用于不同种类合同的特别规则所分割,合同法内部不会完全和谐一致。一个高度抽象的核心合同理论实在不能说明合同法的全部主题。然而,合同法却是对周边社会的各种规范选择的一个合理的反映(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话)。〔pp.273-274〕
通观全书,希尔曼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合同法与合同理论的许多有益洞识——就像他已经在他无数的期刊论文中所做的那样——但在本书评中,我将关注他的总主题:即对不能反映出合同法丰富性的“统一的”或“高度抽象的”合同理论的全面质疑。在这一点上,希尔曼是符合其前代合同法学者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希尔曼企图通过检视诸多原理的具体情境:如合同订立、显失公平和诚实信用,来说明其姿态的正当性。他顾及到了多种理论进路:允诺理论家、信赖理论家、女性主义理论家、效率理论家、关系理论家和批判法学家。
但是,尽管希尔曼声称要从总体上关注统一合同理论,但他似乎一开始就受到他并不赞同的合同理论的困扰。例如,他没有对女权主义合同理论进行批评,实际上他还接受了玛丽?乔?弗鲁克(Mary Joe Frug)本人对所谓的“女权”的分析和描述。 [28]在对批判法律学者的合同理论进行了10页的非批判性的总结之后,希尔曼得出结论说,他发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CLS)的不确定性论题”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尽管没有详细阐明,但他最后补充道:“合同法可能并不像批判法学者所试图主张的那样不确定。”(p.209)希尔曼对关系合同理论的批评同样是很温和的,他仅用一句毫无支持的话驳斥了已经发表的对关系合同理论的无数冗长的批评(尽管对于这些批评他也进行了忠实的引用 [29]):“这些批评似乎低估了进行高度情境化调查和评估相关关系合同规范的司法能力……”(p.260)——尽管他也承认,“人们可能夸大了关系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结论。”(p.260)
不幸的是,这是本书的一个总体倾向。对于自己赞成的合同理论,除了在脚注中引用他人发表的相关批评外,希尔曼教授几乎没有提出甚或从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然而,对于自己并不赞成的理论,希尔曼就会大加指责。当然,希尔曼教授完全有权利赞同或不赞同某些特定的理论——简言之,就是在一个理论争论中拥护与自己相同的主张。但是,本书声称是要关注抽象合同理论或一般合同理论的自身缺陷,希尔曼在前文将合同理论的此种缺陷笼统地称作“处于危机之中”。 [30]他试图提出一种更高境界的主张,以超越那些深陷于“纯理论争论”(p.7)中的人们。如果这真是他的论点,那么该观点也只是得到了有选择的运用。
[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