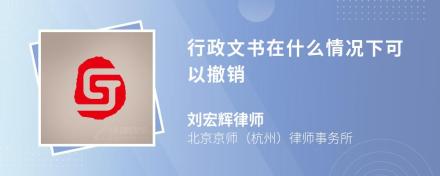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赋予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享有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定权力。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基本的行政救济制度,因此,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撤销主要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完成。权力机关拥有对行政立法、执法的监督权力,更是当然的享有行政行为撤销权的主体。在我国,有权撤销行政行为的主体还有一类,就是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原行政机关。虽然法律、法规并未明文规定原行政机关享有行政行为撤销权,但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难看出它们拥有这种权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条规定:“当事人对海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或者上一级海关申请复议。”前几年,对人事问题争议的处理也有类似规定。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人们一致认同了行政机关有权撤销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这种作法,其理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行政行为是自己作出的,自己当然有权改变或撤销。
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撤销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在国外的做法不尽一致。在法国,行政处理是行政机关对具体事件所作的决定,是数量最多和与公民关系最密切的行政行为,对其有撤销权的机关是原处理机关和对该行政处理有监督权的机关。[1]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其行政法体制按德国和法国模式建立。无需法律明文授权,一般行政厅对其自身行为拥有当然的撤销权。[2]在美国,行政行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规章的行为,更多的是行政裁决行为,行政相对人对美国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不服,可以要求重新审查,称之为行政上诉;有关行政机关及官员据此对原行政裁决重新审查,称之为行政复议。上诉不是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一般是向原行政机关或专门机构提出。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第2款之规定,复议机关行使复议裁决权,拥有初审裁判所享有的一切权力,它可以维持、改变和撤销初审裁决。[3]在英国行政法中,行政行为的撤销权掌握在行政组织系统以外的机关(主要是法院)手中,所有行政机关,更不用说原行政机关,都无权撤销行政行为。即便是部长,也只能就政府决定的事实方面、法律方面以及决定是否妥当进行全面考查,无权变更地方政府的决定。[4]
由此可以看出,凡是承认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有权撤销该行政行为的国家,都把这种撤销权作为原行政机关的自身权力看待,似乎是行政机关的“当然权力”。对于作出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的这种撤销权,可以作两方面解释:一是原行政行为是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基于自身享有的行政职权作出的,是自己的意思表示,这三方面是统一的。撤销该行政行为同样是出于上述目的,是原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如此理解,则撤销权是原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组成部分,是职权。二是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该行为违法或不当,原行政机关有撤销或改变的义务,如此理解,则撤销权是原行政机关行政职责的组成部分,是职责。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理解,原行政机关实际上是在自由支配撤销权。从职权角度讲,原行政机关理所当然可任意作出撤销决定;从职责角度看,原行政机关作出撤销决定要以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为前提,但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或不当,实际上是由原行政机关判定,这与其他有权撤销行政行为的机关以局外人身份认定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原行政机关还是在自由支配撤销权。
毋庸置疑,原行政机关拥有这种撤销权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各自管理的行政事务所作出的,对行政行为违法不当的认定、决定行政行为是否应撤销,需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作保证,原行政机关比其他人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就为行政行为撤销的合法和正确增加了安全系数,使得行政机关能充分地行使管理权。其次,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能最快地失去效力,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危害,又能预防某些危害结果发生,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发生。第三,留给行政机关一个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树立自律意识,健全自我监督机制,积累行政行为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这种撤销权的“自由性”,使得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公正、合法地撤销行政行为是建立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操守这一理想愿望之上的。因此,在英国,行政行为的撤销权是由行政机关以外的机关行使,行政机关无权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日本,行政机关(指行政厅)虽然拥有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但行政厅依职权撤销或撤回行政行为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有些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5]虽然各国对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限制强度不同(总体说来,英美法系国家相对较强,大陆法系国家相对较弱),但明显可以看出人们对行政机关有可能滥用行政行为撤销权的担心。在我国,即便是基于法定权力有权撤销行政行为的国家机关在行使撤销权时,也是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以人民法院为例:依《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限定在五个方面:(1)主要证据不足;(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而原行政机关撤销自己的行政行为则完全没有明文限制。从有关的立法宗旨、精神、原则上判断,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似乎是撤销的标准,学者们也默认了这一做法。[6]如前所述,这一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行政机关如何合理有效地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并无规则可循。因此,行政机关享有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如:第一,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没有切实保障。例如,某工商局作出某公民从事个体经营的许可决定后,又可能借用某种理由随意撤销原来的许可决定,使得该公民失去个体经营的权利。第二,行政机关可依撤销权不履行某种义务。例如某村民计划外生育,当地计划生育部门作出处以罚款的决定,后因该村民的亲友说情,该计划生育部门完全可能依撤销权撤销原行政决定,不履行依法实施计划生育管理的义务。第三,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随意性增大,导致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增多等。因此,对行政机关的这种撤销权力进行有效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及行政行为实践活动来看,对行政机关如何正确有效地行使撤销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进行制约,尚无具体制度和方法,笔者试对此问题提出若干思路。[page]
从常理分析,对一种有危害或有缺陷的事物进行控制,最有效、最彻底的方法是消除该事物本身。既然行政机关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有种种弊端,就应废除这种权力,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我国能否完全废除行政机关撤销自己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原行政机关行使撤销权有其不同于其他机关行使这种权力的特殊性,除了上面提到的积极意义外,还有两个根本性原因。第一,原行政机关的这种撤销权从本质上讲应是行政职权的组成部分,理由上面已经提到,在此不再赘述。既是行政职权,就不应否定这种权力的存在。第二,行政行为经常、大量地存在,行政行为的撤销完全由原行政机关以外的机关行使不现实,任何一个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以外的人和组织,是不可能注意到该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的。况且,社会事物是不断变化着的,公共利益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这一切,只有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较好地把握,适应这种客观要求,依职权主动撤销。因此,对行政机关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的控制,必须建立在行政机关拥有这种权力并能充分行使这种权力的基础之上。
在日本,对行政机关行使撤销行政行为权的控制,是通过内部制约机制完成的。由行政厅撤销时的撤销权者,分为不服审查厅和处分厅,在有明文规定的场合,专门的监督行为厅行使撤销权。[7]这无疑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可以在行政机关内部建立同样的机制,使行政机关的行为权和撤销权相分离,拥有撤销权的主体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决定是否撤销该行政行为。享有撤销权的主体可以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个专门机构(如××室、处、科、委员会)或某个人(如行政首长)。这种做法的有利之处是方便、高效,并能保持一定的公正性。但我国行政领导体制是首长负责制,因此这种分离实际上要受到某种钳制。加之我国行政文化传统本位性强且根深蒂固,这种控制模式有可能治标不治本。
由此观之,对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控制不能拘泥于现有的经验,必须重新审视行政机关的撤销权,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控制模式,既能保证行政机关享有该权力,又能使其充分、正当地使用它,不致滥用。
行政机关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相对人的请求撤销;二是依职权主动撤销。对于第一种方式,相对人不服尚可通过复议或诉讼而使撤销权失去效力从而得以监督、控制。在第二种方式中,行政机关撤销权是作为一种终极性的权力在使用。对该权力的控制处于“真空”状态。我认为,行政机关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行为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看待,是一种特别形态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撤销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它是针对特定的事项———行政行为而作出的;撤销权是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的组成部分,因此撤销行为是基于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所作的行为;行为的法律效果能实际影响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撤销原行政行为使得相对方丧失了某种权利或不履行某种义务。既是具体行政行为,就可以对其合法性予以审查。但应认识到,这种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即被撤销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重合的。原行政行为有抽象行政行为,也有具体行政行为,而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此都变成该撤销行为的相对人,因为撤销行为的针对事项是特定的原行政行为。原抽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本不特定,但因原行政行为本身特定,而撤销行为又是针对原行政行为作出的,相对人相对于撤销行为而言就成为特定之人。相对人的特定与否在行政法中是相对的,相对人相对于撤销行为而言就成为特定之人,应根据不同情况鉴别。相对人只要认为撤销权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即可寻求救济途径。第二,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原行政行为作出的,这一点恒定不变。因此,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总是与原行政行为的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由此,对行政机关撤销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的行为合法性审查就不能等同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而必须确立符合这种行为特性的标准、规则,要达到这个要求则又必须紧扣原行政行为。因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之后即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任何机关和个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或撤销之。这不仅针对相对人而言,也是针对行政机关的。但同时,行政机关又不能永远受这些条件的约束,致使自己不能充分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总体说来,应在对原行政行为的性质、种类、相对人和第三人的地位等考虑的基础上,对因职权主动撤销而获得的价值、利益与因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效力而获得的价值、利益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作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正当的评判决定。在此,笔者提出几种规则供参考。
1.原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原行政机关不能单方面自由地撤销,除非抽象行政行为的结果———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尚未生效。这是因为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其社会效果、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一时不易判定(如某条例一经颁布,有些地方的人就马上实际享有某权利或承担某义务)。因此,行政机关须会同权力机关或上级政府共同决定是否撤销。
2.原行政行为已对相对人或第三人创设权利,如果原行政行为合法,原行政机关不能撤销,除非法律规定允许撤销或相对人请求撤销,但在这种情况下,以不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为前提;如果该行政行为违法,其撤销应受一定的限制,原行政机关只能在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内,有权撤销。因为违法行政行为所创设的权利,在起诉期间内,还处于未确定的状态,一旦起诉的时间已过或法院已判决,违法行政行为所创设的权利成为确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不能撤销。
3.一切由相对人提供虚假材料而创设的权利,后被原行政机关发现,应视为原行政行为没有创设权利,原行政机关可以撤销,且不受时间限制。
4.行政行为涉及的是较大的公共利益,原行政机关不能单方面自由地撤销该行政行为。如修建高速公路或大型桥梁,施工正在进行中,此时原行政机关不能对其作出的修路、建桥的决定自由撤销,应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共同作出是否撤销原行政行为的决定。
5.行政行为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原行政机关义务的,该行政机关不能自由撤销。[page]
「注释」
作者简介:刘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曾获武汉市第五次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2]参见胡建淼:《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
[4]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3]同上,第342页。
[5]在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可变更力,只有经准司法争讼程序进行的行政行为才具有不可变更力,无特别规定,行政厅不得依职权予以撤销和变更。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24页。
[6]参见张尚族鸟:《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4页。
[7]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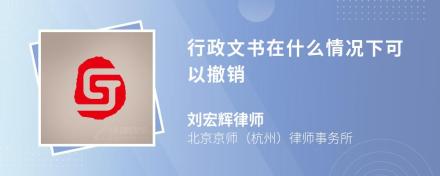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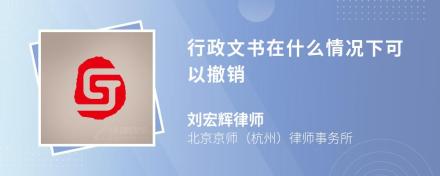


 01:30
人已看
01:30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