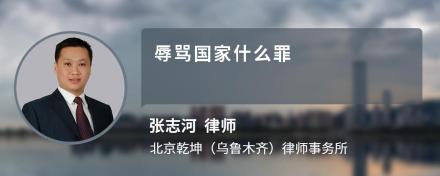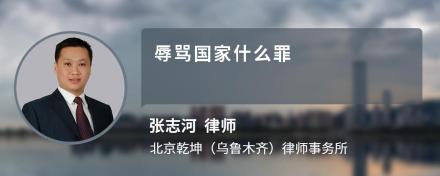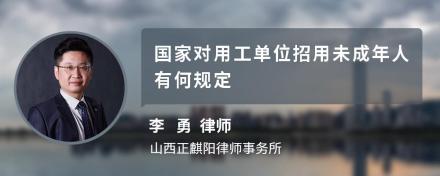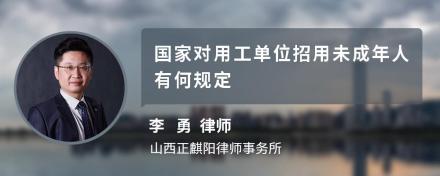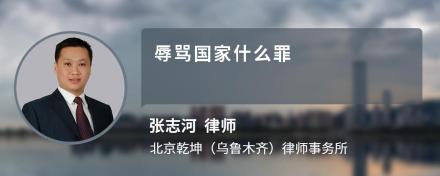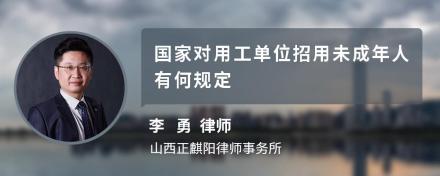糟糕的法律是暴政中最恶劣的一种(艾德孟德 伯克Edmund Burke)
警察法,这是个多少有点尴尬的法律称谓,其实应该是称作限制警察的法律。通常对这些法律的研究包含了四个部分:截停拍身搜查、搜查与扣押、逮捕、讯问,并且要对联邦最高法院创设的两个规则--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以及“米兰达”规则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当然在最高法院那里的警察法律是在完美世界中的警察法律,它与在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那些在街头警务活动中施用的警察法律有着巨大的差别。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包含了保护公民免于警察权力滥用的条款,但是如何在现时代为这些条款做出解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最高法院在其历史上称作沃伦法庭Warren Court (1953-1969)时期制订了绝大多数令警察“穿上紧身衣”的法律规则,但在较具保守性的时期,最高法院也创设出了为数众多的针对上述规则的例外规则。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上,美国有着一套独一无二的制衡制度。人们时常看到有罪之人仅仅因为警察犯下的错误或是莽撞行事而被放行,这看来令人震惊。但这只是这一伟大实验的总体中的一方面,在最高法院看来确实如此;由于警察犯下的错误而惩罚社会,最高法院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令警察将来能犯下较少的错误。
截停与拍身搜查
有些时候警察的兴趣不在于逮捕任何人,也不是想确保任何将会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的可采性。警察这时只是处在调查的初始阶段,只是对核查看似可疑的人或场所有兴趣。警察的这些行动有着多种称谓:现场调查、现场询问、现场探访、初始点探访、前期截停或仅仅是常规询问,但是不管称谓如何,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置于截停与拍身搜查法律之下,这些法律规则的架构在Terry v. Ohio (1968)中得到阐明。在那个案件里警察截停了三个看似很可疑地透过商店橱窗对内张望的人并对他们三人做了自上而下的拍身搜查。美国法律中的截停与拍身搜查与外国法律中的“身份核查”有很大相似性。
截停与拍身搜查法律给予了警察在公共场合暂时留置他人人身的权力,在获得特定的可清晰表达的事实足以引导一名合理的警官相信有犯罪也许正在发生即可成立行使这种权力的正当性。这一标准就是所谓的“合理怀疑”标准,有些人也称这一标准为“可清晰表达的怀疑”或“超过简单怀疑”。并不必须要警官确认是何种具体的犯罪他们认为正在发生,只需要存在的一组情势能够引导警官相信有某种犯罪活动正在发生即可,最高法院将这种怀疑看作程度高于预感而警方则将这种怀疑标准看作是察言观色。
有一些特定的事项是警察明显不能去做的。警察不能在私人场所对任何人实施截停与拍身搜查,尤其是不能在私人住所做这些事情。警察有时使用X射线眼或是红外扫描装置对房屋内进行观察,如果没有获得令状即这样做的话将会构成非法,最高法院在(Kyllo v. U.S. in 2001)中这样裁判。事实上,第四修正案法律的整体思路就是要令警察手中握有的专门技术,宁可再少一些而不是更多一些。
第二件警察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依据种族外貌作出分析,绝对不允许警察利用特定少数裔族群的肤色和配饰风格样式作为依据获得任何可在刑事司法中使用的内容。警察唯一可以貌取人的事情就是在调查运送毒品情形时,这时允许警察将相对人神经紧张的外貌和为外在服饰等因素连同其他情形共同作为判断的依据。
最后的一件警察不能做的事情是脱去特定人衣服、侵入其身体腔孔进行检查,比如对口腔检查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在轻拍搜身、或称“自上而下拍身”中,其动作目的必须是首要为发现武器并仅仅对外层衣服实施。延迟公民的时间长度必须是合理的,并不设定一个武断的限定,法院曾宣布三十分钟是合理的而九十分钟曾被宣布为不合理的时间长度。这都取决于情势和情形,这一标准就是所谓的“整体情势规则”,这一规则是截停与拍身搜查法律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连同“有经验的警察标准”(这一规则让警察自己决定其是否感受到伤害的恐惧)共同作为是否需发动截停和拍身搜查的衡量依据。
警察可以做的事情是对那些举止怪异行为与时间场合不匹配之人,对那些闲逛无所事事看似与已知犯罪人员有关联之人或是对那些符合受缉拿罪犯描述之人实施截停。警察有权力截停任何他们认为是正在考虑或谋划犯罪之人,这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部分。也许未来最高法院很快就会在案件审理中面对这一争议问题。
搜查与扣押
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Mapp v. Ohio案中最终裁判认为:州以及地方警察部门都要对排除规则负起责任。而在这之前只有联邦的警察和少数州警察遵从排除规则或有对以不当方式获得证据有专门规则。对所有的场所都会有对应的令状,申请令状时警官作出宣誓下的书面证词表明在某处可以获得犯罪证据,此时的标准时形成合理可能,这点在申请搜查令和申请逮捕令之间差别不大。Mapp案中要求实施排除规则,这意味着第四修正案中的合理性标准将在各州内适用。合理性是一个涵义复杂有众多涵义的字眼,是指逻辑性的合理性、实务上的合理性、情感上的合理性、智力上的合理性以及可能性上的合理性。法律学者对这定义进行了辩论。合理可能是指在警察使用其训练、利用其经验或专业知识推断或确认某种样式的合理性。
排除规则是法院对警方进行控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非法获得的证据可能是归罪证据中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谋杀用的凶器,这也将被排除,也就是所谓“毒树之果” fruit of the poisoned tree 理论;并且任何从非法获得的证据部分中之后衍生获得的证据都将被排除不具可采纳性。关于排除规则也有着众多的例外规则,列表如下:
诚信规则或轻微侵犯规则(警察在当时确实相信其成立合理可能而实际法律上并不具备) | U.S. v. Leon (1984) Massachusetts v. Sheppard (1984) Illinois v. Krull (1987) Maryland v. Garrison (1987) Illinois v. Rodriguez (1990) | 直接目视规则或公开检查(警察出于偶然巧合观察到违法犯罪;证据将不可避免会被发现) | Harris v. U.S. (1968) Coolidge v. New Hampshire (1971) U.S. v. Irizarry (1982) Nix v. Williams (1984) Horton v. California (1990) | 机动车之例外或制作财产清查目录例外(对乘客区域的搜查、对后备箱的搜查、对门、地板、以及任何移动中的机动车辆) | Carroll v. U.S. (1925) Chambers v. Moroney (1970) New York v. Belton (1981) U.S. v. Ross (1982) California v. Carney (1985) California v. Acevedo (1991) Ornelas v. U.S. (1996) | 紧急情况。紧迫情势或附带情势之例外(危及生命、有脱逃的风险、证据毁损,实施敲门并宣告规则会产生危险或无用后果,实施保护性清查搜查,以维护公共安全的名义要做出迅即的行动) | Warden v. Hayden (1967) Chimel v. California (1969) U.S. v. Edwards (1974) Mincey v. Arizona (1978) New York v. Quarles (1984) Borchardt v. U.S. (1987) Maryland v. Buie (1990) Wilson v. Arkansas (1995) Richards v. Wisconsin (1997) Illinois v. McArthur (2001) | 开阔地域或遭抛弃的财产(在庭院内旧物或物事;从空中用肉眼直接观察) | Hester v. U.S. (1924) Oliver v. U.S. (1984) California v. Ciraolo (1986) U.S. v. Dunn (1987) California v. Greenwood (1988) Florida v. Riley (1989) | 警方线人在狱中号房内 | Kuhlmann v. Wilson (1986) Illinois v. Perkins (1990) Arizona v. Fulminante (1991) | 职员造成的计算机操作错误 | Arizona v. Evans (1995) | 这些例外规则意味着,警察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令状就实施证据搜查与证据扣押。在实践中,警察通常会尝试申请获得令状,或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依靠人们对警察权威的尊重、利用同意下的搜查之例外规则保护自己。人们会惊讶于如此之多的嫌疑人都假设在被警察问及时如果拒绝警察进入自己就会陷入麻烦之中。
逮捕
逮捕是一种特别形式的扣押,在这种形式中特定人被扣押人身或被置于羁押之下。这里,标准过去一直是、也将一直是“合理可能”。但是最高法院允许地方性操作程序规则修改这一标准,因为有时在有时间去获得逮捕令之前确有必要实施逮捕。在讨论侵入性逮捕中要注意这种逮捕方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物理强制或使用武力剥夺特定人的行动自由。通常这意味着上手铐、带上运输车辆、带至警局。逮捕不是指截停、命令不许动、激烈交谈、电话交谈、或其他相关人(理论上)有离开自由的场景。逮捕的要件关键是羁押。
美国法中对逮捕权力施加的合理可能要件限制是出于防止警察出现不想出现的局面的目的,毕竟设定合理可能要件会保留法官而不是警察有最后话事权的权力。不幸的是,对这位法官而言构成合理可能事情对另一位法官而言并不一定尽然如此,毕竟解释第四修正案的方式如此之多。但是依据普通常识加以解释的路径很可能是主导性的解释路径,这种解释路径认为,构成合理可能应当包含犯罪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实质的高可能性substantial probability”。
讯问
一旦有人被羁押事情就开始变得似乎调查的重点聚焦于他的身上将其作为特定的嫌疑人(通常羁押和重点调查都是同义含义有时候也不尽然),必须对他们大声宣读米兰达权利(可保持沉默,任何陈述可以用作对其不利的使用,在被提问中可以要求律师在场也可以获得向律师咨询,如果负担不起律师费用,将有受指派律师提供给他们),米兰达规则被提到时通常称作“第五修正案与第六修正案的婚姻结合”。
违反米兰达规则导致的后果是任何建立在被告言辞上的证据被直接(自动)排除,无论嫌疑人对警察作了什么陈述也无论警察利用这些陈述作任何用途的使用都将由于违反米兰达规则而致无效。但是,违反米兰达规则本身并不是认定被告无罪或是推翻有罪认定的依据。
如果出现以下两个要件,那么米兰达规则就会被触发或者说得到适用,这两个要件是:羁押和讯问。对这两个要件的界定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困难得多。一般性规则是羁押出现在嫌疑人被置于其不熟悉和敌意性环境之下。而讯问是指在内在本质上对其有说服或施压行为,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语言上的巧计获得供述,或至少获得承认(软性供述),以及任何将会使得嫌疑人牵连入犯罪行为的信息。嫌疑人必须作出明确清晰不含混的会见律师要求(也就是艾德沃德规则Edwards rule),警察必须尊重嫌疑人的要求并停止问话。所谓明确清晰不含混的意思是其使用的语言要强硬于“也许我应该和和律师谈”这样的表述。如果警察停止提问,而嫌疑人自己重新开始交谈,或重新发起与警方的进一步交流,这时起任何其说出可以归罪的陈述都可以用作对其不利的使用。关于此有众多的其他规则,现列于下:
ATTORNEY WAIVERS (Moran v. Burbine 1985)放弃律师权规则。如果嫌疑人在其放弃要求律师到场权利而嫌疑人的律师电话告诉警方表明其希望他的客户不要开始对警方谈话,而此时嫌疑人已经开始和警方交谈,此时警方不负有任何法律义务通知嫌疑人其律师的愿望。
BOOKING PROCEDURES (Pennsylvania v. Muniz 1990)立案程序。如果警方正在执行标准化的勤务操作,比如在立案程序中仅仅对嫌疑人按捺指纹、拍照摄像等则不必对其宣读米兰达警示。
DELAYED WARNINGS (Oregon v. Elstad 1985)迟延后的警示。如果嫌疑人在收到米兰达警示之前即刻做了供述而之后在警局获得了米兰达警示又做了供述,最初的陈述可能不得使用、但后一次陈述可以使用。没有即可作出米兰达警示并不会令之后的讯问不具法律效力。
DERIVATIVE EVIDENCE (Michigan v. Tucker 1974)衍生证据规则。如果嫌疑人没有被宣读米兰达警示并且对警方的问话做出提出不在场抗辩的反应,那么就会出现适用衍生证据例外规则。如果警方对嫌疑人提出的不在场抗辩加以核查并从中获得指引获得证人并从中获得可对嫌疑人做不利使用的归罪信息。则任何证人证言的可依赖度都不受警方先前违反米兰达警示之影响。
ILLEGAL SEARCH AND SEIZURE (New York v. Harris 1990)非法搜查与扣押规则。如果警察以不合法的方式进入了居家并实施了非法的逮捕,然后将嫌疑人带至警局向其宣读权利,嫌疑人作出供述,则搜查与扣押的非法性不会玷污之后供述的合法性。
IMPEACHMENT (Harris v. New York 1971)质疑证人资格。质疑规则是审判程序中摧毁证人可信度的规则。如果被告人本人作对其有利的证言,则法律允许非法获得的供述在审判中获得采纳,因为这可能能揭示出被告人实施作伪证。另外,在被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而之后被告在审判中试图采用自我辩护的辩护策略那么其先前的保持沉默将会被推定为有罪。这是由于如果其有自我辩护的动机那么被告人对警方说出此动机本将是合情理的事情。
INDEPENDENT EVIDENCE (Arizona v. Fulminante 1991)独立证据规则。如果同监人在受到其他同监服刑犯物理攻击的威胁,而获得同监犯(实为卧底警察)的保护承诺,作为回报条件,他讲出实情;这种供述属于受到强迫下作出,因为存在物理攻击的威胁,但是如果能引入支持有罪事实认定的充分独立证据那么有罪认定没有必要被推翻。
PRIVATE SECURITY (U.S. v. Garlock 1994)私人保安。米兰达规则完全不涉及嫌疑人与缓刑官员、私人侦探(可能是受雇于受害人)或任何私人法律执行官进行谈话的情形。私人行为主体,即使是其最为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也不可能侵犯第五修正案为嫌疑人规定的免于自我归罪的权利。
PUBLIC SAFETY (New York v. Quarles 1984)公共安全规则。如果警察在抓捕或追击隐藏或丢弃枪支或毒品之人,如隐藏或丢弃地点可能会有无辜公众经过、其可能遭遇这些违禁品,那么警官不必宣读米兰达规则而可以直接发问“东西在哪里?”。
PURGED TAINT (Wong Sun v. U.S. 1963)洗净污点规则。在非法逮捕后获得的供述可以作为证据获得可采性,如果警方的非法行为特征可以被用某种方式洗净的话。通常这一规则适用于涉及在不同时间点多次提问的场合;比如,有休息间歇的马拉松式的讯问或是更常见的情况是嫌疑人在被释放后自愿回来继续回答提问。在有时间上的间歇后,嫌疑人自愿谈话的情况下先前的警方行为的非法性就被洗清了。
RESUMED QUESTIONING (Michigan v. Mosley 1975)接续问话规则。如果第二位警官在几小时后在不同的房间内开始新的讯问,不必对嫌疑人重新宣读米兰达警示。但是如果经历实质性长时间段间隔后根据所谓“陈旧性原则”staleness doctrine应当宣读米兰达警示。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警察机构(联邦或州)进行讯问之时,有必要重新宣读米兰达警示。
SURREPTITIOUS QUESTIONING (Illinois v. Perkins 1990)如果使用便衣警官或是警方线人从嫌疑人处获得归罪证言,将不会违反米兰达规则也不会侵犯嫌疑人的第五修正案权利。但是如果在作出正式指控后警方采取这种技巧手段的话将会侵犯嫌疑人的第六修正案权利。如果嫌疑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法律执行官讲话,那么就不需要对嫌疑人作出米兰达警示。
【作者简介】
蒋天伟,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