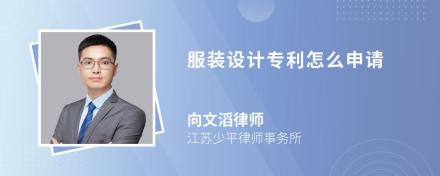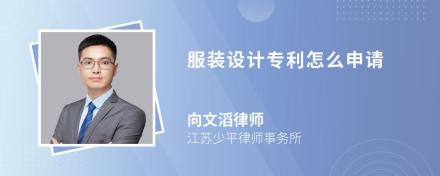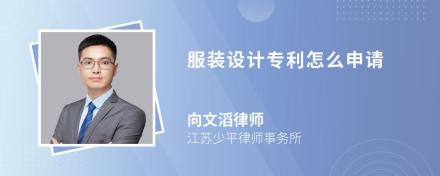【摘要】2009年
重庆市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因伪造民族身份,被取消录取资格。一时间众说纷纭,但从现有法律制度来看,何川洋并非无辜,虽北大弃录于法无据,但重庆市招办则可以取消其录取资格。通过个中法律问题的交织,可以看出,这种没有进入司法场域的事例,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案例研究的绝佳素材。
【关键词】高考状元;行政处罚;案例研究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基本案情[1]
自古以来,状元就是最耀眼的明星,而今年夏天,重庆市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则更加引人关注。
1991年,何川洋出生在重庆市
巫山县官阳镇,父亲何业大、母亲卢琳琼当时都是乡镇干部,从童年开始,何川洋就展现出聪慧的头脑,学习成绩让父母长辈充满了期待。2006年,何川洋以全县第四名的中考成绩考入南开中学,进入这所由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重庆名校。这通常被理解为离大学仅有一步之遥,但为了确保儿子能荣登名校,何业大开始着手办理更改何川洋民族成分一事,以便高考时获得20分加分。虽然明知这是个错误,但面对20分的巨大诱惑,在招生办工作的何业大决定为儿子铤而走险,不想却为何川洋3年后的高考埋下了苦果。
2009年6月9日,高考结束的钟声刚一落下,就有群众举报巴蜀中学多名学生以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考生身份报名,骗取20分加分,由此拉开了重庆“加分门”调查的序幕。随后,重庆市查实,确有31名违规更改户籍获取加分资格的考生。6月22日,重庆市对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份,试图骗取高考加分的学生作出取消加分资格的处理,但未公布具体的名单。
6月24日,随着重庆高考成绩张榜,原本已经沉寂的“加分门”事件再次引人关注。何川洋以总分659成为重庆“文科状元”。然而,这匹黑马在媒体正要热烈报道他的时候,却失踪了。没多久,便有网友报料称,何川洋是因为民族成分造假被查,所以不敢面对媒体,而何川洋的父亲何业大还是巫山县招生办主任。在媒体的追问下,何业大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上级的任何处罚。6月29日,重庆巫山县公布对何川洋少数民族成分变更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免去何业大职务,对身为组织部副部长的卢林琼也予以停职反省。但6月30日,重庆市教委证实,何川洋因违规更改民族成分而被取消少数民族加分资格,但其录取资格仍保留。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尽管何业大和卢琳琼为错误承担了责任,但坏消息仍接踵而来。7月2日凌晨,之前与何川洋签订预录协议的
北京大学招办主任刘明利发来短信,称北大决定放弃录取何川洋。何川洋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报了北京大学一个志愿,北大的弃录意味着他走到了本次高考的尽头。在重庆31名违规考生中,何川洋成为出局第一人。7月7日,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对2009年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加分问题处理情况的通告》,其核心内容是:
一、按照国家民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份有关规定的通知》(民办政法发[2009]121号)之规定(以下简称“三部委文件规定”),取消联合调查组查实的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份的考生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资格。
二、鉴于31名考生系青年学生,其中大多数系未成年人,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本着“教育和保护相结合”和有利于青年学生成长的原则,故不对外公布这31名考生姓名及相关信息。[2]
二、法律争点
高考状元、身份造假、官员子弟,这些称号加在一起让未满18岁的何川洋成了这个夏季街头巷尾的谈资。截至写稿时,笔者在“谷歌”搜索栏输入何川洋,得到的查询结果达483,000 条之多。《南方周末》、《新京报》等纸质媒体也都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抛开人们对当下高考制度、民族政策、大学之道、诚信品格等等的情感争论,笔者仅把有限的目光投在状元落榜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上。对事发以来,众说纷纭的争论进行归纳,大致有以下几个法律争点:
1. 尚未成年的何川洋面对父母一手操办的身份造假是否无辜?
2. 北大是否有权“弃录”何川洋?
3. 谁有权对违规状元作出怎样的处罚?
4. 两年多前更改的民族身份,是否已经过了处罚时效?
三、法律分析
1.尚未成年的何川洋面对父母一手操办的身份造假是否无辜?
在百度“何川洋吧”有人呼吁“孩子是无辜的,十二年的寒窗不能因父母的过错而让孩子承受罪过!”。许多为何川洋辩护的人也指出,造假者是其父母,何川洋系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一言以蔽之:他是无辜的。[3]那么,何川洋果真是无辜的吗?答案显然不是。
按照1990年开始实施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凡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须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后,方可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具体到学生参加考试,更改民族成分需要过五关:(1)伪造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分证明;(2)通过民族事务主管部门的审查(3)经公安部门审批;(4)更改考生的户口簿和身份证;(5)在高考报名点老师的监督下,报名参考,获得加分资格。何川洋更改民族身份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15岁。如果说伪造身份证明,经相关部门审批都是在其父母操办下完成的,那么,学校的学籍档案应该是他本人填写,或至少说本人是知情的。15岁的年龄,虽不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但在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上,必定是具备了相应的责任能力。高考报名时,再度填写民族身份,年满17岁的何川洋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已不能说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要知道,高考报名的所有个人档案信息都是由本人填写,如果说未满18岁,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高考报名由考生本人填写的报名信息还有何意义呢?因此,不能说何川洋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享受了父母所给予的利益,而是他也参与了这项造假事件,至多不过说他可能是“从犯”罢了。
2. 北大是否有权“弃录”何川洋?
向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的北京大学,在高考成绩揭晓后,便主动于填报北大的何川洋联系,面谈后许诺他被光华管理学院预录。但随着身份造假事件的争议愈演愈烈,7月2日凌晨,北大又以短信告知放弃录取何川洋。于是乎,北大也成为众人争议的对象。著名律师周泽首先发难,于7月4日在《新京报》发表《弃录何川洋涉嫌违法》。次日,学者陈步雷在《新京报》发表回应文章《弃录何川洋无涉违法》。除此之外,法律学者张千帆,《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童大焕,评论家盛大林等人均撰文发表高见。[4]
众专家见仁见智,观点一分为二,答案经纬分明,理由分明是“情”与“法”的较量。认为北大弃录何川洋并无不当,甚至为其大唱赞歌的评论家盛大林先生认为,北大应该就是纯洁的“象牙塔”,应该把诚信的道德品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可北大弃录合法的陈步雷认为,何川洋和北大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考生可以报考、要约,学校可以选择、承诺。即使是一比一地投档,北大也没有义务录取重庆投送来的所有考生,更何况是按照1.2比1的比例投档。”法律学者张千帆也认为“诚实和信用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个人素质,应该作为决定录取的重要因素”,北大弃录是有一定理由的。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诚信的重要性,甚至从情感上来说,笔者也认为堂堂北京大学是应当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但从现有的制度来看,北大的做法则未免失当。周泽律师对其的指责颇为合理。
北大是在7月2日作出弃录决定,而6月30日,重庆市教委已经明确表示,何川洋因违规更改民族成分而被取消少数民族加分资格,但其录取资格仍然保留。根据《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条关于“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录取,取得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的规定,“对考试成绩优异的考生,被报考的高校理所当然地应该通过审批,予以录取,给予其入学资格,否则,就是滥权,就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侵害!”[5]也就是说,在北大决定弃录时,何川洋是享有录取资格的,只不过是以“裸分”参加录取。北大虽然有在投档考生中挑选的权力,但绝不是随意挑选,而是在招生政策所限定的条件中进行挑选,考生的成绩当然是最主要因素。除非排名在前的考生有特殊情况,否则只能按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根据北大发给何川洋的信息可以看出,[6]北大弃录的主要理由就是何川洋伪造民族身份,认为何不诚信,犯了“原则错误”。那么,北大录取过程中,那些是需要考虑的“原则错误”呢?这种“原则错误”的认定有何依据呢?笔者尽力查询了高考录取工作中所有的政策性规定,涉及考生思想品德的要求是教育部于2009年3月3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附件《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第9条规定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属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或参加邪教组织的; (2)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治安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何川洋的不诚实显然不属于品德不合格的范围。莫非北大适用了未曾公开的内部规范?
3.谁有权对违规状元作出怎样的处罚?
北大无权弃录何川洋,不等于纵容违规造假,更不必然意味着法网疏漏。实际上,在2009年4月22日,国家民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第四条规定:
“对于弄虚作假、违反规定将汉族成分变更为少数民族成分的考生,一经查实,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试机构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7月7日,重庆市招办恰是依照该《通知》对何川洋等31名篡改民族身份的考生给予了处罚。但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只有法律和
行政法规才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第11条)。《通知》发布的对象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教育厅(教委)、公安厅(局)”,实为一个内部行政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当然无权创设新的行政处罚,也不宜对现有的行政处罚作具体规定。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相关规范性依据吗?笔者查询之后发现,原国家教委在1988年5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处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至今仍然有效。其中第8条规定: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取消报名资格、考试资格、被录取资格,或者取消入学资格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并给予一至三年不准报考的处罚;在职考生,还要通报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规定的第一项行为即是:“假报姓名、年龄、学历、工龄、民族、户籍、学籍,伪造证件,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骗取报名资格的”。《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暂行规定》由原国家教委颁布,属部门规章,当可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鉴于考试已经结束,取消报名资格和考试资格已不可能,因此,重庆市招办可对何川洋作出给予通报批评或取消被录取资格的决定。
倘若法律问题如此单一的话,本事例也便失去研究的价值。纵然笔者为重庆市招办找到了处罚依据,但对于何川洋来说,并不是没有为权利而斗争的余地。且不说,重庆市招办的处罚决定只是在网上发布,且未署名。只是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人们即视为是招办作出的决定。没有遵守法定程序的处罚应属无效。重庆市招办全称系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包括重庆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和重庆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是重庆市负责大学中专招生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的副厅(局)级行政机关,于1998年起正式行使省级管理权限。享有行政处罚权。但《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而并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对高考违纪情况作出取消录取资格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只能“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暂行规定》所设的“取消被录取资格”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应属无效。
4. 两年多前更改的民族身份,是否已经过了处罚时效?
有论者认为何川洋违规变更民族成分的违法行为发生于2006年,距离2009年何川洋参加高考已历时2年有余,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应当再对何川洋的民族造假行为予以处罚。也就是说,何川洋的违法行为已经过了处罚时效。[7]这种观点颇有道理,因为何川洋的违法行为确实是在2006年已经完成,该行为已经结束,持续的不是违法状态,而是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何川洋更改民族身份的违法行为已经过去两年,但在高考前填写报名信息时,何川洋再次做了违法行为。前述《通知》第一条要求“公民个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分确定。父母双方均不属少数民族成分的,本人不得变更为少数民族成分。考生在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报名时填写的民族成分必须真实有效,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何川洋在报名时填写的民族身份非真实,当然无效。由此来看,两年的处罚时效应从2009年高考报名时起算,而非2006年更改民族身份时。何川洋的违法行为并未“过期”。
5.结语
状元落榜在这几年似乎已不新鲜。高考移民、特长生加分,如今又有更改民族身份,真是应有尽有。纵然我们的高考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迫切需要改革,但法治的大敌是超越法律、漠视法律。无论是考生的“投机钻营”,还是管理部门的“严惩不怠”,都应当在现有的制度内进行,民众的讨论也应立足于现有制度在诉诸于情理。这样才能发现法律的漏洞,也才能建设性地捍卫法治(制)。遗憾的是,对于高等院校的招生,我们还没有相关法律对其作出规范,行政法规也鲜有涉猎,多是以教育部的红头文件作出规定,由此给管理机关的处罚行为造成盲区,被处罚者完全可以站出来说“不”。[8]
四、案外余墨
除此之外,笔者还想说的是,众说纷纭中,多是以情论事,少有人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做深入细致的分析。此次事件中,周泽律师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但应者寥寥。虽然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学界公认,[9]而进入学者们视域的“案例”(case)多是进入司法领域、为法院所审理或判决的案例,甚至更主要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人民法院选编的各类文献中出现的案例。这固然与我们的案例研究刚刚起步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法学对社会的关注和反应还很不够,还不能从书斋理论回到现实,回答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关心的问题。[10]笔者认为,完整的案例(case)研究还必须关注那些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例”,要像其他社会科学学者那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谈case,这不是凑热闹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现实和理论所需要的,也是法律人所应有的担当。
首先,相对于法院汇编的“案例”来说,“事例”没有经过他人的“咀嚼”,也免受当事人的诉求、律师的争议以及法官的裁决所框定的问题(Issue)所左右。我们完全可以在全面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其中的法律问题,分析个中缘由。少一些条条框框的拘束,多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
其次,法院汇编的“案例”都已尘埃落定,学者的分析尽管对于法律的完善,法官思考方式的提升,下一个个案的公正有所助益,但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说,不过是事后诸葛。而“事例”则恰恰是当事人,乃至社会的迫切需要,捋清法律缘由,正是应当事人之所急,送当事人之所求。同时也是社会对法律人的渴望和期待。
最后,限于我国目前案例公开的信息不够,学者们所能获得的可供分析的案例实在不多。从现有的文章来看,多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案例指导》、《人民法院案例选》等为数不多的案例汇编的热捧,对其中所收的案例反复咀嚼,而媒体追踪报道、热炒的一些司法外“事例”则鲜有问津,似乎没有法院的介入,就不成为案例(case)。认真对待“事例”,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让我们攫取的样本可以更广些,恐怕也能更多地关照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中国的问题。
【作者简介】
李松锋,法学硕士。
【注释】
[1] 本部分案情概述主要参考了:《重庆文科状元民族身份造假,其父为县招办主任》,载《新京报》2009年6月27日;《重庆状元:从“王牌”到“弃子” 重点中学高考竞争惨烈手段起底》,载《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
[2] 《关于对2009年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加分问题处理情况的通告》,见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公众信息网。http://www.cqzkb.gov.cn/news/html/2009/090707.htm。最后登陆时间为2009年7月19日。
[3] 这种观点的评论很多,在百度和谷歌上输入“何川洋”“无辜”两个检索词即可查询出大量结果。比如,笔者于2009年7月19日检索时,在第一页即看到有:考题网:“无辜的高考状元何川洋及其它”,见http://www.kaoti.net/index.php?mod=group_thread&code=view&id=6068;复兴论坛上有署名为霄懿写给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北大,别伤了无辜 ——— 致北大校长”,见http://fuxing.bbs.cctv.com/viewthread.php?tid=12071107;凤凰网网友“西南偏南”在其博客上撰文“何川洋被北大和港大拒招绝对无辜”,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2894494.html等等。
[4] 相关文章主要有:周泽:《弃录何川洋涉嫌违法》,载《新京报》2009年7月4日;陈步雷:《弃录何川洋无涉违法》,载《新京报》2009年7月5日;周泽:《再说北大弃录何川洋违法——兼回应学者陈步雷 》,见http://blog.163.com/zhousanwei@yeah/blog/static/99889822200965102510324/。童大焕:《何川洋不能因状元身份受豁免》,载《东方早报》2009年7月6日;张千帆:《高考加分是一个制度难题》,载http://const123.fyfz.cn/blog/const123/index.aspx?blogid=496790;盛大林:《弃录“造假状元”,北大令人起敬!》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eba5600100dmy2.html。最后登录时间均为2009年7月19日。
[5]周泽:《再说北大弃录何川洋违法——兼回应学者陈步雷 》,见http://blog.163.com/zhousanwei@yeah/blog/static/99889822200965102510324/。最后登录时间为2009年7月19日。
[6] 北京大学本科招办负责人表示,依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北京大学招生办在核实全部事情之后决定,放弃录取重庆考生何川洋。他“希望所有考生引以为戒,做诚信之人,行正义之事……并从自身找原因,改过自新,努力在今后的道路上不再犯原则错误,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未来的道路上,北大依然欢迎他!”(据7月2日《
成都商报》)
[7] 王稷象:《取消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录取资格违法》,见http://wangjixiang.fyfz.cn/blog/wangjixiang/index.aspx?blogid=495002。最后登录时间是2009年7月19日。
[8] 相关法律分析可参见李松锋:《“李洋事件”的出路何在——兼谈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话语悖论》,载《华中法律评论》第1辑第1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周泽:《取消录取资格违法:考生如何说“不”》,见http://blog.163.com/zhousanwei@yeah/blog/static/99889822200961311423116/。最后登录时间为2009年7月19日。
[9] 相关的新近论述可见余凌云:《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载《读书》2008年第11期。
[10] 笔者欣喜地看到,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余凌云教授“选材”的案例已经包括未被起诉的案件,以及只能称得上是一种行政事例的“案件”。并对这种广义的“案例”标准提出期待。

 01:50
人已看
01:50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