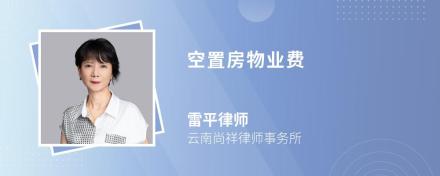相关知识推荐
-
基金监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指按照国家规定,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分别按工资总额及缴费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为保障企业职
养老保险管理人看过
-
受贿罪量刑标准
 02:38
人已看
02:38
人已看 -
项怀诚:社保基金不是托市资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表示,全国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是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战略储
社会劳动保险人看过
-
私募基金怎么发行
在生活中,我们接触的基金一般都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是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资金。相对于公募基金来说还有一
公司法人看过
-
空置房物业费
空置房物业费一般为小区总费用的70%,具体看物业的公示。根据《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八条: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按照政府价格
物业管理人看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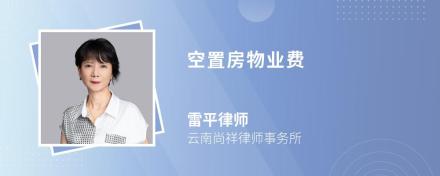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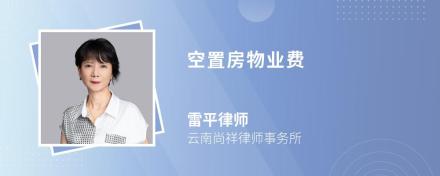
-
股票和基金
股票是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一部分也是发行的所有权凭证,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
债权债务人看过
-
受托人是否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受托人无权以自己名义起诉,只能以委托人的名义起诉。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
信托法人看过
-
信托与委托代理的区别是
信托与委托代理之间的区别包括有:信托的当事人为多方,而委托的当事人为双方;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
信托法人看过
-
委托和信托代理要怎样进行区别
委托和信托代理的区别方式:1、信托的当事人至少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而委托代理的当事人仅有委
信托法人看过
-
信托与委托代理的不同是什么
信托与委托代理的不同之处是:1、信托的当事人至少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而委托代理的当事人仅有
信托法人看过
-
委托和信托可以怎么区分
委托和信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区分:1、信托的当事人至少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委托代理的当事人仅
信托法人看过
-
信托与委托代理怎么区分
信托和委托代理可以通过以下方面区分:1、信托的当事人至少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委托代理的当事
信托法人看过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