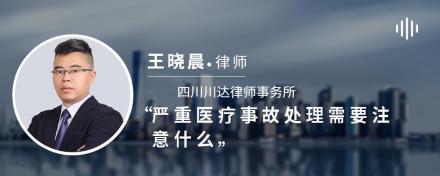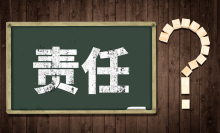相关知识推荐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最新全文是怎样
医疗事故发生后处理方式有好几种,医疗事故发生后可以先跟医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介入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看过
-
处理医疗事故要哪些证据
处理医疗事故需要的证据有:1、患者及其近亲属、医务人员的陈述;2、住院单、药物清单等病例资料;3、证人证言;4、通过向卫
损害赔偿人看过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废止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的,关于医疗方面主要还是要遵循专业的医疗法律。那么为了让大家能
医疗事故处理人看过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规定的情况
按照法律冲突的解决规则,不同位阶的法律发生冲突时,高位阶的法律效力优于低位阶的法律效力。只有同一位阶
医疗事故人看过
-
严重医疗事故处理需要注意什么
尽早复印并封存病历保存证据,分析是否伪造、篡改病历,发现以上问题及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投诉。造成患者死亡的必须在规定期限
医疗事故人看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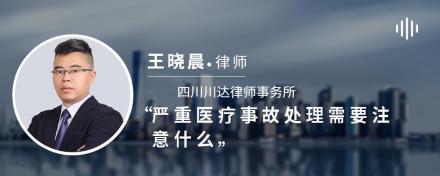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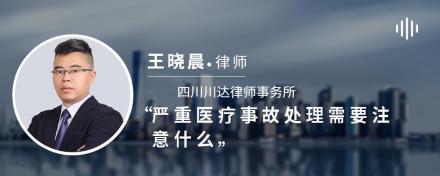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规定的有哪些?
按照法律冲突的解决规则,不同位阶的法律发生冲突时,高位阶的法律效力优于低位阶的法律效力。只有同一位阶
医疗事故人看过
-
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的诉讼时效怎么算
医疗事故赔偿纠纷的诉讼时效为三年,应当自受害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
医疗事故人看过
-
医疗事故医院不赔偿该怎么办
医疗事故中医院若不予赔偿的,当事人可以与医院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医疗
医疗事故人看过
-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反悔怎么撤销
医疗纠纷中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协议书反悔了的,无法自行撤销,必须经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之
医疗事故人看过
-
病历复印的内容有哪些
病历复印的内容一般包括有:病历首页、病程记录。以及各项检查的内容如实验室检查、超声、心电图、照片、C
医疗事故人看过
-
哪些情形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包括有: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的;医务人员
医疗事故人看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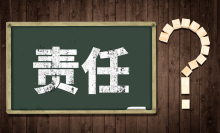
-
医院出伪证如何处罚
医院出伪证若是构成伪证罪的,会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医疗事故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