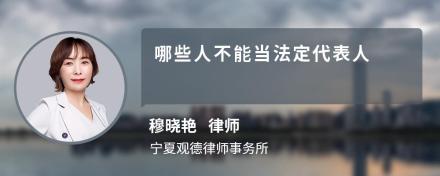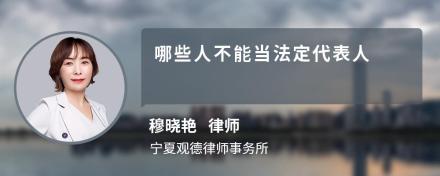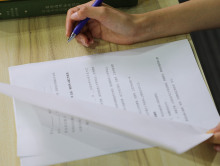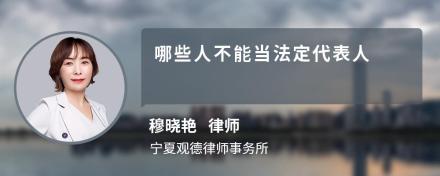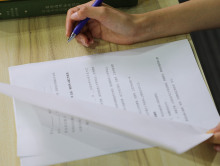一、导 言
1.如果某人遍览瑞士债法的有关判决和文献,不久他就会遇到一个鲜明的“理性人”形像。无论是合同解释、合同补充、注意义务(Sorgfaltshaftung)还是其他事项,其间始终都存在一个“理性人/合理人(vernuenftige/verstaendige Mensch[1])作为衡量尺度。”理性人这一神秘的存在体(Wesen)裁定了诸多案件。在论述“法律中的人像”的书中,自然不可或缺。令人惊讶的只是,在瑞士,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大量研究的对象。究竟何以如此,的确是个谜团——如果人们想想,法官为阐明其他东西投入了何等辛劳,而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同样并不存在。[2]理性人研究方面的滞后,可能主要是因为立法者至今几乎也没有发现“理性人”。[3]所以,瑞士债法(Obligationenrecht,简称OR)只有几处使用了“理性”这一用语;[4]瑞士典(简称ZGB)也仅限于在解释“判断能力”时,加入了“符合理性的”进行行为的能力这样的表述。[5]
2.本文是为庆祝所写,它虽然不能弥补这一研究上的疏忽,但可能会带来一些思想启迪。文章定位于瑞士债法。[6]因此,本文的主题是严格限定的,否则就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一研究。因为在债法外,自然也还存在“理性人”。[7]而且,在国外也有理性人,他在那里甚至得到如下一段颂词(不是很严肃的看法):
总之,(理性人)没有人类的缺点,他没有保留一点恶,没有任何偏见;他不拖拉,脾气不坏,不贪婪,也从不疏忽;对待自己的事和对待别人的事一样。这个完美的、但又可憎的角色,像一座纪念碑矗立于我们的法庭上,徒劳地向他的同胞呼吁,要以他为榜样来安排生活。“[8]
二、理性人的一些特征
3.这里所涉及的“理性人”,当然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常常还是表现出“不理性”的一面。相反,他是一个假设的形象[9](一个思想形象)。在法官裁定相关法律问题时,他被用作指导形象,以衡量法律制度对现实的人有哪些期许。血肉之躯(在相同的处境和情景下[10])应像一个“理性人”那样行为、思考、理解与反应。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现实中的人而言,这样的问题是很明显的:作为其榜样“理性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答案比乍看起来要错综复杂。因为“理性人”不单按照“理性”(Vernunft)的要求从事行为。更确切地说,理性人还体现了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瑞士民法典,第2条)所要求的其他各种品质。这些品质包含在“理性的”(vernueftig)[11]这一词语中。有时,这个词也单独使用。[12]但是,因为“理性人”的这些品质突破了这一词语的单纯字面含义,(使用其他词语)表达更为精确,例如“理性人”也是“善意的”(redlich)、[13]“恰当的”(korrekt)、[14]“正直的”(anst·ndig)、[15]“正派的”(ordentlich)、[16]“认真的”(gewissenhaft)、[17]“忠实的”(loyal)、[18]“审慎的”(besonnen/réfléchi)、[19] “诚实的”(honnête)、[20]“公正的”(juste)[21]“de bonne foi”、[22]“精明的、符合交易习惯的和善意的”(tüchtig ,verkehrsgewohnt und rechtlich denkend)[23]或“勤勉及诚实的”(diligent et honnête)。[24]
有时,也完全不使用“理性的”(vernünftig)这一形容词,而仅仅用“理智的和善意的”(verst·ndig und redlich)、[25]“忠实的、恰当的”(loyal, korrekt)[26]、“恰当的、勤勉的、谨慎、机智、镇定”(correct, diligent, avisé, doté d‘adresse et de sang-froid)[27]以及(类似的)说法取而代之。另外,在其他一些地方,干脆说成:任何人都应以“理性的方式”(“正派的方式”或“忠实的方式”)去行为、理解或者不做出行为。在这里,重点就不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行为了。[28]
4.总之,我们可以相信,“理性人”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诚实信用戒律对人类的形象的假定。这一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形式,是相当多种多样的,只要几个例子就足够说明其扩散之广。依据判例和学说,“理性人”时而是一个纯朴的百姓;[29]时而是一个合同当事人;[30]而且还可能是一个寻求建议的人,[31]一个起重工,[32]一个工人,[33]道路使用者,[34]街道使用者,[35]汽车司机,[36]家父……[37]甚或是一个法官。因为,法官也势必谨慎行为(se montrera prudent)。“[38]
这些例子并不是全部,我们也不能这样理解:“理性人”主要是“男性的”(m·nnliches)存在体。[39]虽然在个别地方,“理性人”明显以“男人”(Mann)的面貌出现;[40]而且,在其他场合,他扮成“理性的男人”(reasonable man),[41]将英美法上的示范形象(Paradefigur)[42]植入瑞士法律语言。然而,这是一个过时的术语,因为“理性的男人”也逐渐被“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取代了。[43]后者早已为我们瑞士法语区的同仁所洞察,他们都使用“personne raisonnable”[44] (法语,“理性人”——译注)或“persona ragionevole”(意大利语,“理性人”——译注)。[45]
三、信赖原则、合同合意以及表示错误
A
5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理性人”出现的具体领域,信赖原则(Vertauensprinzip)应是我们停留的第一站。这一得到普遍承认的原则,[46]指引法官对意思表示做出客观解释,其要旨是,受领者作为一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当时可以和必须如何理解。[47]
对意思表示的解释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也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受领人事实上对意思表示的理解。应该说,其标准是与受领人处于同样情景的“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的理解。他是法官在进行解释不得不求教的一个指导形象(Leitfigur)。他对表示过程的假定的理解,将裁定一个意思表示是否已经发出;意思表示的内容是什么;它是向谁发出的;[48]或者,简而言之,从表意人的行为推断出一个理性人必然会得出的那些结论。[49]
这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主宰了对意思表示的解释,有时他也以其他名称出现:“善意和理性的接受人”[50]:“理智的、善意的判断者”;[51]“忠实的、不犯错误的第三人”;[52]“理性的、正派的市民”。[53]但这一要旨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同样,在下述情况,这一要旨也改变甚少:只是简述信赖原则而不特别提及这一指导形象,即直接说,意思表示应按照相应受领人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可以和必须如何理解来进行解释。[54]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的理解”,[55]这种理解将决定意思表示行为的客观意义。一个意思与该意义相符,无异于宣布它是“有效的(gilt)”。
6.为什么对于意思表示的解释而言,表示出来的(erw·hnten)(客观的,objectiven)意义是重要的?其理由在于交易安全(Verkehrssicherheit)。信赖原则适用的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56]当事人双方都享受这种保护:“表意人信赖对方理性的理解,而接受人则相信表意人(表示了)真实的意思。”[57]这一保护目的使信赖原则正当化了,但同时也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即以下两点:
——首先,一旦确定意思表示的接受人事实上已经正确理解了表意人的意思(即认识到表意人的真实意思),那么,信赖原则就不再适用。因此,此时要求真实的当事人被迫接受一种客观的意思,即一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的假定的理解,就没有任何基础了。毋宁说,意思表示直接依当事人双方表示的一致理解生效。[58]这符合私人自治的基本原则,无需从交易安全的角度来匡正。
——其次,这一原则适用的前提是,(至少)意思表示一方当事人(表意人或者接受人)已经理解了意思表示的客观意义。相反,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意思表示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意义A和B),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理解(意义A和B)与意思表示的客观意义(意义C)相一致,那么,就根本不能主张表示生效。[59]因为,如果此时适用意思表示的客观意义,而这种意义是表示的发出人和接受人都没有认识到的,[60]这就既不符合信赖原则保护的目的,也不符合法律关系(Rechtsverkehrs)的其他要求。一位德国的法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他径直称之为“纯粹的教义学”(schieren Dogmatismus)和“毫无意义(Un-Sinn)的胜利”。[61]
B
7.虽然信赖原则(的适用)存在这两种限制,但在实践中,它还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62]通过这一原则,“善意而理性的人”同样被引入到了中,即合意学说(Konsenslehre)中。[63]因为,瑞士债法第1条要求合同的成立必须存在意思表示合致,对合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以对意思表示的合致进行解释为前提的;而且,该解释也受制于信赖原则,因为判断合同合意是否存在,依据的是“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对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会如何理解。如果判断结果是肯定的,就会形成一个“规范的合意”(“normativen” Konsens),[64]这一合意的基础是一种评价(Wertung),而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对这一观点,需要立刻补充的是:
这种用“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取代真实合同当事人的合同客观理论,在其适用时,只受信赖原则固有的限制。因此,一旦确定了一方当事人事实上正确地理解了另一方的意思,合意就取决于表示出来的真实意思(而不是信赖原则!)。[65]而且,如果一份合同的内容既不是这一方也不是那一方追求的,它就不能是合同。[66]人们努力使合同缔结“客观化”,但有时却顾此[67]失彼[68].
8.我们可以对此进一步讨论。即使一个合意以信赖原则的适用为基础,但对于有效的合同缔结而言,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完全不重要的。即,如果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的表示错误,该合同对他(单方)是没有拘束力的(瑞士债法第23条)。但是,如果他主张该合同不能对他适用,并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过失,那么他就应向对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瑞士债法第26条)。对方的请求权的基础主要是信赖损害赔偿(瑞士债法第26条第1款)。“依据公平原则,法官可以判决当事人承担其他损害赔偿责任。”(瑞士债法第26条第2款)。这里有必要对上述内容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表示错误的前提是,受领人对意思表示的理解与表意人不同,而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受领人可以那样理解。[69]在这种情况,依据信赖原则,意思表示以及(在存在合意的情况下)合同依据意思表示受领人的理解发生效力。其中包括,表示错误只是不重要的错误,或者错误表意人没有(及时[70])主张(unterlaesst)重大错误。
——但如果表示错误性质上是重大的,而且表意人(及时)主张了错误,对意思表示受领人的保护就限于瑞士债法第26条规定的错误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该责任以存在过错责任[71](Verschulden),即以错误是因过失(Fahrlaessigkeit)发生的为前提。这种错误表意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是对他所引起的(已落空的)信赖的一种责任,同时,它也是“缔约过失”责任的一种适用情形。[72]
9.依据上述判断,合同缔结者的表示错误为这种法律状态(Rechtlage)提供了基础:对于非重大的表示错误,合同(以合意为前提)依据意思表示受领人的理解生效。受领人有根据地信赖其理解的内容的效力的,其信赖将“无条件地”受到保护。这是因为,错误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与相对人理解的意思分歧甚微,以至于错误人的利益状态可以不予考虑。相反,在重大错误的情形,错误表意人的利益则也被考虑在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错误表意人享有选择的可能性:
——(首先)错误表意人可以有效宣称,他不受合同拘束。如果他对错误的产生有过错,那么,对意思表示受领人的保护就被限制在瑞士债法第2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上。[73]如果错误表意人没有过错,则意思表示的受领人根本不受保护。[74]
——(其次)或者,错误表意人可以通过不(及时)主张其错误或者明确地主张,让合同依据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的理解生效。[75]如果联系到错误表意人可能的损害赔偿义务(以及他人可能要准备承受的来自社会/商业方面的制裁),合同生效比合同无效给他造成的损害更小,他会往往选择使合同生效(如果他“理性地行为”)。
错误人可以选择(使其意思表示)不生效力,一方面符合“意思理论”(Willenstheorie)的思维财富,另一方面,它和过错责任(瑞士债法第26条)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一道,带来了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与现代思潮一致:重新强化并突出违反“合同”义务(Lasten)行为的“侵权”(Delikt)性质。[76]当然,无论是把瑞士债法第26条规定的责任,理解为“缔约过失”责任(Culpa-Haftung)还是“特殊种类的责任”[77],对此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法学“发现”的目的就在于,不适用不受人欢迎的侵权规则,虽然此时事实上是存在侵权责任的(不存在违约责任)。
D
10. 以上内容可以概括为:只要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受领人对表示的理解,与表意人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有差异,该表示的意义就由信赖原则以及一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意思表示受领人的理解来确定。只要这种客观意义符合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一方面),或者符合受领人事实上所做的理解(另一方面),表示行为就按照其所传递的意义生效。据此,相信意思表示是按照一个理性而不犯错误的法律榜样的理解而产生效力的表意人或受领人,就分别受到了保护。
明确地说,理性的、不犯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的形象规范了:一个真实的人必须如何表达意思,以及对相对方的表示必须如何理解,表意人的意愿或受领人的理解才能获得效力。但该规范在下述情形有所保留:即在确定了受领人事实上已正确理解表意后,意思表示就按照表意人的意愿(以及相对人的理解)而发生效力,而不适用信赖原则(以及“理性而不犯错误的人”的理解)。此外,如果重大的表示错误的缔约人更愿意不让合同对他产生效力(瑞士债法第26条),[78]此时,对受领人信赖的保护也被限制在以过错为要件的损害责任上。
注释:
[1] 参照Keller/Sch·bi, Das Schweizerische Schuldrecht, Band I, Allgemeine Lehren des Vertragsrechts, 3. Auflage,Basel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88,S.57; Gauch/Schluep,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 4. Auflage, Zürich 1987,Nr.190及Nr.197.
[2] 如参照Cohen,Transcendental Nonsense and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Columbia Law Review, 1935,第 809页及以下。
[3] 我将该认识归功于哈佛大学的法律硕士Ra Daniela Gmuender Perrig女士。她在储存于计算机的瑞士民法典和瑞士债法文本中,搜索了“Vernuft”和“vernueft”两个词。
[4] 瑞士债法第267a条第2款。
[5] 参见瑞士民法典第16条。
[6] 但不包括——弗里堡大学法律系(出于实践理性的考虑)将它与瑞士债法教学领域分开了,而将其与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教席。
[7] 例如,区分所有权人(Stockwerkeigentuemer)有义务以一种“理性的、有教养的和想法正常的人”自然会采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解决(BGE 113 II 18)。一个“理性的、负责爆破的官员”,处于同样的情势……会采取危险性更小的爆炸方法,或者警告在危险区域内的人,并采取防止碎片造成伤害的有效措施(BGE 111 Ib 199.)。没有交AHV费用的雇主,应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如果他忽视了一个“合理人”在同样的场合和情景下必定会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BGE 08 V 202 f.)。如果某人担心因程序期限过长而受到损害,而不得不请求加快程序进行,也最多能够提起权利迟延之申诉(eine Rechtsverz·gerungsbeschwerde),因为受害人不能指望得到任何损害赔偿,就必须采取一个理性人在相同情景下会采取的措施。(BGE 107 Ib 158 f.)。对一个尚未达到法律规定的取得驾驶证的年龄的“有教养的、懂事的”儿子而言,如果其父亲不让他取得钥匙,进入车库和开车,他不能因此责怪父亲。(BGE 97 II 258)。对于一个“理性的、正派的人”而言,从具体情形可以得出如此结论:一个重伤员是不允许被探访的,或者未经特别许可是不允许被探访的,这符合治疗机构的意思((BGE 90 IV 77 f.)。
[8] Herbert, Uncommon Law, London, New edition, 1969, p.4.
[9] “一个拟制人,无论在世界哪里都从来没有存在过。”(Prosser/Keeton, The Law of Torts,5ed, St.Paul, Minn.1984,p.174.)
[10] 参照,如Keller, Haftpflicht im Privatrecht, Bd.1, 4. Auflage, Bern 1979,S.85页; J·ggi/Gauch, N 667关于瑞士债法第18条。
[11] 对“合理的”(reasonable)这一措辞,大意参见 Corpus Juris Secundum((C.J.S.), Volume LXXV, Brooklyn,N.Y., p. 634 f.):“‘合理的’被界定为一种适合理性的方式;与理性相协调……它也被界定为具有公正(just)、合适(proper)、公平(fair)、衡平(equitable)的意义;此外,这一术语常常被解释为具有诚实的意义。”
[12] 如 Bucher, S. 29; J·ggi/Gauch, N 667关于瑞士债法第18条;Keller Haftpflicht im Privatrecht, Bd.1, 4. Auflage, Bern 1979, S. 85; BGE 96 II 177; 88 II 436; ZR 72, 1973, Nr. 58, S.143.
[13] (Bucher), S. 122; Gauch/Schluep, Nr. 868, Nr. 917 和 Nr. 920; J·ggi/Gauch, N 498 和 651关于瑞士债法第18条; Von Büren,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 Zürich 1964, S.128.
[14] Von Tuhr/Peter, All-gemeiner Teil des Schweizerischen Obligationenrechts, Band 1, 3. Auflage, Zürich 1979,S.287; Gauch/Schluep, Nr. 190, Nr. 197 和 Nr. 868; AGVE 1983, S. 32.
[15] Bucher, 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age,Zürich 1988,S. 182, 188.
[16] Von Tuhr/Peter, S.429.
[17] Rep. 1984, S.366.
[18] Kuhn, SJZ 82, 1986, S.348.
[19] Deschenaux/Tercier, La Responsabilité Civile, 2. Auflage, Bern 1982,S. 83, Nr. 27.
[20] Partie Général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2. Auflage, Zürich 1982, Nr. 835 ,Nr. 885; Engel Traité des Obli-gations en Droit Suisse, Dispositions Générales du CO, Neuchatel 1973,S. 167.
[21] Yung L‘Interprétation Supplétive des Contrats, in: YUNG, études et Articles, Mémoires Publiés par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Genève, Nr. 32, 1971, S. 207.
[22] Yung, L‘Acceptation par le Silence d’une Offre de Contracter, in:YUNG, études et Articles, Mémoires Publiés par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Genève, S.210.
[23] Von Büren,S. 128.
[24] Engel, S. 154.
[25] Gauch/Schluep, nR. 197; Sch·nenberger/J·ggi, N 195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26] ZR 87, 1988, Nr. 79, S.185.
[27] Engel, S. 313.
[28] BGE109 II 329; 99 II 396; 94 II 104 f.; 92 II 348; 91 II 209.
[29] Bucher, S. 182.
[30] Gauch/Schluep, Nr. 917; J·ggi/Gauch, N 332, 342 和 498关于瑞士债法第18条。
[31] Kuhn, Sjz 82, 1986, S,348.
[32] BGE 92 II 241.
[33] Guhl/Merz/Kummer, Das Schweizerische Obligationenrecht, 7. Auflage, Zürich 1980,S.161.
[34] BGE 96 II 36.
[35] BGE 95 II 578.
[36] BGE 92 II 255.
[37] Guhl/Merz/Kummer, S.161.
[38] BGE 109 II 329.
[39] 与此相反,苏黎士地区法院(Bezirksgerich)在一个古老的判决中,表达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歧视观点(被联邦法院判决不恰当、不正确):“在司机碰到女人、牛和母鸡时,司机根据经验无法预料,他们会向哪边避让;但在碰到男士时,司机却始终可以预计他们可以做出恰当的行为。”(Neue Zürcher Zeitung vom 25. 3. 1925, Nr. 466, Blatt 5)
[40] 如参见Von Tuhr/Peter, S.287; Becker, N 1关于瑞士债法第96条; Von Büren, S. 128.
[41] 如参见Gauch/Schluep, NR. 1634b f.
[42] 详见Flem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orts, 2nd. edition, Oxford 1985 p. 22.
[43] 详见Fletcher, The Right and the Reasonable, Harvard Law Review, 1985, p. 949; Prosser/Keeton, zit. in Anm. 10, S. 173 (§ 32: "The Reasonable Person")。
[44] 参见Yung, L'Interprétation, S. 207; Deschenaux/tercier, S. 83, Nr. 27;Gauch/Schluep/tercier, Nr.835 和 885.
[45] 参见Yung, L'Interprétation, S.207; Deschenaux/Tercier, S. 83, Nr. 27; Gauch/Schluep/tercier, Nr.835 和 885.
[46] 详见Krammer, N 37 f.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47] 参见如Gauch/Schluep, Nr. 190; Oftinger,Bundesgerichtspraxis zum Allgemeinen Teil des Schweizerischen Obligationenrechts)Band 1, 4. Auflage, Zürich 1975,S.46; Sch·nenberger/J·ggi, N 195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Von Tuhr/Peter, S.28 7; 另参见Bucher, S. 122.
[48] 参见Gauch/Schluep, Nr. 189.
[49] Bucher, S. 29.
[50] 参见Bucher,S.122.
[51] 参见Sch·nenberger/J·ggi, N 195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Gauch/Schluep, Nr. 190 和 197.
[52] ZR 87, 1988, Nr. 79, S. 185.
[53] Bucher, S. 182.
[54] 参见如BGE 113 II 50; 详见BGE 111 II 287 ;Guhl /Merz / Kummer, S.91; Krammer, N 37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55] Oftinger, Bundesgerichtspraxis, zit. in Anm. 48, S. 46.摘自前注48, S. 46.
[56] Meier-Hayoz, Das Vertrauensprinzip beim Vertragsabschluss, Diss. Zürich 1948, S. 120.
[57] Guhl/Merz/Kummer, S. 91.
[58] BGE 105 II 19 f.; Krammer,N 30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Gauch/Schluep, Nr. 193 及以下进行了大量的引证。
[59] Gauch/Schluep, Nr. 200.
[60] 这样的观点,参见Keller, SJZ 57, 1961, S. 317 f.以及Keller/Sch·bi, S. 132.
[61] Jahr, Geltung des Gewollten und Geltung des Nicht-Gewollten, Juristische Schulung,1989, S.252.
[62] 这也关系到举证责任的配置。如果谁提出反对信赖原则的适用的理由,就应承担举证责任。
[63] 参见Bucher, S.122.
[64] Krammer, N 126 ff.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65] Gauch/Schluep, Nr. 286 ff. und Nr. 317; MERZ, ZBJV 117, 1981, S. 124.
[66] Bydlinski, Die Grundlagen des Vertragsrechts im Meinungsstreit, BJM 1982, S. 1 ff. (S. 15);Gauch/Schluep, Nr. 323; Krammer, N 102 a.E.关于瑞士债法第1条; Piotet, ZBJV 121, 1985, S. 151.
[67] 参见BGE 64 II 11.
[68] Keller/ Sch·bi, S. 132.
[69] Gauch/Schluep, Nr. 610; Von Tuhr/Peter, S. 301.
[70] 瑞士债法第31条。
[71] 瑞士债法第25条有所保留。
[72] BGE 113 II 31在(涉及基本错误时)提到,[错误表意人的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einer "Haftung eigener Art"),以与侵权责任(瑞士债法第41条)划清界限。
[73] 原则上说,也即对信赖损害(Vertrauensschadens)的赔偿。
[74] 为了防止合同全部无效(同时还可能产生或者不产生损害赔偿),意思表示的相对人毕竟至少可以让合同按照错误人对意思表示的理解使合同生效。(瑞士债法第25条第2款)。
[75] 这种同意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使仅对单方有拘束力的合同生效(瑞士债法第23条)。这种“解释”(Konstruktion)与“无效理论”(Ungültigkeitstheorie)一致。瑞士联邦法院目前也认为,这种理论有其优点。(BGE 114 II 142 及以下)。后者(错误表意人不主张错误——译注)虽然是正确的,但因为受“撤销权理论”“通说”的制约,瑞士的民法理论对此几乎没有积极响应。
[76] 参见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1979 (Paper back Ausgabe 1988), p.733;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Boston 1972, p.46. 一般性详述参见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1974.
[77] BGE 113 Ⅱ 31.
[78] 但请注意瑞士债法第25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