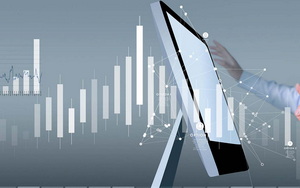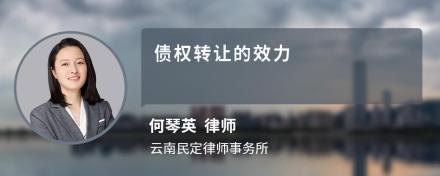德国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之研究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2019-07-15 12:58
人浏览
德国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Normative Wirkung)与“债权性效力”(Schuldrechtliche Wirkung)的区分理论奠定了德国集体劳动法的理论基础。任何一本德国劳动法的教科书或评注都是以“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相区分作为集体合同法展开的基本框架的。这种区分在德国法上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史尚宽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劳动法原论》中就曾介绍过这一重要理论,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的“集体合同法”中也可以看出该理论对我国立法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法学界迄今尚缺乏对这一核心理论的深入研究。笔者有理由认为,该理论的研究将对我国劳动法至少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基础理论的明晰有助于我国集体合同具体制度特别是集体合同主体、效力等制度的合理建构;从理论发展层面看,深入分析这一理论将为论证劳动法与私法之关系提供有力论据。因此,深入考察这一核心理论是构建我国集体合同法乃至劳动法理论的基础性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的内涵和核心
(一)“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的内涵
德国集体合同的“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在立法上的表现是《德国集体合同法》。该法第1条第1款规定:“集体合同规范集体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它还包含法规性效力内容,即对于劳动关系的建立、内容和终止以及企业规章或企业组织法上的规范具有法规性效力。”该款前半部分规定的是“债权性效力”的内容,具体以集体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为体现,其内容按照德国劳动法学界的通说,主要是当事人的履行义务、和平义务;后半部分规定的是“法规性效力”的内容,包括受到集体合同约束的当事人成员个别劳动关系的成立、内容与终止,以及有关企业劳动规章、企业组织法上的权利规则。
德国集体合同的“法规性效力”内容与我国集体合同中劳动标准条款相似,其效力的体现包括三个层面,即对于该集体合同当事人(工会或雇主/雇主组织)所属成员的劳动合同、企业规章以及企业组织法具有强制性(Unmittelbare und zwingende Wirkung)、不可抛弃性(Unverbrüchlichkeit)和余后效力(Nach-wirkung)。“债权性效力”的内容主要包括集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负有的履行义务、和平义务,凸显集体合同也具有债权相对性的特征。
(二)“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的核心
由上可见,德国集体合同“债权性效力”的内容是集体合同作为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约束,也是集体合同作为“私法上契约”的题中应有之义,体现了集体合同作为私法合同的基本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集体合同认定为私法上契约,则无法解释契约当事人———工会或雇主/雇主组织———通过契约为其成员(劳动者或雇主)设定强制性权利或义务的行为,因为这明显突破了契约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突破奠定了劳动法的不同于私法释义学(Rechtsdogmatik)的劳动法释义学(Tari-frechtsdogmatik)基础。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在有着深厚私法传统的德国,构建突破了私法释义学的“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的区分理论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产生对劳动法的发展影响如何?在现代德国劳动法中这一理论又有什么新的发展?笔者力图在本文中勾勒出集体合同效力理论来源于私法,最终又与私法相分离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集体合同效力的理论与立法状况。
二、集体合同私法效力的确认———集体合同效力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一)集体合同私法效力的立法障碍———私法中“人”的局限
19世纪德国法对集体合同的性质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当时的立法看,立法者对于工人结社(Koali-tion)持较为负面的态度,工人们通过残酷的斗争达成的集体合同完全是工业化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直接驱动的结果。但是,这种联合破坏了“私人自治”中对人的基本假设,在以完全个人主义为宗旨的法律理念中难以取得私法上契约的效力。1845年《普鲁士工商业管理条例》规定对参与结社的劳动者处以刑罚。普鲁士统一北德后,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同盟通过《工商业管理条例》,废除了对工人结社的禁令。1869年《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68条规定对工人的结社自由解禁,但第169条规定,凡有人通过人身强制手段、威胁、损害名誉或者通过诽谤性宣传,命令或者企图命令别人参与这样的结社或者服从结社的协定结果者,或者使用同样的方法阻止或企图阻止别人退出这种结社,如按照普通刑法不涉及更为严厉的惩罚,则将被处三个月以下的监禁。这一规定不仅表明社团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该团体,法律不介入社团成员内部的任何事务,而且在实质上使得该社团无法在内部为其成员设置任何法律义务。
从法律性质上说,1869年《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69条的规定保障并且仅仅保障劳动者的“消极同盟自由权”。这样的立法以个人自由作为团体形成的绝对前提。据学者考察,这种规定是基于以消极的同盟自由为完全上位的个人主义,或者可以说是以完全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团体法思想而来。《工商业管理条例》虽然取消了工人结社的禁令,但其通过保护工人消极同盟自由权的方式,实际上否认了“团体”作为法律行为主体的可能性。正如德国劳动法之父辛茨海默(Sinzheimer)教授所言,当时的法律以“个人”作为法律制度的核心,这种个人主义的法律观阻碍了“集体”法律行为在法律中的发展。1871年德国统一后,这部分立法内容被《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52条和第153条完全吸收。
(二)司法对集体合同效力的定位———自由退出的“结社”
集体合同作为与传统合同完全不同的法律形式,由于合同主体不符合私法上对法律行为主体的假设,最初并没有受到法学界与实务界的重视。集体合同订立后,其履行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保障,完全以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信念与利益为履约保证。当工会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雇主同意选择集体合同作为平息劳资斗争的结果时,集体合同大量发展起来,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也大量增加,向法院起诉的劳资纠纷也在短期内迅速增多。德意志帝国法院(以下简称帝国法院)通过对当时立法的解释和司法实践,否认了集体合同在私法上的效力。1903年,帝国法院针对集体合同的一则判决对德国集体合同的效力判定曾在短期内产生重要的影响。帝国法院的解释是,集体合同在性质上应当定义为《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52条中的结社。另外,根据该法第153条的规定,任何人可以随时退出该类结社,因此集体合同可以随时收回并且在法律上不具有可诉性。[page]
上述判决奠定了20世纪初期帝国法院审理集体合同案件的基本方向。此后,各地方或州法院的判决大都坚持帝国法院对集体合同的态度,将集体合同定义为《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52条中定义的结社,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退出。在《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的立法者与帝国法院的法官看来,该合同虽然也被称为集体“合同”(Tarifvertrag),但本质上并非契约。因为如果集体合同具有履约强制力,则颠覆了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签订合同的“团体”如果强迫其会员或其他工人接受该合同的约束,那么显然是对个人意思自治的破坏。依当时的司法理念,“私人自治”为最优先保护的法律价值,在集体合同与私人自治相冲突时,司法的态度是采用刑罚手段优先保护私人自治。
(三)学理的发展与司法的重新解释———集体合同私法效力的确认
帝国法院的上述判决在实践中严重影响了集体合同的发展。19世纪著名的社会改革者布赫塔诺(Lujo Brentano)有一句形容此种现象的传神之语:“毫无疑问工人有同盟自由权。但只要他们行使,就构成刑事犯罪”。就是当时的国务大臣尼博得林(Nieberding)1908年在帝国议会的一次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53条的规定根本不允许集体合同的产生。”
由于在法理上缺乏说服力,该判决的理由遭到了法学家们的猛烈抨击。辛茨海默称之为“难以解释的谬误”。针对司法上将集体合同解释为结社的观点,当时著名的劳动法学家罗特玛(Philipp Lotmar)教授认为,集体合同并非结社,两者性质明显有别。工人结社最重要的特征是当事人以追求更好的劳动条件与更高的工资为行动目标,而“集体合同是劳工与雇主作为当事人签订的,它并不以追求更好的劳动条件和更高的工资为目的,只是将谈判达成的条件固定下来。”换言之,集体合同符合私法上合同的定义,应当确认其合同法上的效力。
1910年1月20日,帝国法院在另一则判决中终于修正了将集体合同等同于结社的观点。在这则判决中,法院承认集体合同的私法效力,当事人违反合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管签订者是有能力社团还是无能力社团,集体合同的有效性……最终抛开一切质疑被确定下来。”至此,集体合同被视为《德国民法典》债编中的“无名合同”,其履行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的团体对其成员施加压力的方式进行。这一判决被视为“德国集体合同宪法史上的里程碑”。
三、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的推衍———集体合同效力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一)集体合同法律性质的再探讨———私法理论捉襟见肘
1.集体合同定性探讨
虽然大多数法学家反对帝国法院于1903年确定的集体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但在法学家内部对集体合同的法律性质也长期存在争论。在新的理论框架没有确立之前,他们在原有的私法框架内寻找、比较与集体合同性质相近的合同,理解集体合同与其他合同不同的性质。集体合同是劳动合同还是预约,是和解协议还是公司章程,或者是利他合同?学者们在私法框架内进行了各种探索。
由于集体合同约定的雇主向雇员给付工资或劳动条件等内容并非为工会的利益,而是工会成员的利益,因此许多法学家认为,将其性质定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较为妥当。客观地说,在以上所有合同中,集体合同的性质最接近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但是,辛茨海默提出了他的疑虑:“工会成员作为集体合同的受益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给付,但也可以放弃该利益,往往雇员(工会成员)可能在雇主强势地位影响下自动放弃集体合同上的利益,从而导致个体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低于集体合同的标准。”
帝国法院在上述1910年的判决中将集体合同作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行为,没有在私法领域之外为其创制特别规则,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只能在现有私法体系之外创造出集体合同效力理论才能解决。理论准备的系统化是异常缓慢的过程。不过,随着学者们逐渐深入地研讨以及司法实务经验的积累,德国劳动法学界开始慢慢形成对集体合同的一致认识。
2.集体合同法律效力探讨
传统合同相对性理论难以解释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从而引发了当时德国法学家的激烈争论,下文将对当时争议的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1)集体合同的主体界定。集体合同与一般合同的显著区别是,后者以个体作为当事人,合同的违约责任也应由个体承担。而集体合同是工会代表工人与雇主/雇主组织签订的合同,如何界定集体合同的主体?该问题是解决集体合同法律效力的前提。在确定集体合同对人的效力范围时,当时德国法学界有以下三种理论:一是代表理论,该理论由罗特玛创立;二是团体理论,辛茨海默和学者胡戈林、俞特曼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三是组合理论,学者沃布林是该理论的创立者。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法学界,以“团体”为法律主体的理念尚没有被人们接受,因此辛茨海默的团体理论奠定了集体合同法理论的基础。
按照代理理论,由于团体(工会和雇主组织)是作为团体成员的代理人签订集体合同的,因此团体成员按照合同均单独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又由于代理的法律基础是成员的授权,因此,团体应当在成员大会上选举代理人签订集体合同,或者通过大会决议的方式追认一开始并没有全权授权签订的集体合同。如果被代理人没有全权委托或者没有特别许可授权团体作为代理人,也可以通过之后的默示或明示的方式进行授权。而团体理论与代表理论恰恰相反。按照团体理论,集体合同的当事人仅仅为签订合同的团体(少数由没有组织化的集体签订的合同不在考虑之列),团体成员通过团体与该合同产生法律上的联系,该合同并不及于成员个人。组合理论则是将单个团体成员与团体都看作合同的缔约方。因为在实践中团体大部分时候是其成员利益的代表,但团体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团体理论的产生是德国集体合同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如前所述,正是基于团体观的法律思想,辛茨海默发展了“团体”在集体合同法上的特殊定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德国私法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当个人意思与团体意思相左时,法律不再如同早期司法那样以维护个人的意思自治为最高原则,而是承认团体对个人有一定程度的强制作用。
(2)集体合同的违约责任。集体合同对合同主体的界定直接决定了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按照帝国法院的判决,集体合同等同于一般合同,当一方违反合同时,另一方可以依照《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请求损害赔偿。[page]
根据上述诸种理论,承担集体合同违约责任的主体各不相同。按照代理理论,由于团体的每个个人都直接受合同约束,因此违约责任应当由单独的个人承担,团体则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依据团体理论,团体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然而,团体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责任?应否为个人的违约承担责任?辛茨海默此时提出了“影响义务”学说。团体如果对其义务不作为或疏忽履行则应对成员的违约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工会成员违反和平义务举行罢工,工会的影响义务是:第一,工会不能组织其成员罢工,也不能强化这种行为如保护罢工纠察线、支付罢工费用等;第二,工会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尽力阻止成员参加罢工,如管教“野猫罢工”的发起者、剥夺工会中罢工者的会员资格。然而,当时要实现“影响义务”在法律上最大的阻碍在于《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53条禁止社团对其成员实行纪律化管理的规定。后来德国集体合同立法吸收了辛茨海默的观点,“影响义务”才在现代德国集体合同法中体现为社团对其成员的“敦促义务”。
(二)集体合同的强制效力———私人自治语境下不成功的尝试
集体合同的强制效力是集体合同法律问题中最具争议的话题,是其作为劳动规范合同“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包括如下几个问题:(1)集体合同的内容是否自动成为受集体合同约束的个人劳动合同的条款?(2)违反集体合同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3)个人能否在劳动合同中排除集体合同的适用?如果说承认集体合同的私法效力是法律开始从原来“个人”的单向性思维扩展到“团体”并赋予团体与私人平等的法律地位的话,那么承认集体合同的强制效力即意味着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团体意志优先于个人意志。在这里,私法的个人主义思维受到了限制,市民社会中一种新兴的法律理念开始产生。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基本法》以同盟自由权的名义确认了这种理念在现代社会的正当性。这也是德国法律体系成熟的标志。
集体合同强制效力的争论在法学界始于罗特玛。尽管他在私法领域建构的强制效力理论并不成功, 但却开辟了集体合同法律效力“另辟蹊径”的源头。罗特玛是德国法中“集体合同强制效力”的发现者,他对集体合同强制效力的理解来源于对集体合同的目的解释:“如果集体合同不具有强制效力,那么通过集体合同达到维护劳工利益及工业和平就没有意义”。罗特玛坚持在私法框架内用私法释义学的方法来推导集体合同的强制效力,理由有三:(1)一个由大多数人同意即签订的合同,不能够通过与个别团体成员逐个约定的方式被推翻;(2)一个违反集体合同的个体劳动合同也违反了集体合同签订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因为当事人签订集体合同是为了尽可能地执行该合同;(3)集体合同的功能与《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34条、第154条规定的企业内部规章(Arbeitsordnung)相似,而按照第134第3款的规定企业内部规章具有绝对效力,因此集体合同也应当具有绝对效力。
然而,罗特玛的上述三点理由很难为当时的学者们所接受。例如,辛茨海默认为罗特玛的三个理由在私法领域内都是站不住脚的,甚至罗特玛将集体合同与《帝国工商业管理条例》第134条规定的企业内部规章的类比也是失败的,因为第134条确定的企业内部规章是雇主单方面制定的。这种企业内部规章尽管具有法律效力,但并非强制性的效力,雇主和雇员完全可以通过约定予以更改。
(三)“法规性效力”的理论建构
辛茨海默对代表理论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他否认集体合同强制效力的必要性。辛茨海默之所以拒绝罗特玛的“强制效力”理论,原因在于他认为完全从私法释义学出发很难推导出集体合同法的强制效力。在私法框架内,一个违反集体合同的个人劳动合同应当是有效的,无法令人信服地将其解释成无效。在发现这种理论尝试不成功后,辛茨海默开始尝试用社会自治思想来构建集体合同的法律理论。
1.辛茨海默的社会自治思想
辛茨海默本人的学术思想来源较为多元。从法学方法上,他深受法律社会学家埃里西(Eugen Ehrli-ch)的影响,形成了强烈的法律社会学思维。在价值取向上,他不仅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劳动者的权利始终十分关注,而且也受了基尔克(Otto von Gierke)思想的影响,他的社会自治思想有许多来源于基尔克的自治理论。因此,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劳动法学者,在“魏玛时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
针对当时德国私法无法解决集体合同法律效力的难题从而造成社会问题及社会压力的现象,辛茨海默批评了议会制政府立法的弱点。他认为:“传统的立法程序太过于僵化与刻板,以至于法律经常在刚生效就已过时。从法律需求到具体的法律规定是如此的遥远,因而法律与社会之间经常存在矛盾,仅仅通过立法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呢?基尔克研究德国合作社的历史后认为德国历史上的行会、农业协会等都存在自治法规。辛茨海默引用了基尔克的研究成果,于是将自治的概念发展为“社团的自治法规(autonomischen Rechtssetzung)”。辛茨海默指出:“基尔克认识到法律创造的自由价值具有自我管理的力量。”由此可见,由社会直接立法实现社会自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最好的例证就是劳资团体签订的集体合同。虽然法律没有承认集体合同的特殊地位,但辛茨海默认为,应当通过社会组织自治的方式赋予社会组织力量,即赋予集体合同双方构建的法律关系与国家法同样的效力。他认为,集体合同的发展实质上已经是社会自治的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大范围实践,只不过因落后于社会的法律而不肯被承认罢了,因此应当承认团体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的性质,这就是今天德国集体合同法上“法规性效力”的理论起源。辛茨海默认为,在国家特别是议会制国家发生结构性变革的今天,“社会直接立法”代表了法治发展的基本方向,而社会自治的目的也是分散国家的集中立法。
2.团体主义法律观的落实———辛茨海默对集体合同效力的构建与立法的吸收
在社会自治思想的指引下,辛茨海默设计了不同于私法释义学的劳动法释义学,其最主要的应用对象即集体合同的效力问题。如前所述,在集体合同取得私法效力之后,如何确定合同的当事人直接决定着集体合同效力的作用范围与违约责任的承担。辛茨海默坚持团体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劳动规范合同”(Arbeitsnormenvertrag)理论。劳动规范合同理论将集体合同的效力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集体合同的“债权性效力”。在这个层面上,该理论主要采团体理论学说。也就是说,集体合同的当事人应为工会与雇主/雇主组织而非劳动者个人,集体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具有履行义务与和平义务,因此合同的主体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主体是团体而非个人。第二个层面即为规范性效力层面。这一时期集体合同的“法规性效力”由于尚未得到宪法的授权,因此尚不能称之为“法规性效力”,而仅仅具有自动进入个体劳动合同的规范性效力。在规范性效力层面,受到约束的对象为集体合同签订团体的成员。1918年在德国威廉皇帝退位后,获得政权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通过了德国《集体合同规定》(Tarifvertragesverordnung简称TV-VO)的法案。TVVO在很大程度上以辛茨海默提交的草案为依据,第一次在立法中确定了规范劳动关系双方劳动条件的集体合同具有规范性效力,奠定了集体合同效力理论的法律基础。至此,集体合同效力理论的构建基本完成。[page]
(四)现代德国法对集体合同效力理论的发展
辛茨海默的社会自治思想作为德国劳动法的思想传统,不仅影响了《魏玛宪法》,而且对《德国基本法》也有重要的影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以及学说的发展,确立了《德国基本法》第9条第3款为劳资自治的宪法来源,也是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因为集体合同并非国家立法,其在现代德国取得“法规性效力”的权力来源是宪法委托。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劳资自治”(Tai-fautonomie)是宪法托付工会与雇主及其组织在同盟自由的范围内以保护和改善劳动、经济条件为目的在劳动生活的范围内享有的管辖权。集体合同双方就工资与劳动条件自行达成协议,国家不予干涉。换言之,国家在劳动生活中放弃了国家法的手段,任凭力量相当的劳资双方通过集体合同的方式约定工资与劳动条件。按照今天德国法上的通说,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的来源为“国家立法权的授予”。
四、德国集体合同效力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与“债权性效力”理论的区分建立在私法释义学上的突破。在社会自治理念下建立“法规性效力”后,德国劳动法通过自身逻辑实现了对集体合同的引导。这种新的法律推理和解释方法与原有的法律部门之间能够保持沟通与对话。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合同立法既不符合私法释义学的基本逻辑,又没有如同德国法那样构建出劳动法释义学。虽然现阶段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尚不发达,集体合同的订立又被排除出司法的视阈,立法的重大缺陷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理论上的补充与发展已势在必行。
(一)我国集体合同不具有“债权性效力”
德国集体合同“债权性效力”理论具有两点重要特征:(1)受“债权性效力”约束的当事人应为签订集体合同的团体;(2)当事人在债法上的义务主要为履行义务与和平义务,当事人如果违反债法上的义务,对方可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集体合同是否具有“债权性效力”,在合同法与劳动法上均无明确规定。考察相关立法,可以发现我国集体合同并不具备所谓“债权性效力”的特征:(1)根据我国《集体合同规定》第3条的规定,集体合同的当事人是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二者并不具备团体的特征。因此,从法理上将这种合同认定为集合的劳动合同或多数劳动者同时成立的劳动合同的集合,似乎更为合理。(2)集体合同“债权性效力”的作用是约束合同双方,促使其在约定的范围内承担履行义务与和平义务。如果双方意思悬殊,在合同规定的义务之外由双方采用包括劳动斗争在内的方式自行解决争议。但是,我国《集体合同规定》第32条、第3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书面提出协调处理申请;没有提出申请的,劳动行政部门可视情况进行协调处理,协调处理结束后,最终制作《协调处理协议书》。立法者的意旨很明确:劳动斗争的手段是禁止的,即使双方就集体合同达不成合意,也应当由政府进行协调,而不能采取斗争的手段。至于履行义务,由于和平义务并不存在,主要合同义务又有强制效力的规范,因此团体的履行义务对集体合同并不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我国集体合同并不具有“债权性效力”。
(二)我国集体合同强制效力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虽然并未确认集体合同的“债权性效力”,但吸收了德国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下的强制效力理论,只是对“法规性效力”有明显的误读。德国法中“法规性效力”理论来源于辛茨海默的社会自治思想,其最为重要的意义是要在劳动生活领域实现团体自治权,因此“法规性效力”的作用范围只能及于团体成员。反言之,若雇主雇佣非工会成员,则“法规性效力”对该劳动合同不能产生作用。与德国法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以及我国《集体合同规定》有关集体合同效力的条款非常清楚地表明,集体合同的强制性效力不仅及于签订集体合同当事人的成员即工会成员,同时对于非工会成员也具有强制性效力。特别是在集体合同的签订层次为行业性或区域性时,这种强制效力的扩大更为明显。
我国集体合同强制效力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1)集体合同的强制效力来源。德国劳资团体自治经历了从单纯私法释义学到建构劳动法理论的转变过程,最后由《德国基本法》一锤定音真正加以落实。正是由于《德国基本法》保障了“同盟自由基本权”,集体合同的“法规性效力”才获得国家的确认。相比之下,我国宪法并未规定集体劳动权,只是在《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具体法律中有限承认了劳动者结盟以及团体交涉权,但并没有对集体合同能够取得强制效力作出充分说明。(2)集体合同的效力范围。
立法者如此规定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集体合同效力的优位规定来达到保护劳动者的目的,但其中的不妥之处也是明显的,概而言之有二:(1)强迫非工会成员接受集体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显然违反了私法中的基本价值判断规则,“即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德国集体合同“法规性效力”缘起于辛茨海默的社会自治思想,受到《德国基本法》对劳资自治制度的保障才最终确定为劳动法释义学,并且这种释义学在当代还饱受部分学者的指责。相比之下,我国立法在没有任何理论准备也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规定现行集体的合同强制效力实为不妥。(2)从立法的引导方向看,非工会会员与工会会员一样享有集体合同规范的劳动条件,有可能导致劳动者鲜有动力参与工会以促进劳动条件的提升,社会自治在这样的制度导向中不仅没有发展成熟之可能,反而会因为外部人都可以“搭便车”而失去吸引力。
参见史尚宽:《劳动法原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127-132页。
Vgl.Wiedermann/Thuesing, Tarifvertragsgesetz, C.H Beck 2007,§1Rn. 864.
Vgl.Thomas Blanke (Hrsg), Kollektives Arbeitsrecht Quellentexte-zur Geschichte des Arbeitsrechts in Deutschland I, Rowohlt,S.33, S.60.[page]
Vgl.Thomas Blanke (Hrsg), Kollektives Arbeitsrecht Quellentexte-zur Geschichte des Arbeitsrechts in Deutschland I, Rowohlt,S.33, S.60.
参见张鑫隆:《德国同盟自由概念的原点》,《宪政时代》2006年第3期。
Vgl.“Tarifrecht-Einigungswesen”,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 Reform, 6. Hauptversammlung zu Düsseldorf 1913,in: Schrif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 Reform, Heft 45/46, Jena 1914, S.19 (Referat Sinzheimer).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院判例从未明确表示集体合同属于合同并具有合同的约束力。英国法中的集体合同仅仅具有“君子协定”的性质,系没有法律拘束力的道德协议。因此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相关因素的影响,也就不可能产生今天德国法上的集体合同效力理论。考察这个过程中德国劳动法为何能够发展出不同于私法释义学的集体合同理论对今天的劳动法研究意义重大。参见王泽鉴:《英国劳工法之特色、体系及法源理论》,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在该案中,建筑行业协会的工人与雇主协会第七委员会签订了建筑工人工资的集体合同,但雇主仍然与一名协会成员达成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工资约定。建筑行业协会就此曾多次威胁该名工人要封锁其劳动,并要求雇主必须遵守工资协议。Vgl.Entscheidungen des Reichsgerichts in Strafsachen , Bd.37,S.236,zitiert nach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S.105.
Daubler, Das Arbeitsrecht 1, Rdnr. 87, 89.
Vgl.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 1977, S.107.
Hugo Sinzheimer, Rechtsfragen des Arbeitstarifvertrags, in: Schrif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 Reform, Heft 44, Jena 1913,S.9.
罗特玛是德国最早探索集体合同性质的学者。Vgl. Sandro Blanke: Soziales Recht oder kollective Privatautonomie? Mohr Siebeck,Tübingen 2005,S.9-12.
Vgl. Philipp Lotmar, Der Arbeitsvertrag nach dem Priv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1. Bd, Leipzig 1902,S.48.
Vgl.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 1977, S.107.
“Sozial Praxis”, 19.Jg., Nr.24, 17.3.1910, Sp.617,zitiert nach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1914, Lang,S.107.
罗特玛指出,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最重要的相区别是:集体合同只为将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或劳动条件,而劳动合同仅仅规范当下成立的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有学者据此认为,集体合同实际上是劳动合同的预合同(Vorvertrag),是“约定订立合同的合同”,即当事人在预约中约定未来合同的主要或全部内容,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时间订立本约(Hauptvertrag)。针对该观点,罗特玛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预合同签订后,如果不签订主合同,则预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集体合同的效力并不受事后劳动合同是否签订的影响。因此,劳动合同不是预合同。Vgl Philipp Lotmar, Der Arbeitsvertrag nach dem Priv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1. Bd, Leipzig 1902,S.93f.,zit-iert nach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1977,S.111.
学者沃布林(Paul Wülbling)认为,集体合同作为和解而产生的合同的观点并不成立,因为根据当时《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的规定,和解的前提是在一个业已形成的法律行为内部产生了法律争议。而且对于劳资关系来说,已经形成的法律行为仅仅是单个的劳动关系,调解只能在单个劳工与雇主之间进行,其结果并不产生集体合同;如果对已经存在的集体合同产生争议而进行的和解,那只是对已经形成的集体合同的变更或补充。Vgl Paul Wülbling Der Akkordvertrag und der Tarifvertrag, Berlin 1908,S.312,zitiert nach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1977,S.112.
学者胡戈林(Albert Hüglin)认为,集体合同不符合公司章程的最基本特征,集体合同制定后仅仅要求当事人执行合同,并没有为对方设立一项共同的目标。Vgl.Albert Hüglin,Der Tarifvertrag zwinschen Arbetisgebern und Arbeitnehmern in Deutschland , in: MünscherVolkswirkschaftliche Studien, hrsg. L. Brentano,76.Stück, Stuttgart /Berlin 1906, S.26f.
Vgl. Hugo Sinzheimer, Der korporative Arbeitsnormenvertrag, Teil 2, Leipzig 1908,S.146.
Vgl.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 1977, S.20.
Vgl. Philipp Lotmar, Der Arbeitsvertrag nach dem Priv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1. Bd, Leipzig 1902, S.796ff.
Vgl. Hugo Sinzheimer, Der korporative Arbeitsnormenvertrag, Teil 2, Leipzig 1908,S.67.
Vgl.Paul Wülbling,Die gesetzliche Regelung des Tarifvertrags,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hrsg. E. Jaffe,29. Bd., Tübingen 1909,zitiert nach Peter Ullmann:Tarifvertrage und Tarifpolitik in Deutschland bis 1914, Lang,1977,S.112.
Vgl.Hugo Sinzheimer: Ein Arbeitstarifvertrag-Die Idee der sozialen Selbstbestimmung im Recht, München und Leipzig,1916,S.46-56.
Vgl. Hugo Sinzheimer, Der korporative Arbeitsnormenvertrag, Teil 2, Leipzig 1908, S.66.
Abdulkadir Yurtsev, Die Bedeutung des Günstigkeitsprinzips bei der Abanderung von Sozialleistungen durch Tarifvertrag und Be-triebsvereinbarung, Inaugural-Dissertation 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 t der Kiel Universit? t 1996, S.37.
Vgl. Lotmar, Die Tarifvertrage(1900),S.106-115;ders.; Arbeitsvertrag, Bd.1(1902), S.780-788.
Vgl. Sandro Blanke: Soziales Recht oder kollective Privatautonomie?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5, S.7.
Vgl. Sandro Blanke: Soziales Recht oder kollective Privatautonomie?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5, S.12-35.
Vgl. Korsch, Der tote Sinzheimer und der lebende Marx(1923), in: Buckmüller(Hrsg.),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d.2(1980), S.537-541.[page]
Vgl.Hugo Sinzheimer: Ein Arbeitstarifvertrag-Die Idee der sozialen Selbstbestimmung im Recht, München und Leipzig,1916, S.181-186.
Vgl.Hugo Sinzheimer: Ein Arbeitstarifvertrag-Die Idee der sozialen Selbstbestimmung im Recht, München und Leipzig,1916, S.181.
Vgl.Hugo Sinzheimer: Ein Arbeitstarifvertrag-Die Idee der sozialen Selbstbestimmung im Recht, München und Leipzig,1916, S.183.
Vgl.Klaus L. Alberecht: Hugo Sinzheimer in der Weimarer Nationalversammlung, Sein Beitrag zum wirtschaftlichen Ratesystem undzu den arbeits und wirtschaftsrechtlichen Grundrechten der Reichsverfassung, Inaugural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grades der Re-chtswissenschaftilichen Fakult? t d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 t zu Frankfurt am Main,1970,S.102-103.
Vgl.Hugo Sinzheimer: Ein Arbeitstarifvertrag-Die Idee der sozialen Selbstbestimmung im Recht, München und Leipzig,1916,S.46-56, S.187.
《魏玛宪法》制定时,辛茨海默是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又是宪法小组中唯一的劳动法专家。因此,《魏玛宪法》通过第159条保障工人结社自由和第165条第1款确认集体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第2款确立“工厂代表会”与“经济委员会”制度,全面落实了辛茨海默教授的社会自治与“社会议会制”思想。这种影响在1949年制定《德国基本法》时仍然存在。Vgl.Klaus L. Alberecht: Hugo Sinzheimer in derWeimarer Nationalversammlung, Sein Beitrag zum wirtschaftlichen R? tesystem und zu den arbeits und wirtschaftsrechtlichen Grundrechtender Reichsverfassung, Inaugural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grades der Rechtswissenschaftilichen Fakult? t der Johann WolfgangGoethe-Universit? t zu Frankfurt am Main,1970,S.102-103.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可参见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7页。
See Manfred Weiss,Marlene Schmidt,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ermany,Aspen Publ, 2008,p.136.
Vgl.BVerfGE 44, 322,340.
Vgl.BVerfGE 34, 307,316.
我国劳动法学界在理论上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反思,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孙德强、沈建峰:《集体合同主体辨析》,《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常凯:《劳权论》,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以下;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的社会化与国际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Vgl. Franz Gamillscheg:Kollektives Arbeitsrecht Bd.I, C.H Beck, S.541.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查看更多
相关知识推荐
-
“保证书”的效力
盐田路女士:我和汪某1997年结婚,感情一直很好。今年5月,在我回娘家照顾年老病重的母亲期间,汪某竟
婚姻动态人看过
-
请问“声音制作”是否与著作权中的13项权利中的“复制”权相等?请问“以网络等其他形式发行传播”中的“等”字著作权合理使用范围】《著作权法》主席令第26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3)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4)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5)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6)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7)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8)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9)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10)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11)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12)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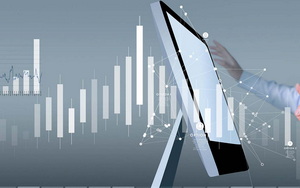 巴音郭楞州律师
人看过
巴音郭楞州律师
人看过


130人咨询过
去咨询 -
债权转让的效力
债权转让的效力是,如果是依据债权的性质,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是可以转让的,并且及时通知债务人的,则该转让行为有效
债权债务人看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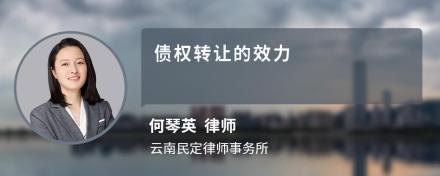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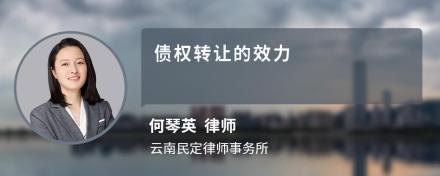
-
对效力待定合同制度“效力”的思考
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第51条的规定,在我国的合同制度中规定了这样一类合同,它被大多数的
效力待定的合同人看过
-
“地条钢”买卖合同的效力
[案情]原江西省宁都县长江钢铁厂(以下简称长江钢铁厂)系制造、销售钢材的私营合伙型企业法人。被告姜某
买卖合同知识人看过
-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中“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具体权威的司法解释是什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的规定: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宜宾律师
人看过
宜宾律师
人看过


496人咨询过
去咨询 -
公司章程补充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吗
 01:30
人已看
01:30
人已看 -
格式条款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
合同纠纷人看过
-
并签下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第四条规定: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经登记后发生物权效力。房屋买卖合同是一方转移房屋所有权于另一方,另一方支付价款的合同。转移所有权的一方为出卖人或卖方,支付价款而取得所有权的一方为买受人或者买方。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效力我国是这样规定的合同生效有两种情形:一是须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这种批准、登记指的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将合同在规定的部门办理批准或登记才生效。二是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本身无需批准或登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属于第二种情形,他调整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后的产权登记不是合同生效的要求,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是物权变动的要求。
 雅安律师
人看过
雅安律师
人看过


491人咨询过
去咨询 -
几种质押合同都是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合同成立即生效;《物权法》第15条也明确区分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节选)明文规定如下: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其他相关法律条文: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郑州律师
人看过
郑州律师
人看过


159人咨询过
去咨询 -
“司契单”的法律效力是否等同于“合同”?这个银行没有听过,请注意查询。
 周雪峰律师
人看过
周雪峰律师
人看过


101112人咨询过
去咨询 -
物权效力高于债权效力吗?一般情况高于。
 董毅智律师
人看过
董毅智律师
人看过 -
教师承担教育法律责任的条件是
教师承担教育法律责任的条件是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法律论文人看过
-
什么叫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中明确关于合同效力的立法条款
 法律快车律师团队律师
人看过
法律快车律师团队律师
人看过 -
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什么
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立法的目的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
法律论文人看过
-
物权效力和债权效力,债权的效力具体案情是什么呢
 孙表华律师
人看过
孙表华律师
人看过 -
孩子现在上高一,6月份要考什么合格考。但是他上户口的时候大两岁,现在正在改户口还能改学籍吗?你好,具体是什么情况
 宜春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宜春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
规定隐私权的意义
规定隐私权的意义是:保护隐私是对人性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宪法人权
法律论文人看过
-
昭通的身份证掉了,可不可以在昆明办理你好建议咨询你需要办理证件的主管部门的具体办理流程
 文山州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文山州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
隐私权的名词解释
隐私权的名词解释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是隐私权。自然
法律论文人看过
-
汉阳区看守所会见律师收费按照什么算你好具体是什么案件呢
 襄阳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襄阳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
自甘风险的概念
自甘冒险的概念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
法律论文人看过
-
安顺地区平坝看守所会见律师费用怎么收取你好具体是什么案件呢
 黔南州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黔南州法律问答顾问律师
人看过 -
立功的效果是什么
立功的效果是:1、在法院判决之前立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法律论文人看过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