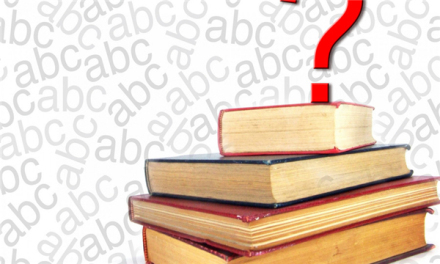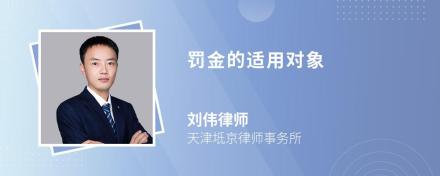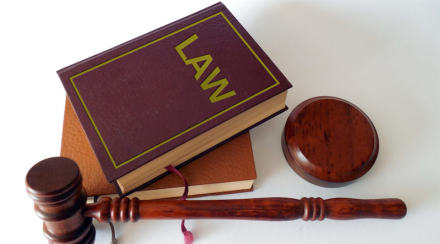关键词: 判例/法律/统一适用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法律的统一适用要求搁置是否应当建立、引入判例制度的争端,而将判例作为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从而确认判例在司法审判中的拘束力,以有力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这不仅技术上可行而且具有立法依据,同时亦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可资借鉴。对案例或判例形成问题,可以从体系、冲突规范、形成程序、发布程序等具体问题提出讨论方案。
就法律技术层面而言,统一适用的法律和法律的统一适用是任何法治国家的必要前提。统一适用的法律和法律的统一适用是完全不同性质或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前者属于立法,而后者属于司法。在司法层面上谈法律的统一适用,其核心问题就是司法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对我国法制的发展可谓贡献斐然,但是国人对司法解释的批评却不绝于耳。因为我国司法正在陷入一个“解释—不足—再解释—再不足”的怪圈。学者们和各级法院法官在抱怨审判依据不足的同时,又谴责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侵犯立法权。
本文认为,摆脱这一怪圈的方法就是重新定义司法解释和判例制度。判例或曰案例在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地位问题困扰国人良久,近两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对法律统一适用的强调,案例的地位问题再度被凸现出来。
一、具有拘束力的判例而非指导性案例是我国司法审判的客观要求
(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并未受到所期望的尊重。
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5月开始公布指导性案例以来,至今已愈20多年。但是截至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形式公布的案例仅500多例[1],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迄今仍然有效的司法解释却多达1256件[2]。最高人民法院起初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通过公布案例,① 公布这些案例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外介绍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具体案件的情况,二是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3]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第二个目的恐怕才是最高院公布案例的初衷。因为我国判决并不保密,获取法院判决文书的途径很多,因而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来了解司法审判情况未免过于局限;再者,全国法院每年审判的案件多达八百万件[4],裁判文书的数量也绝不会少于这个数字,因此,仅仅通过精心挑选的少数案例了解中国的司法审判无异于盲人摸象,未必是最可靠的方式。所以,公布案例的直接目的或主要作用,应该说就是希望这些案例能够切实指导今后的司法审判工作。
但无论经正式公布的指导性案例,还是非经正式公布的一般性案例,只要不具有拘束力,就不必须被遵循。案例“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释,又不具有约束力,它自然不会被列入法官们学习和培训的计划之内,有多少法官能像熟悉法律和司法解释一样熟悉这些案例是值得怀疑的。现今的状况是这些案例实际上成为法官想遵照就会被遵照而不想遵照就不会被遵照;……所谓‘指导’由于实际上带有太大的弹性,结果就成为被‘指导’者的主观随意性,任其取舍。一个案例如果要真正被遵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法官对该案例的知晓和熟悉;二是该案例可以成为二审法院维持、变更或撤销一审裁判的根据或理由。一句话就是这些案例具有拘束力。”[5] 351
但是最高院所公布的案例并无拘束力,所以各级法院法官只遵循那些对案件处理有直接影响力和直接拘束力的规定,唯有此才最具权威、无可辩驳。而那些仅供参考的案例既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引用,也不能作为判决依据;即使当法律或有拘束力的司法解释不能为案件处理提供解答时,法官也不一定会参考这些不具拘束力的公布案例,而是更倾向于从法学著述中获得解答。“大陆法系法官碰到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时,很可能是法学家的观点而不是判例。……碰到法律难题,也是先寻找权威法学家的论述,而非以前的判决。”[6] 5-6这其中除了法律传统及运用法学著述比运用判例的区别技术更为简单明确之外,恐怕法学家知名度甚高其观点影响更为深远也是原因之一。上述情形显然完全背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指导性案例的初衷。
(二)“案例”与“判例”之分的文字游戏背后折射出的认识误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年来大家都在争论能否建立或引入判例制度,但从未有人否定判例或有拘束力的案例将在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大家的共识是:有拘束力的判例会对我国的司法审判发挥巨大作用。而分歧仅在于: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判例能否取得拘束力,判例这种形式的法律渊源是否能够存在?
若一旦对此做出肯定回答,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我国宪法并未确定我国是判例法国家,我国法律也未规定判例具有约束力,如果承认判例的拘束力地位,是否有司法权篡夺立法权之嫌疑?是否违法甚至违宪?主流学说认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和审判权分别由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故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裁判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而不能违背法律,更不能以任何方式超越自身权限另行创设法律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不是司法解释。“在性质上,《公报》案例虽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案例,但只具有参考、借鉴的作用,不属于法律渊源的范畴,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审理同类型其他案件的依据;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法律授权对审判活动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说明和解释,是我国法律的重要补充形式,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以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作为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3] 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热切的希望案例能够被遵守而非仅仅被尊重,但是我们却不得不一再谦恭地表示,公布案例仅仅试图为司法审判提供参考或指导。甚至于我们对“判例”这个泊来词的使用都小心翼翼,在很多正式场景中我们宁愿称其为案例而非判例,宁愿称其为指导性案例而非拘束性判例。
普通法系国家的case一词并不区分所谓“判例”和“案例”。“判例”即判决的案例或案件,先例拘束力就是指上级法院的先例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具有拘束力,本院的先例对本院以后的判决具有拘束力。根本不存在上级法院的先例或下级法院的先例就是判例,而下级法院的判决或本级法院的后例就是案例的问题。然而我国是成文法体系,无论在理论上、立法上抑或司法实践中均未肯定具有拘束力的判决实例的存在,故当然不承认我国存在普通法国家那样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并且不允许将判决实例称之为判例。所以在我国,案例特指法院判决的案件实例,而判例特指西方国家(尤指普通法)法院有拘束力的案例,以试图表明“案例”对司法判决不具拘束力而“判例”对司法判决具有拘束力,从而与普通法国家具有拘束力的判例相区别。
但是,问题的本质绝非“判例”具有拘束力,而“案例”就当然地没有拘束力,因为这不过是文字游戏。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希望经过法定挑选程序选择的案例能够被普遍遵从,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敢大胆宣称这些案例必须得到遵从,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样就不会违法或违宪。个中缘由,恐怕皆在于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以为判例就是立法、法官造法,而这在成文法国家是绝不能容忍的。矛盾的是,我们敢于创制出成百上千个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毫不比立法逊色的司法解释,却竟然不敢宣告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具有拘束力!
(三)法官对判例的渴求直接促生了地方法院的参阅案例。
本文所关注者并非我国能否建立或引入判例制度这样的应然性问题,而是实际的司法审判需求:不但最高法院,近年来一些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都纷纷通过一定的形式筛选并公布所谓的参阅案例。② 这说明,我国司法审判亟需统一而具有拘束力的判例体系。“是否引入判例法,关键在于我国法制建设对其有无要求,以及他对我国的制度创新有无实际作用,而不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教条,也不在于某种操作技巧的不具备。”[7] 10
当然,呼吁判例体系并不意味着否定指导性案例。相反,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多层级不同效力的案例指导制度。因为我国各地的人口、民族结构、风俗、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非常不平衡,所以统一的法律不可能完全覆盖各地各类的不同情况。故以一定地域的司法管辖区域为单位由地方法院公布指导性案例作为国家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具有拘束性判例的补充十分必要。
二、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应该并可以成为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
一种似乎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我国的司法案例若要取得拘束力,就必须建立或引入判例制度,而要建立或引入判例制度,就一定要修改现行法律或经立法机关授权。[3] 而笔者认为,即便完全不修改现行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也可以具有拘束力。
实践证明,通过建立或引入一种新的司法制度以确立判例的拘束力,从而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并不现实。固有的司法观念以及与国体一样敏感的法律体制,并不允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创新,特别是与判例法国家走得更近的创新。既然我们对判决实例应当在我国取得拘束力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们就不应当仅仅将建立或引进判例制度作为唯一途径。笔者认为,将判例纳入司法解释的范畴,是实现法律在司法审判中获得统一适用的合法且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一)以判例为司法解释的形式不仅技术上可行而且有立法依据。
审判组织或法官解释法律是法律适用所必需的手段。应该说,有效的法律解释权是审判权的附属权力,也是审判组织和法官的当然权力。很多国家并不需要法律另外对此予以规定。而在我国,1955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明确确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凡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解释。”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也有类似规定。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何谓“审判过程中”?何谓“具体应用”?似乎明确又不甚明确,究竟是指“某一个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过程中”遇到的法律具体应用问题,还是指“整个宏观的审判活动过程中”遇到的法律具体应用问题?是指一个特定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还是指某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是前者,任何一个法官或审判组织都已在现实地行使着这种权力,这个规定纯属多余;否则就是旨在限制或排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审判组织或法官在审判活动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权,这实际上就等于剥夺了法官适用法律的权力,显然不符合立法者本意。若是后者,是否意味着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脱离特定案件和具体审判活动进行抽象解释法律的权力?分析这些年各个方面(包括来自立法机关的某些声音)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的各种非议,并不能当然得出此结论,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定:或许立法者就是明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审判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以判例的形式解释法律!然而,恰恰司法者自己忽略了这一点,按自己当时的需求理所当然地理解上述规定,却排除了其他理解,以至误入迷途,至今尚未走出这个死胡同。也正是因为这种片面而机械的认识,导致上述规定在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提供立法依据的同时,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扩张甚至变异埋下了隐患。
可以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遭受非议。近年来随着司法解释数量的增多、作用的突显以及法治理念的不断强化,非议大有与日俱增之势。现阶段我国的司法解释以抽象解释为主要形式。抽象解释是指作出解释不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系统而具有规范性的司法解释。抽象解释目前在我国最受非议,被指责为超越司法解释权的“司法立法”。“司法解释的内容是近年来遭受非难最多的一个方面,焦点则是针对司法解释超越司法权从而侵犯立法权的问题。”[5] 228这一类司法解释本不应成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流,但它的形成确有其历史原因:一是建国以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基本上是在无法可循的状况下运作审判活动的,所以极为依赖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各种通知、意见、办法、试行的规范性司法文件以为审判依据。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立法步伐有所加快,但由于我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处于急剧的变革时期,立法的滞后和经验不足显得比较突出,司法实践客观要求以抽象的司法解释形式弥补立法之不足。
应该说,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抽象司法解释应当而且必将逐渐减少直到完全被取消,代之以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最好形式应当是判例解释。判例被认为不仅是具有司法拘束力的法律渊源或准法律渊源,而且这种拘束力被视为司法附属的或当然的权力,并不一定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授权。从最简单的道理来讲,上级法院有权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如果下级法院法官毫不理会上级法院的判决,就有可能承担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的风险,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会为下级法院法官所乐见。因此,下级法院法官遵循上级法院的判决可谓顺理成章。
当然,现阶段完全以判例解释取代抽象司法解释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保留抽象的司法解释完全必要。但我们也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判例解释,而应当以抽象司法解释与判例解释共存的方式,逐步实现此消彼长,以实现从完全抽象解释逐步向主要或完全是判例解释的过渡。
(二)判例制度并不与成文法体系冲突。
完全实现以判例解释法律,对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作用巨大。因为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同一法律的理解和解释都有可能不同,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判。所以,为了避免因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与其通过个案改判的方式解决下级法院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不如通过公布统一的具有拘束力的判例一并解决问题,不但能更好的统一法律适用问题,而且还可以降低司法成本。
放眼世界,即使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判例地位也日益凸显,德国、希腊、意大利、瑞士、瑞典诸国都不同程度地将判例当作法律渊源或准法律渊源,使其成为司法判决的依据。“判例虽然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渊源并因此而号称判例法作为法系划分的一个标准,但判例绝非英美法系所独有,在大陆法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判例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 332《德国民法典》能够历经百余年而无需整体性的大修改,判例可谓功不可没。德国学者指出:《德国民法典》总体结构的维持是司法判例的功劳,这些判例在使民法典内容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富有社会生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却又常常为人误解的作用。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德国民法典》其全部领域均穿上了色彩鲜明的法官法外衣以至于人们现在已经不再能够从法典条文的单独阅读中简单的领悟现行实际法律。[8] 175,280一个世纪以来,大陆法系的判例汇编日益完善,今天在罗马日耳曼法系的很多国家都有官方汇编,如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土耳其等国家。[9] 131-132我国台湾地区“宪法”中并无判例的规定,但台湾“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对下级法院是具有拘束力的,而且,判例的变更也有严格的程序。依台湾“法院组织法”第57条、第25条规定,“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所持法律上之见解,认为有编为判例之必要者,应分别经由院长、庭长、法官组成之民事庭会议、刑事庭会议或民刑事总会议决议后,报请司法院审查。”“最高法院各庭审理案件,关于法律上的见解,与本庭或其他庭判决先例有异时,应由院长呈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变更判例会议决定之。”[10] 在我国澳门,为统一法律之适用,每年也都会精心挑选一些案例,汇编成《司法见解》,这些司法见解即是有司法拘束力的法律渊源。在瑞典、荷兰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所以,判例解释应当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终审法院最主要的司法解释形式。在当前国内尚不具备完全取消规范性抽象司法解释的条件下,我们应该逐步着手尝试并积极实践判例解释这一司法解释的新形式。
三、案例或判例形成问题的若干构想
第一,我国案例或判例式的司法解释的体系。在我国,用案例或判例的方式解释法律可以设计的两个层次: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对全国各级法院判决具有拘束力;二是各终审法院公布案例,对本院及其下级法院判决具有拘束力。
第二,冲突规范。(1)案例对法律的解释不得与判例的解释相冲突。(2)下级法院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解释不得与上级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解释相冲突;本院后例对法律的解释不得与本院先例的解释相冲突。(3)上级法院认为下级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解释不当时可以宣布撤销;任何法院认为本院先例对法律的解释不当时可以宣布撤销。
第三,案例或判例的形成程序。(1)指导性案例应报上一级法院备案;各终审法院对本院终审的新类型和复杂疑难案件凡遇需要补充法律漏洞的法律解释问题,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可逐级报送上级法院作为指导性案例或判例的备选案例。(2)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法院设立指导性案例审查办公室专司备案案例审查工作。(3)备案审查办公室对备案案例应逐件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凡认为备案案例解释法律不当需要撤销的应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可。
第四,案例与判例的发布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或上级法院在选定判例或备案指导性案例前可以直接调卷审查该案件,凡被选定的判例或指导性案例,经统一编号并发布或公布,对全国法院或一定司法辖区的判决具有拘束力,在司法判决中可以引用,也可以成为上级法院变更或撤销案件的理由。
第五,案例或判例的编撰。(1)判例与指导性案例通过汇编进行整理编纂,其中判例汇编由最高人民法院实施,指导性案例汇编由高级人民法院实施,判例和案例的编纂一般应三年进行一次。(2)判例或指导性案例的制作形式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判例的制作形式。
第六,案例或判例的追溯力。生效案件的判决被选定为判例或指导性案例后并不当然导致已生效原判案件的再审,也不得以该判例或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解释作为再审的理由。
注释:
①1985年至1990年公报都注明“本公报公布的案例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②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商事审判中实行判例指导的若干意见(试行)》(津高法民二[2002]7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典型案例发布制度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的意见》(苏高法[2003]174号);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等等。
【参考文献】
[1]最高法院将进一步公开重要司法活动信息[J/OB]. 人民网. 2005-05-25.
[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请示答复全书[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3]龚稼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指导性案例[A]. 北京:中国司法解释与外国判例制度国际研讨会论文[C],2005-04.
[4]2005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5]董皞. 司法解释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潘荣伟. 大陆法系的司法判例及其启示[N]. 判例与研究. 1998-03.
[7]谢晖. 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N]. 判例与研究. 2000-04.
[8][德]K·茨威格特,H·克茨. 比较法总论[M]. 潘汉典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9][法]勒内·达维德. 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 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陈石狮. 台湾地区解释、判例制度之建构与运作[A]. 北京:中国司法解释与外国判例制度国际研讨会论文[C],200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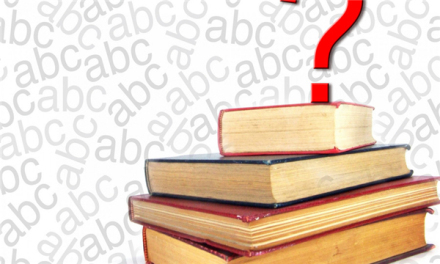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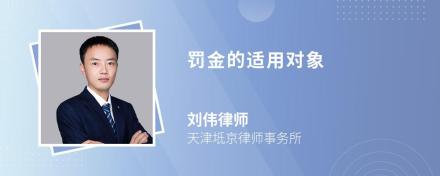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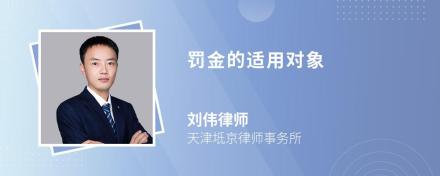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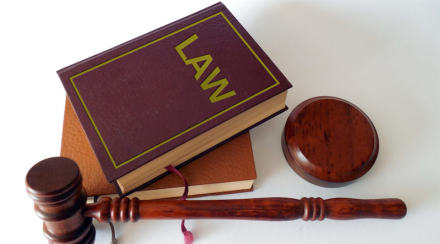

 01:30
人已看
01:30
人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