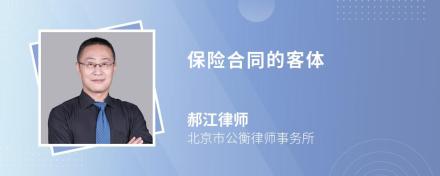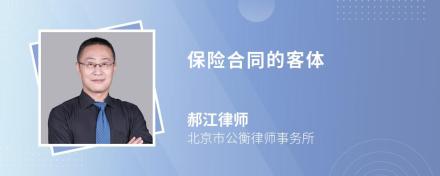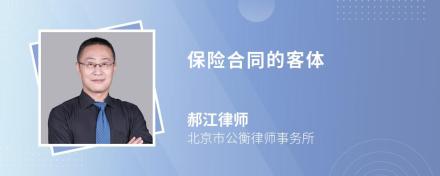(五)将生命下注
screen.width-55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50;">
我的一个哥们的哥们在1993年春天的某天,从一家信用社贷到了一笔金额60万的贷款。在1993年的时候,60万并是一个小数。第二天他邀请了多达几十人的一大帮狐朋狗友去吃饭喝酒卡拉OK桑拿,我的那个哥们也在被邀请之列。据说,一个晚上下来就花掉了十几万。那个家伙对他的狐朋狗友们说,这是庆祝他刚从信用社赚到了一笔钱而举行的。从银行贷出的款扣除有关回扣、费用等,剩下的就是借款人的纯利,这就是当时的事实。这位哥们赤裸裸的一点不加掩饰的方式,不免让场面上的人很难接受。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许多人在向金融机构张口提出贷款申请之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将来归还贷款的事情,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只要到了他手里的东西当然就是他的,不论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于是,到手的贷款当然就成了利润。在当时,这样的人实在不是个别或少数。我再举一个自己亲历的例子。钱天马,民工出身,小学文化,在1992年的炒地运动中乱中崛起的大老板,特区大名鼎鼎的著名企业家,据说拥有超过10亿的身家,1992年他刚起步时在我们公司贷款五十万,之后他发了大财,却从没有支付过一分钱利息,更不提归还本金的事情。我在调到信贷部后他的贷款转由我专管。我多方设法才见到他一面,他谈笑风声,除了言语粗俗,其他的迹象都证实他确实不是可以被小看的人物,给我的印象是他很豪爽,热情地请我吃饭,点了一大堆山珍海味,这让我对要回我们的贷款或者至少拿到一点利息有了一点信心。在多喝了几杯后,他竟然将嘴巴贴近我的耳朵大声说:“你知道吗,其实中国真正的首富不是牟其中,是我!牟其中比起我来差得远呢!”。我听他这么说就更加有了点底气。但是,事后我拿着钱天马的名片---上面列着一大堆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委员之类的头衔,连续几天按照上面印着的一大堆手机、座机号码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竟然不是关机就是空号。后来我又见过几次钱天马,他每次都信誓旦旦,不是说马上就给就是说已经安排下面的人办了。很难想象,一个自称中国首富的人,而且事实上很有钱并且是很有社会身份、地位的人(听说他还是一家叫做可赖墩大学的教授),对区区五十万债务却硬是赖着不还。
那时侯极为活跃的骗贷者,其骗贷手段在今天看来大都很不高明,但却屡屡得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量银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流进了他们的腰包。那个时代特区的酒店歌厅桑拿里拥塞着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款爷,经常向正在弹奏钢琴或唱歌的小姐随手抛出几张大票点上一首诸如“百毛女”之类的曲目。倒是在社会已经远比那个时代富裕得多的今天,无论在那里也很少看得到这样的款爷,这与那时的款爷钱来得实在太容易、成本实在太低大有关系。
信贷资产质量低下是传统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痼疾。但是,信托公司资产质量的低下却被媒体所反复炒作,资产质量的低下被当成信托就是坏小孩的铁证之一。实际情况是,不论从信托公司资产质量问题的严重性,还是从信托公司信贷资产质量低下的原因来看,都与银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相反,很多信托公司的资产质量比银行要好得多。在导致信托公司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的深层原因上,金融机构的权位人员与社会闲杂人员(大都以社会贤达人员身份出现)内外勾结,在诈骗、套取贷款及逃废债务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倘若不是如此,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就是金融机构的权位人员都是SB。有人曾专门研究过骗贷者的一些手段,结果发现大多数骗贷和套钱手段都很小儿科,只要不是白痴就几乎能一眼看穿,例如私刻的公章、伪造的房产证,上面的字经常都是歪歪斜斜的。实际上,在90年代,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涉嫌内外勾结骗贷或者收取外部人员贿款案发后锒铛入狱乃至被枪毙之类的新闻多得不计其数,以至社会对这类新闻几乎都失去了兴趣。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些人在事发后逃匿,而部分逃匿者在风头过后又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
我的一个哥们,因为姓马,又总是发出各种悲观预期,在我们这个圈内都呼之以“马尔萨斯”之名。他所在公司信贷部的头离开信托后,很快就成为了某地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很显然,在信托公司期间这位企业家成功地完成了原始积累。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描绘的“羊吃人”的血淋淋的原始积累相比无比文明,没有什么“羊吃人”,也没有人吃人,一切都是在和平有序的情况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马哥们在进入信托业之前是个学者,有两个毛病,一是愤世嫉俗,二是凡事总要从理论、发展趋势之类的角度议论一番。早在90年代初期,我们在一起侃大山的时候他就经常唉声叹气,大发感慨。他所说的许多话后来不幸都言中了。他说的有两句话我最难忘,一是“泰坦泥克号是早晚要沉没的,你们的挣扎是徒劳的”;二是“如果我们不从现在起就彻底挣脱道德、良心的束缚,终有一天我们就会给不讲道德、没有良心的人打工,反之我们就可以让别人为我们打工”。他说他看透了人间世事,并一再扬言、发誓要下决心象*女一样出卖自己,以避免将来沦为那些厚颜无耻之辈的打工仔。可惜他一直是一位理论的巨人,行动的懦夫。他说理智与良心的不断搏斗使他太痛苦,最终他还是在信托大厦摇摇欲坠之际离开了信托业。
许多与我初次谋面的人,一听说我在信托业工作过,往往都语带羡慕甚或妒忌地说出诸如“发大财了吧”、“你这辈子是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有六位数还是七位数了”之类的话。我的许多同事、同行都有类似的经历。更令我吃惊的是,甚至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这么看我。在信托业风雨飘摇尤其是即将崩溃的日子里,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甚至有点歇斯底里。我的一个算得上关系很不错的朋友,有一次在与我喝酒聊天时,可能是多喝了几杯,也就多说了几句心理话。他说他早就发现了我不太正常,肯定是担心自己出事,劝我想开点等等。我告诉他我在信托违规经营的事是做了,但还不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没有干过他想的那些事。他根本不相信,用了“常在河边走,不会不湿鞋”这类的话来回答我,还说我没有把他当真正的朋友。不言而喻,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你在信托公司工作,而且成天与钱打交道,又掌握着一定的权利,那么你一定有钱也有问题。对于这类诘问,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置可否。无论我怎么郑重其事,怎么表现真诚,发问者都会说我很虚伪。许多发问者并没有对被问者进行道德否定的意思。相反,他们会认为如果真有人在有权的职位上不捞钱,那他不是脑袋有毛病就是蠢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样人给予回答没有任何意义,可能不答才是最好的回答。不过,无风不起浪,如此之多的人这样看待信托业或者金融业者,也的确说明在这个新旧交替的金融体制剧烈变革过程中,可能确实有太多的金融资源占有者或支配者取得了原始积累的成功。在过去的20余年中,制度空白或制度模糊是改革过程的一大特点,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但是,在相当多情况下,许多当事人都是因为个人私利原因而利用制度空白或模糊故意试错的。正是由于有太多的制度空白和制度模糊有机可趁,许多人将金钱资本、政治资本甚至生命作为了本钱下注。许多人认为成为烈士是概率很低的事件,而低概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因为对风险的评估值很低,有些胆大妄为之徒的原始积累甚至是在赤裸裸地抢劫,几乎没有一点掩饰。但是,事实表明,固然有许多人在发了不义之财后安全着陆,要么潜逃在外,要么至今仍未东窗事发,甚至一些人还成了著名的企业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烈士,而且还不断有人成为烈士。这是一种特殊的赌博,一些人赌赢了,但这些赌赢的人永远能赢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赌输却将被永远埋葬。道理虽然如此,将生命下注者至今仍然前赴后继,络绎不绝。
(六)最后的挣扎
screen.width-55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50;">
虽然信托业每隔两三年就要来一次清理整顿,但信托业的真正灾难始于1993年6月宏观调控后开始的第四次清理整顿。在这次调控中,信托业的资金链几乎绷断,但随即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即所谓“国债回购”挽救了信托的生命,使之暂时转危为安。所谓当时的“国债回购”,通常是拿出10%甚至更少的国债现券(俗称“铺底券”)为抵押进行的回购交易,实质是以铺底国债作为抵押的资金拆借。当时,国债回购交易异常火爆,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据说是体改委背景的STAQ、地方人民银行背景的
武汉、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三大国债回购资金交易市场,参加交易的有信托、证券、信用社、银行、租赁公司及财政系统的国债服务部等。各交易市场实行会员制,参加交易者须交纳一定会费成为会员并买进席位后才能进场交易。大多数信托公司都加入了各交易市场,向政府财政部门或者其他机构借来“铺底券”,而且多是资金净拆借方。当拆借额度用完时,许多信托公司又利用这些资金市场的制度漏洞,以下属证券营业部的名义做为独立会员取得席位进场融资。
在这场资金交易大战中,信托公司的人马争相活跃在各大交易市场。为了把融资功能发挥到极至,许多信托公司都急忙向人民银行申请在各地设立证券营业部,以作为回购交易的平台。后来,这些证券营业部成了许多信托公司最为优良的资产,并一度成为许多信托翻本的主要资本和希望,真是歪打正着。当然这些信托公司对外宣传中所说的都是他们如何如何高瞻远瞩,早就确立了以证券为主业的发展战略等等。特区所在的一家地方信托公司由于在融资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积极配合了政府的重大工程建设、财税和安定团结等工作,多次受到了当地政府、领导的表扬,除了由政府出资、出政策奖励公司法人代表和全体员工外,还在金融工作会上,多次要求银行们向该公司学习。为了开创当地金融业的新局面,政府还决定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财政债权等方式对当地地方信托公司增资。当然,很多信托最初的资本金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来的。
“国债回购”运行期间竟然形成了证券交易中心席位交易的拌生市场,据悉一个席位曾被炒到过1500万元以上。这些借用席位的人员或机构有相当多是深明其中之道的套取资金和投机钻营的高手。当全国性的国债回购清理运动开始后,这些席位“借用”者大多人去楼空,不知去向,而外借席位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不背上别人以其名义借用的巨额资金债务而徒唤奈何,一批从中获取好处费的行长经理锒铛入狱。
信托的最后一个冬天在黄道吉日到来。1995年8月8日,一个被商人认为大吉大利的日子,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家联合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决定全面清理买空卖空的所谓“国债回购”,严令信托机构归还因国债回购交易而形成的债务,并成立“全国清欠办”督导国债回购债务的清理。几乎所有信托公司和参与“国债回购”的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弄懵了,一时间方寸大乱。从此之后,多数信托公司无力支付到期机构债务,实际上一场真正的金融危机自此爆发。这场危机的后果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发酵,虽然没有人渲染,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但有业内人士认为,2002年和2003年关闭的几家证券公司都与“国债回购”危机有很深的渊源,其中的
大连证券实际上是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借尸还魂(据说,海南华银也是仰融打造华晨帝国的原始资本的最初来源)。
从1995年8月后,维持生存成为多数信托公司的唯一“经营目标”。在资金链条崩断后,信托公司的社会信用本已破产,但信托的金字招牌、股东背景无不意味着政府对信托的背书,因此不再能够从银行、证券拆借资金的信托公司,却竟然仍然可以继续以高利率为诱饵从个人和一些非金融的机构处融资,当然融资规模远不可与从前同日而语。占负债大头的同业到期债务,信托公司已经不需要支付或者至少不需要全额支付(其实是没有能力支付),但信托家大业大,且作为贵族人家,基本场面还是要有的。再加上少量压力较大的机构债务和个人到期债务的按时支付,以及希望通过新项目及炒作股票等投资快速获利,因此各信托公司的资金压力仍然很大。尽可能多的融资,在这一时期比过去更显得意义重大。于是,信托们推出了“地产信托”、“信托受益投资证券”之类的一系列融资新业务。人民银行监管机构对新业务的性质拿捏不准,但信托们歪理正说,说你人民银行过去总说我们信托不务正业,乱耕别人的地,我们现在响应你的号召开办信托业务,不荒自己的田,你怎么能禁止。当然信托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所开办的“信托业务”是个什么玩意。
到了1996年春节过后,参与国债回购的机构才终于从错愕中反应过来,开始派出人员追收债款。据说在最高峰时,飞往各地的飞机航班一时爆满,各路催债的人马占到了乘客一半。在这场追收债款的混战中,纯粹的债权人几乎没有,甲欠乙,乙欠丙,丙欠丁,丁与丙欠甲等等,有场内欠,有场外欠,有内外都欠,三角债的关系异常复杂。那一段时间,各信托公司热闹非凡,经常有多路讨债大军挤在信托公司归口业务部门和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要债的人也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哭的有闹的有骂的,有带着律师、法官的,有带着各级政府官员和新闻单位的。有的信托公司在经历了数月时间的被动挨打之后,才终于总结了一整套推委、扯皮、胡搅蛮缠的经验,开始根据来客的类型分别制定应付方案并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各信托公司都锻炼出了一批对付追债人的赖皮高手,这些同志一般均具备能吃会喝、能说会道、能唱会跳等多方面的能力,并陆续将这些人才调入新设立的诸如“国债回购清理整顿总部”等机构委以重任。此间,我所在的信托公司也派出了多路讨债大军,但不久即纷纷传来败绩,其中一路人马竟然还中了埋伏,被一群不明身份者暴打了一顿。
这一期间,中银国投和中农信先后被关闭。在中银国投被关闭之时,我们极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从没有想到国家有一天会真的抛弃我们这样官办的金融机构,在这之前有些信托也被“撤消”了,但那不过是与银行之类的机构合并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对中银国投的关闭最终仍然判断为一个个别事件。但接着对中农信的关闭使我们认识到,国家可能真的要对我们动手了,没有死刑的时代将要成为历史。我们不想成为中农信,危机感骤然而生,紧张空气在我们这群信托业者中弥漫,于是在此之前一直停滞不前的信贷资产的清收工作大幅推进。除了当地的国有企业,我们把几乎所有的其他欠贷企业全都告上了法庭,一度我们成了特区法院最大的客户,感觉法院就是咱家开的了。紧接着,我们又成了特区最大的地主,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清收回来的资产抵偿法人债务。在一次清欠会上,当总经理为过去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及现在无法以现金偿还债务向债权人表示道歉时,没有想到一位国内著名券商的与会代表对我说:“你们老总老说对不起我们,其实没有谁对不起谁,今天这样的结局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你们的资产我要了,我们马上就顶给人家”。我当时深为他的开通而感动,同时也很意外,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那个以资产规模和开拓创新著名的证券公司是不可能有不能偿还的债务的。
并不是所有的债权人都那么开通或者傻,有许多债权人指定只要现金,其他资产坚决不要。我们想尽办法让对方相信我们公司严重资不抵债,早晚会破产。并反复对他们说:“现在还能拿点土地之类的资产,到我们关门时可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不知道别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反正我觉得特别对不起那些对我的话信以为真的人。但时过境迁,我们所说的一切竟然都成了事实,那些接受了资产的债权人真是庆幸。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理,老实人不一定总是吃亏。
这一时期信托公司最为成功的经营领域是证券。1996年一家证券营业部的转让价只要一百余万元,一年后上涨了十几倍。若不是顶上了资本金限额的天窗(收购证券营业部的数量受资本金大小限制),也许我们会在后来成功地转型为一家证券公司,成为信托公司中死里逃生的英雄之一。但在现在,证券公司的处境一如当年的信托公司,甚至有人说大多数证券公司在理论上已经破产。就算我们当时死里逃生,今天我们又会如何呢?也许最终我们还是逃不过死劫。就是没有生死之虞,也可能在为当年放弃信托的身份而懊恼不己,据说几家由信托改证券的公司都是如此。世事无常,我们真的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信托陆续关门,我们的情况却似乎在逐渐好转,负债大幅度下降,证券业务做得风生水起。但就在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脱离危险的时候,一场金融地震爆发:某城市合作银行出现支付危机,并很快波及信托及农村信用社,这件表面上与信托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成了压死信托公司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场危机中,当地所有信托都未能幸免于难,一家接一家倒下,最终全军覆灭。这个一度以信托的数量最多傲视中国各地的特区,从此成为信托的禁地。
据悉,该城市合作银行是由几十家城市信用社拼凑起来的,从其出生到死亡,竟然还不到两年。这些组成合作银行的信用社实际上大都控制在私人或机构手中,成为个人和机构融资的工具或平台,其管理之混乱、经营业绩之恶劣,比信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当地金融圈中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该城市合作银行成立后仍然是一盘散沙,其总行只能控制少数几个原国有机构控制的信用社改编的支行和直属营业部,其他支行仍然是原控制者的地盘。该城市合作银行出现支付危机实际早有迹象,在海南发展银行爆发危机之后,城市合作银行的存款就开始不断流失,资金头寸日益紧张,向人民银行和政府连声告急。后来的事实表明,在合作银行宣告不能支付到期存款之后,信托公司立即出现了挤兑的苗头,最终引发了信托业的全面危机。
我们当然清楚不能支付个人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1995年8月后信托不能正常支付同业债务没有立即遭致灭顶之灾,但现在如果不能支付个人债务,关门几乎是唯一的结果。此间,我们紧急动员起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将融资任务分解到每个员工,工资奖金与融资额直接挂钩;抓紧信贷资产的清收,不论是否本地国有企业,不还贷款的一律采取法律行动;不计成本变现各类资产;向政府紧急求救,请求政府注入资金;启动各类宣传工具大肆渲染我们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经营状况如何良好等。可叹的是,我们公司从成立以来几乎从没有做过广告宣传,但这个时候特区几乎所有各类媒体都接到了我们的广告定单,与我们有关的报道和广告连篇累牍,街头的横幅铺天盖地。为了节省资金,许多广告费都是用一些欠贷酒店的签单权支付的。这段时期,我们每次进酒店几乎肯定会遇见各类媒体的记者、领导之类的人。酒店叫苦不叠,因为只有人气,没有钱进。招数用尽,但效果并不明显。政府那边虽然也是急火攻心,但财政吃紧,也只能口头上一再表示坚决支持,并要求我们一定要顶住。对于我们查封、起诉欠贷国企资产的做法,鉴于可能造成企业关门、工人下岗,并引发影响安定团结的严重事件,政府严令立即停止。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虽然稳住了部分存款客户,但一些精明之人反而对此起了疑心,把没有到期的存款纷纷提走。公司老总们这期间神经异常紧张,一接电话往往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又没有钱了?”,弥补头寸缺口的唯一办法也就只有挪用股民保证金了。这期间,一家又一家的信托公司宣布停止支付,而随着我们挪用股民保证金的数量越来越大,证券营业部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营业部经理们分成两派,一派是所谓的“投降派”,认为再这样下去支付固然不保,证券营业部也要同归于尽,现在一打新股资金头寸就异常紧张,爆仓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另一派是所谓的“抗日派”,他们认为保不主老子也就保不住儿子,宁可同归于尽也不能弃守。每次会议,双方都要舌枪唇战,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也就不了了之。
这样的平衡终于被一次爆仓事件所打破。在爆仓事件的当天,我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应对办法,接着就商议停止支付的问题,和战双方再次激烈交锋,由于“抗日派”的几员大将倒戈,会议于凌晨作出决议,第二天起停止一切债务的支付。在我们停止支付之后的一个月内,当地所有的信托公司全部关门。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凄风苦雨,我们终于理解了什么是1949年的“国军”。在这期间,存款户多次到公司集会闹事,有一次竟然把大门给封上了,我们几乎一天不能进出,许多战友差点饿昏。大量债权人通过法院大肆执行我们的资产,造价数亿元的信托大厦被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为五千余万,由法院裁定给了债权人。我们被赶出了信托大厦,真正体会到了丧家之痛。也就是同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三年前曾经把国际信托大厦评估为五亿六的价值。最让我们不能理解也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的一些战友一下变得面目狰狞,竟然向债权人出卖关于我们财产的情报,带着外地法院冻结、查封、执行公司的大量资产,协助债权人办理资产过户手续等等。按照我们内部的说法叫做“涌现了一批汉*”,其实也就几个人。这几个人原先我们也没有感到他们的能力有多大,但现在他们从事破坏活动的时候,我们才真正领教了他们的厉害。这些汉*与“皇军”并肩战斗,公司的几乎全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在很短的时间中就被瓜分完毕,只剩下象债权这样的难于追收的资产和残缺不全的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由于其特殊性,最高法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不能被冻结、查封、扣划股民保证金,但一些地方的法院根本不管,照样冻结、查封、扣划。当然,这些证券营业部的转让权、固定资产、在交易所的席位等资产权利,最终被N家法院反复查封了N遍。那些动手晚些的债权人,几乎什么也拿不到。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病入膏肓者为什么有生不如死之感。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盼望着的就是赶快关闭或者破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刚进信托时总经理形容信托公司大有作为时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想一语成谶。我们的信托骆驼因为没有资金的粮草被饿死了。在它死亡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多少资产的肉却有很多负债的骨头,纵然比马大些又能如何,只能徒增我们的痛苦罢了。作为历史的证人,信托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注:本文中的图片由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