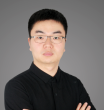1. 引言:问题的提出
行政程序之所以倍受关注,一方面是在正义观念逐渐由实质正义向程序正义渗透的趋势下,越来越凸显出其在确保客观(objectivity)与公正(impartiality)方面的巨大价值。因此,行政程序也实现了自我超越,不再仅仅是辅助结果正当性实现的工具性角色,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也对程序裁量产生了巨大的约束效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法律没有对程序做出要求,行政机关在程序裁量上仍然不是自由的,仍然要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与实体性规范相比,程序的妙处是,在约束的同时又不呆板,有原则又不失灵活,能够根据个案之不同调整、整合产出的结果,以谋求个案正义的实现。也是在这一点上,它与行政政策以及遵循先例的约束机理殊途同归。无怪乎戴维斯(K. C. Davis)在他的裁量构造(structuring discretion)理论体系之中,程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1]
但是,在这里,我更加关注的是行政程序在司法审查上的意义。因为法院对行政程序的违法(瑕疵)及其效力问题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不仅能够左右行政机关在执法之中对行政程序的基本态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司法审查上选择什么样的判决形式和处理。从制度建设上讲,这样的研究,对于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草拟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也会大有裨益。
《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3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该条款在行政诉讼上的重要意义是,确认了违反法定程序(breach of statutory procedures),或者说,程序不适当(procedural impropriety, procedure irregularity)是司法审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不言而喻,上述第54条(二)3之规定对于行政裁量的控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但是,第54条(二)3看似解决了不遵守行政程序的法律后果问题,实际上却远远没有解决。因为那种认为“只要违反法定程序都一律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的观点,(从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单一化了,会人为地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对原告也不见得总是有实际的收益,所以,不完全符合现代行政法发展的实际。况且,另一方面,在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上还一直存在着无效(void)与可撤销(voidable)二元结构理论以及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而且,在制度法的层面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折射与体现,所以,必然也会上述第54条(二)3之规定发生碰撞。因此,本章将详细分析和探讨其中的有关问题,希望通过比较的分析方法和细腻的理论批判能够为我国现行的理论给出一点参考,推进有关理论研究的深化。
2. “法定”程序能够从正当程序、从法律默示之中衍生出来吗?
从《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3之规定看,毫无疑问,进入该条款射程之内的程序都应该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是,众所周知,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一般的行政程序法。即便是在那些规定了行政程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也多是侧重行政行为的流程和手续,较少体现出现代行政程序的控权理念的程序要求。所有这些,意味着对于有些行政行为来说,会出现被程序规范“不该遗忘、但却遗忘的角落”,缺少着对保障相对人权益有意义的基本程序要求。
那么,作为上述立法疏漏的弥补,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能不能直接根据正当程序的理念,要求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某些(个)程序要求呢?
这在普通法国家是可以的。比如,成文法或规章(statute or regulation)规定了相对人有申诉的权利,那么,就可以根据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规则,或者认为是上述申诉权规定之默示,推导出行政机关有说明理由的义务。[2] 其中的合理性在于,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课加说明理由义务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有助于(facilitate)提起审查程序、更加有效地将行政机关控制在法院的监督之下。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法院判决中都表达出这样的理念。[3] 当然,普通法国家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与其“法官造法”以及法院判例构造行政法规则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自然正义的观念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有关。
在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审查方式,比如,东京地方法院对有关个人计程车执照不许可处分和群马县中央巴士执照不许可处分两个案件的判决,都是在有关法令未做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由宪法或有关法规之合理解释来判断正当程序是否被遵守。这种审查有利于弥补当时日本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所生之缺陷。[4]
但是,在我国要这么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法院的审判依据是什么?作为主审案件的法官个人是无权创设出上述程序要求的,因为缺少法律明示规定的缘故,哪怕是要法官从法律的默示规定之中推导出上述程序要求,恐怕也难免不会不发生很大的争议。
当然,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这种默示的法律规定进行统一的司法解释。既然法律赋予了相对人寻求行政救济的权利,那么,为了使行政救济更加快捷、更加有成效,当然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应该说明理由。
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上述程序要求是由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在案发之后由法院施加的,那么,会不会有损于法的可预测性和可度量性呢?这也不会。因为尽管我国不存在判例法,但是,法院的判决,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仍然会有效地影响着、事实上拘束着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不可能不考虑到上述司法解释,不可能不顾及法院对其行为的基本态度和司法后果。
紧接下来,就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如何判断什么时候需要科加程序上的义务?需要科加什么样的程序义务?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法院给予程序性保护。从普通法的经验看,法院在把握的分寸上一般要拿捏住两点:第一,具体授权法上规定的法定程序不足以实现正义;第二,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这些附加的程序不会损害立法目的。[5] 在我看来,除此之外,法院还可以综合考量原告利益的性质,原告能够从程序性权利之中获得多大的收益,程序的缺失会对行政决定的正确性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行政机关遵从这些程序义务之后会增加多少成本等因素,然后,裁量决定之。
3. 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后果(I):无效(void)与可撤销(voidable)
程序既然是由法律规定的,或者是从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中延伸出来的,自然应该遵守。假设违反了程序规定,那么,当然构成违法。但是,从第54条(二)3之规定看,我们关心的不是程序违法本身,而是程序违法会对行政裁量决定(具体行政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上看,主要有无效与可撤销两种。依照通说,无效(void)是指在法律上从未存在过。可撤销(voidable)是指在没有被法院或者有权机关撤销之前在法律上是存在的。[6] 所以,无效意味着对相对人根本不发生约束作用,相对人可以行使宪法上的抵抗权,拒不执行。而且,在行政诉讼上也应该没有起诉期限的限制,随时可以宣判无效。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却可以像有效行政行为一样一直处于有效力的持续状态,除非,直到当事人成功地申请法院撤销之。但是,却应该有时效要求,“过期不候”。撤销的效果也可以具有溯及力,一被撤销,就视为从未存在;也可以只是向后发生撤销的效果,不溯及既往。
那么,是不是程序违法也同样会导致行政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这两种结果呢?恰好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了第54条(二)3规定的撤销方式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以及其他制度法之间的不和谐。
首先,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上已经透露出对第54条(二)3仅是部分或全部撤销(voidable)的反动。因为在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之中,除了可撤销以外,还有无效理论、治愈和补正理论。从权威著述上看,程序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效力与影响应该都涉及到这些情形。[7]
其次,其他制度法似乎也在努力地应和着上述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理论,也似乎在背叛着第54条(二)3之规定。比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就试图透射出无效概念之理念,[8] 尽管像有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该条款出现的“无效”概念,其内涵实际上明显地突破了、超过了行政法理论上所认同的重大、明显违法才为无效的见解。[9] 这多少有些不尽善尽美之遗憾,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第49条立法却最终完满地反映出无效理论的抵抗权思想。[10] 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第(三)项之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判决。隐藏在该条背后的理论依据显然是,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由于其在法律上自始不存在,所以,谈不上撤销,只能是确认无效。该条款解释可以认为是对《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规定的撤销判决过于笼统的批判,是在这个框架之下(之外?)的进一步细化、解析与分化。
上述两方面至少反映出第54条(二)3之规定过于简单化、单一化(?)。似乎应该按照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视角再回过头去审视制度法,我们又会发现,制度法本身却又似乎没有很贴切、很伏贴上述二元结构理论,并没有真正把上述理论转换成实际可操作的制度。
第一,最明显的是,无效行政行为既然自始不存在,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者当事人没有起诉,而转变成有效。所以,应该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然而,从《行政诉讼法》第38、39、40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42条有关起诉期限的解释看,却没有相应的规定。[11] 当然,这个问题从技术上是比较好解决的。但是,这种制度上缺少应和的事实却很耐人寻味。
第二,比较棘手的是,在司法上怎么来判断行政行为是无效,或者可撤销?哪些情况属于无效,或可撤销?迄今在司法上缺少着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程序违法,假如只能笼统地停留在“重大的程序违法导致无效,轻微的程序违法导致撤销”,却不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有说服力的论证的话,那么,会因为缺少司法操作性而变得没有价值。
第三,“若干解释”第57条第2款第(三)项又在上述理论之外新划出了依法不成立和无效,是不是受了民法(合同法)的影响?在公法上有没有这种区分的必要?尤其是怎么区分?却是不清晰的,很有疑问的。
但是,我们还先不忙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实在的行政审判制度本身就已经透出对上述无效和可撤销之理论界分的反动或反叛,对上述理论界分本身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和实用价值的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3.1 来自普通法的批评
普通法学者和法官不是像我们那样从无效与可撤销的内涵去分析两者的区别与实际运用问题,而完全是从救济的实际可得性出发,来分析这种二元结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必要。
在他们看来,抛开救济的实际可得性,抽象地谈论行政行为是自始不存在,还是其他什么一种状态,是没有意义的。行政行为即使是“无效”的,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除非,要等到在法院那儿采取了某些步骤判决其无效为止(even if such a decision as this is “void” or a “nullity”, it remains in being unless and until some steps are taken before the courts to have it declared void)。[12] 而要成功地诉诸法院,还必须是由适格的原告遵循恰当的程序和条件寻求适当的救济,样样都得符合规矩,法院才会判决行政行为无效。倘若有一项差错,比如,不具有原告资格,法院即便是已经察觉到行政行为本身已处于无效状态,也不会因此就判决其无效。所以,假如不能成功地获得救济,尽管不意味着就是肯定“无效”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不会使“无效”的行政行为就此转变成有效,但是,至少会使“无效”的行政行为事实上能够像有效的行政行为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处于永远不受攻击的状态。既然不能攻击,就只能接受。[13]
那种认为“无效与可撤销的区别在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在法院宣布撤销之前具有暂时的效力,也可以因当事人放弃诉权而变为有效;无效的行政行为则不具有这种暂时的效力,也不会因为当事人放弃诉权就变得有效”的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效行政行为是自始无效的认识之上的。但是,要是说,只有当开始的时候总得要有某种有效的因素,该行为在法律上才能是有效的,这样的说法是很荒谬的。因为从救济的可得性角度看,只要你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那么,你就得接受现实,哪怕该行政行为是“无效”的。
而且,从实证观点出发,也会发现,在英国法中,对有些行政行为的救济明确是有时效的。比如,1946年的土地征用法(Acquisition of Land Act 1964)和1962年的城镇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62)上都规定了,如果在六周之内没有对强制征用决定和各种规划决定提出异议,那么就不得再提出任何诉讼。因此,假比方说上述决定在作出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是无效的,但如果在六周内没有提出异议,那么该决定就不会被改变,就必须当作是有效的那样接受下来。[14]
所以,现在很多的英国学者都认为无效与可撤销的区分是不必要的。韦德教授(H. W. R. Wade)就说,无效和可撤销问题,具体运用到某种合同上可能有意义,但是,在解决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上没有什么意义。行政行为要么是合法有效,要么是违法无效。[15] 丹宁法官(Lord Denning)也说,对无效和可撤销的讨论,只是文字上的、语义上的游戏,仅此而已(it seems to me to be a matter of words – semantics – and that is all)。迪泼罗克法官(Lord Diplock)说,这种在私法,尤其是合同法上发展起来的学说,在公法上却不适用。罗斯法官(Lord Rose)说,无效和可撤销的划分无助于分析目的(the void/voidable distinction serves no useful analytic purpose)。[16]
3.2 对无效行政行为两个基本要素的批判
隐含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背后的一对矛盾是法的安定性与公民宪法上的抵抗权之间的价值冲突与衡量。无效行政行为在宪法意义上的重要价值应该是认可了公民的抵抗权。但是,在制度法上,《行政处罚法》第49条尽管开创性地赋予了相对人拒绝服从严重欠缺形式要件的罚款收缴行为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用公民权利来对抗国家机关的权力到底能有多大的成效?却是很让人怀疑的。
因为即便是在行政诉讼之中,也绝对不是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制度性拟制对抗,来完成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与控制的。公民权利(比如起诉权)在诉讼中的作用事实上仅仅是启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控机制,推动诉讼的进程,对行政权滥用的矫治和控制,实际上还是依赖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实现。
而且,在制度法上给予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与其说是为宪政文明进步而击节,还不如说是将相对人陷于“以卵击石”之极度危险处境之中,而且,增加了法的不安定性。[17] 因为我们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妥当性的思考,还必须结合强制执行制度一并考虑。在我国,因为实行的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己强制为辅的制度,再加上救济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使得相对人如果行使抵抗权,很可能招致行政机关更加严厉的制裁和强制执行。
退一步说,假如我们认可有将无效行政行为与公民抵抗权制度化的必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上述风险,在制度法上也应该尽可能给出明确的、客观的、不易产生争议的判断标准,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规定却是不够清晰的。
无效行政行为的另外一个诉讼意义上的特征是,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我却很不以为然。因为行政行为即便是“无效”,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可能会衍生出其他法律关系,如果作为其他法律行为或关系之基础与本源的行政行为无限期地处于可以被攻击的状态,这显然不利于法的安定性以及社会关系(秩序)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本行为可以被宣告无效,但是,在本行为基础之上繁衍出来的其他行为和关系却在很多情况下值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即便宣告无效,也无法再还原到初始状态。
倘若作为无效与可撤销之间最明显的区别的上述两个要素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予以特别强调的价值,那么,无效与可撤销之间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基础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单从效果上看,无效的效果是使行为做出之后不产生任何效力,但是,可撤销也可以具有溯及力,所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既然如此,做彼此区分又有何益?
退一步说,在肯定赋予相对人抵抗权是无效益的前提下,即使我们认可了无效与可撤销之间的划分,这种区分的意义也只有在诉诸法院、被法院确认之后方能显现出来。否则,不管是无效还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都会像有效的行政行为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下去,并且对当事人发挥着“法律拘束力”。但是,一个行政行为能不能进入到法院,又会受到诉讼资格(locus Standi)和受案范围的限制。假如因为后面的原因被排斥在法院的门槛之外,那么,从客观状态的改变上讲,即使区分了,也意义不大。
3.3 我的看法
因此,上述区分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只能说是表现在最后的裁判方式上,对无效的行政行为采用的是确认判决,对可撤销的是采用撤销判决。但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说清楚这种区分的判断标准,这又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无效和可撤销之间的界分是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其间实际上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很难说非此即彼。
违法程度
可撤销 无效
就算是说清楚了,如前所述,由于因这种二元论衍生出的、最基本的特征要素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效益,那么,二元论的价值仅仅只是体现在裁判方式的不同适用上,显然意义不大。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很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有“物”(行为)可撤就撤,无“物”(行为)可撤就确认。因此,我以为,取消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4. 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后果(II):撤销理论
4.1 是一律撤销?
《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3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可以撤销或者部分撤销。那么,怎么理解该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之中没有做进一步的明确解释。
《行政处罚法》第41条倒是明确规定,违反说明理由和听取辩解之程序要求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18] 然而,该条规定非但没有解决程序效力的问题,反而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是不是其他程序的违反不会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或不成立?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在第41条之中一并规定?如果是,那么又会是什么法律后果呢?
在实践中有的法官认为,只要是违反行政程序,哪怕是微小的瑕疵,也一律撤销,要求行政机关重做。像这样的理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和根据,在荷兰行政法上,就是持这样的观点。这的确能够督促行政机关严格遵守程序,也符合(机械?)法治主义的要求。但是不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荷兰学者之中也不乏异议。[19]
“若干解释”第40、41、42条之规定却是很耐人寻味的。[20] 假设程序违反都将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的话,那么,第40、41、42条规定的几种情形几乎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价值,法院在受案的同时就可以直接宣判撤销。但是,显然法院的实际审判不是这样的。所以,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恐怕不见得是一律撤销。
反过来说,假设不管什么程度和性质的程序违反,都会像推倒多米诺骨牌那样,导致整个行政行为、乃至以后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其他行政行为都一律被撤销,都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再来一遍,尽管其最终形成的决定(结论)很可能依然故我,那么,这种人为地增加整个行政成本,是否符合执法和诉讼的经济性原则?有什么实际效益?的确令人怀疑。尤其是那些对相对人权利保障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程序违反,比如,仅仅是法律文书错误,也实在没有必要撤销。撤销,即便是对于原告来说,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
普通法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开始也是对违背遵守自然正义之义务(breach of a duty to observe natural justice)持强硬(僵硬?)的态度,要么是无效(void),要么是可撤销(voidable)。对于曾出现过“如果遵不遵守听证规则对最终的决定不产生影响的话,法院也不会提供救济”之观点,[21] 也多有批评,视之为“旁门左道”(heresy)。然而,近年来,法院的态度也有所松动。法官也开始不把所有的程序违反,不管巨(大)细(微)与否,一律撤销。甚至违反自然正义原则的程序违法,也不见得一定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这种观点目前占主流。[22] 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意味深长的。
在新西兰的1948年《治安法院规则》(the Magistrates' Courts Rules 1948)R.8,1969年《最高法院(行政庭)规则》(the Supreme Cour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Rules 1969)R.6,以及1955年《上诉法院规则》(the Court of Appeal Rules 1955)R.69,都有类似的规定,即,不遵守(程序)规则,除非有明确规定,一般不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但是,法院也可以以不适当为由,撤销或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按照成本和法院认为适当的方式来修改、处理行政行为。[23]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违反行政程序,不见得一律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
4.2 司法上判断是否撤销的标准
如果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那么,紧接下来就必须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程序违反要撤销?什么样不要?之间的划分和判断标准是什么?
4.2.1 强制性(mandatory, imperative)与指导性(directory)
这是普通法国家的一种传统观点,也就是通过分析涉案程序的性质来抉择司法审查上的态度。违反的要是强制性的,不管违反的程度有多小,一律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被撤销。如果是指导性的,则不尽然。但是,只有实质性遵守指导性规定,才能使行政行为有效。[24]
识别技术
因此,怎么来区分某个程序规定是强制性的,还是指导性的?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从普通法的经验看,法院主要采取了以下技术:[25]
(1)要求的表述(the wording of the requirement)
从程序规定的文字表述上进行识别。法律对指导性的规定多表述为“可以”,是参考性、建议性的,不怎么强调一定要遵守之。反之,对强制性的规定往往使用“应该”、“必须”等强调性的字样。
但是,因为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多数都是表述成“义务性”的言词,然而,却又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强制性的。所以,上述技术的适用价值十分有限。
(2)在立法情境之中的规定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particular provi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legislation)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技术。就是必须考虑整个法律的适用范围和目的,以及该(程序)规定的重要性,其与法律欲实现的一般目标之间的关系。[26]
如果偏离法律规定的程度比较轻微,或者对那些因该程序得益的当事人并不存在实质性偏见,或者将该程序认定成强制性的、会对公众造成严重不便,或者因为法院出于别的方面考虑不愿意干预该行政决定,那么,法院就很可能把不遵守该程序仅仅看作是一种不适当,而不撤销。[27] 另外,假定法院从法律规定之中发掘出程序的目的何在,而且发现在个案之中上述目的已经实现,那么,尽管行政机关的实施方式不是符合法定要求,法院也不会仅仅因此就撤销行政决定。
但是,违反的程序规定要是在整个法律之中特别重要,或者是形成管辖权的步骤之一,或者不遵守之将对当事人产生制裁的结果,那么,就应该认定为强制性的。比如,新西兰曾发生一个案子,交通法(Transport Act 1962)s.47(1)规定,当驾驶员的违章积分(demerit points)达到60-75时,应该给其一个通知,以示提醒。s.47(2)规定,如果积分达到75-100,就要通知其参加学习。原告接到过上一个通知,但是,当他的积分超过75时,却没有得到第二个通知。结果,因为积分达到115,依据s.48被直接吊销驾照。法院认为,s.47、s.48是形成管辖权的系列步骤。s.48是对当事人自由进行干预的制裁性规定,适用之,必须以s.47的通知为前提。所以,s.47的程序是强制性的。[28]
(3)识别为强制性或指导性的结果会不会对公众产生不便
如果宣布行政行为因某程序违法而无效,会给公众带来严重的不便,或者对那些无法控制有关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上述程序规定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也无助于推进立法目的,那么,法院就会认定上述程序规定是指导性的。[29] 反之,就是强制性的。
(4)对个人利益的影响
如果程序规定是对个人权利或利益的重要保障,那么,就很可能是强制性的,必须严格遵守。[30]
(5)技术性解释(interpretation of technicalities)
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据个案情况,把某个规定仅仅解释为指导性的。[31]
当然,在有些判例中还提出,必须考虑(有)没有偏见、违反(是否)轻微等因素。
来自普通法国家的批判
上述强制性与指导性的界分也遭到了普通法国家学者的批判。批判的要点是:[32]
第一,从法院的判案看,相近似的案件因为适用上述不同的技术,或者因为更加侧重考虑某个因素或方面,使得最终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第二,上述“违反强制性程序将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被撤销,违反指导性的不导致撤销”的观点过于绝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违反指导性程序,如果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对当事人的某种偏见,或者是实质性的不遵守,那么,也可能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被撤销(Breach of a directory provision may cause a nullity, either if the non-compliance prejudiced (or may have prejudiced) an interested party, or if the non-compliance was substantial)。相反,违反强制性程序,假如在其中可以解读出某种隐含的例外,允许不必遵守的例外,也可以不撤销(Breach of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may not invalidate the proceedings if it is possible to read into it an implied exception)。也就是说,上述界分不是非此即彼的,之间还应该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兼有两种可能的灰色地带。在这里,上述界分的价值被完全抽空,变得毫无用处。
指导性 灰色地带 强制性
4.2.2 个案内容评估说(an assessment of the substance of each case)
该理论认为,上述强制性或指导性的划分并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基于以下内容会形成一个各种可能性的幅度(a spectrum of possibilities):
(1)规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provision);
(2)不遵守的程度(the degree of non-compliance);
(3)不遵守的效果(the effect of non-compliance)。
所以,在判断某个程序对行政行为效力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小上,应该在个案之中具体地评估上述内容。首先,必须考虑该规定在整个法律情境之中的地位,以及重要性。越重要,法院就越不能容忍对该规定的违反。其次,要考虑该规定的目的。相较其他而言,目的越重要,法院就越不能容忍对该规定的违反。再次,要考虑违反的程度。最后,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判断在违反该规定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在整个立法以及该规定上欲实现的意图是否已经充分地实现了?[33] 如果没有,就是撤销。
4.2.3 因素考量说(factorial approach)
该理论是在批判上述强制性与指导性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院不再识别涉案的程序规定是强制性的,还是指导性的,因为要在这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合乎逻辑的界线来是很困难的。所以,法院就转向直接根据个案中呈现出的各种因素,甚至是彼此竞争的因素,来判断不遵守的法律效果。
在笆利特(P. Bartlett)的研究中,把法院要考虑的因素分成两类:一是会导致无效的因素(factors tending to cause a nullity);二是法院能够从中解读出要求之例外的因素(factors which may lead the court to read an implied exception into the requirement)。[34]
(1)会导致无效的因素
·法律明确规定的;
·未遵守管辖之要求;
·不符合自然正义之要求,比如,破坏了两造对质程序之不适当(Where there has a failure of natural justice, for instance, where the irregularity undermines the adversary procedure);
·确实存在不公正的可能,比如,偏见;
·不遵守程序虽然对当事人来讲,不会造成不公正,但却会带来不便;
·不撤销行政行为,会造成公众不便;
·原谅其不遵守,被告也不会有合理的胜诉机会(Where, in litigation, the applicant cannot show that he has a reasonable chance of success if his non-compliance is excused);
·原谅不遵守,会损害程序规定之目的。
(2)法院能够从中解读出要求之例外的因素
也就是,尽管程序要求是法定的,但是,因为下列因素的存在,可以考虑不因为不遵守之而撤销行政行为:
·寻求救济的原告不会遭到某种偏见;
·原告得知不遵守之后采取了某种新的步骤(Where the applicant has taken some fresh step after knowledge of the non-compliance);
·因不遵守而判决撤销,会造成实际问题(Where practical problems could arise from holding that non-compliance vitiated the proceedings);
·会招致实质性的公众不便;
·事实上不可能遵守;
·存在着某些困难,即便是不会导致遵守之不可能(行),也会使遵守变得十分困难;
·不遵守是因为原告无法控制的其他人(特别是司法人员)不履行职责之故(Where the non-compliance is due to the default of someone over whom the applicant had no control (particularly, judicial officers));
·由于对善意的法律错误导致的不遵守(Where the non-compliance resulted from a bona fide mistake of law);
·撤销行政行为将使不相干的第三人获得权利(Where innocent third parties have acquired rights as a result of the proceedings which are impugned);
·不遵守是高度技术性的(Where the non-compliance is highly technical)。
4.2.4 由第58条解释透视因素考量在我国的适用前景
在我看来,上述普通法国家的几种识别技术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强制性和指导性的划分也是根据个案中呈现出的各种特定因素来判断的,在考量的方法上和“个案内容评估说”、“因素考量说”同出一辙。所谓的灰色地带,实际上也完全可以人为地消除。法院完全可以根据其干预的意愿,用“结果”来决定“识别”。要干预的,就是强制性的,不想干预的,就是指导性的。当然,这决不是主观任性,也是审慎考量的结果。
所以,在我看来,普通法国家的上述方法对我们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各种考量的因素。实际上,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已经不谋而合地认识(意识到?)因素考量的价值,典型地体现在“若干解释”第58条上。
该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在这里,本该撤销的行政行为,毫无疑问应该包括着程序违法的情形。但是,却因为考虑到撤销“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所以,改用确认违法之判决。这与普通法国家所考虑的“撤销行政行为会不会导致公众的极大不便”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在我看来,第58条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肯定了在着重考虑某种(些)因素之下,可以改变司法判决的取向。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同样的技术运用到处理程序违法的问题上来呢?而且,第58条既然是对《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撤销判决的一种补充,那么,第54条(二)3规定的程序违法也应该是包括在其之中的。因此,完全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上述司法解释中已有的因素考量技术,构建我国的违反行政程序的可撤销理论和司法审查标准。
行政程序作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用来获得结果的正当性的,尽管由程序产出的结果并不可能总是正当的。因此,为获得结果的最大边际效益,最大限度地获得正当性的结果,行政程序的设计之中必定包含着某些对相对人权益保障至关重要的制度或程序要求,比如,听取相对人辩解、说明理由。所以,我以为,在考虑的因素当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应当是:
第一,该程序对相对人的权益保障十分有意义;
第二,遵不遵守该程序,会对行政裁量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会左右最终形成的结果;
第三,特定程序本身具有法律严格保护的价值。
要是违反了上述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在司法上的法律后果就很可能是撤销。但是,并不是说,只要违反上述性质的程序就一定会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而应该是,放在具体的案件之中来考察到底要不要、有没有必要撤销。在有些情况下,(我在下面的治愈中还会提到),并不见得一定要撤销。所以,在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上述普通法中不绝对撤销对强制性程序违反的观点。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不太赞成上述《行政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
因此,如果违反的行政程序仅仅是一种内部的手续,对相对人的权益保障没有实质性意义,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规定的“(治安处罚裁决书)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所在单位,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常住地公安派出所…”,那么,不会因为违反这类纯粹内部手续性的程序而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
即便是违反那些对保障相对人权益有意义的程序,如果能够通过其他制度加以补救,也不见得会因为违反而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比如,没有告诉被处罚人救济的途径和期限,我们也只是通过拉长起诉的期限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撤销。[35]
而且,上述第二个因素只是从违反的程序价值本身上讲的,并不是说,如果让行政机关遵守上述程序重新来一遍的时候,必定会形成与原先结果不同的结果。不排除形成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结果的可能。所以,“若干解释”第54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之解释,仍然是有意义的、有适用价值的。
5. 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后果(III):改良的治愈理论
尽管我们承认,有些非实质性的、轻微的程序违法不会、特别是从诉讼的经济性考虑也没有必要导致行政行为的撤销,那么,在行政诉讼上总该有着某种反应?怎样的反应才算是恰当的呢?
5.1 方法(I):忽略不计
在普通法上认为,如果程序瑕疵非常细微,那么,行政机关根本不需救治,即使当事人告到法院,法院也不会理睬。[36] 在新西兰1924年法律解释法(the Acts Interpretation Act 1924)s.5(i)中就明确规定,对于所规定的程式有轻微的偏离,只要不会误导,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就不必计较之。其中的要点有二:
第一,轻微偏离。库普尔法官(Cooper J.)对此解释道,所谓“轻微的”(slight)是指“非实质性”(immaterial)。爱德华法官(Edwards J.)也说,“偏离必须是很轻微的,所以,程式仍然实质上还是法律规定的程式。” [37]
第二,最关键的是,上述偏离不会误导。
这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也存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若干解释”第40条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没有制作和送达法律文书,自然不符合行政行为的程式要求,但是,只要不会误导,只要当事人能够知悉、证明行政行为的存在,就仍然有权起诉。法院也决不会在决定受理的同时就此判决撤销。说明这种程式违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法院容忍的。
但是,上述忽略不计的态度毕竟粗放,与法治主义的要求还有些微隔阂。因为上述程序违反毕竟是行政行为的瑕疵,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在行政审判中,对上述程序瑕疵完全置之不理、视而不见,不作出一定的司法反应,似乎又有悖依法行政之理念与要求,有放任行政机关随意践踏、背弃非实质性、非根本性的程序之嫌。所以,在行政诉讼上就应该、而且必定有着某种表达法院否定性评价、以及相应的救治方式。
5.2 方法(II):制度性补救
实际上,上述“若干解释”第40、41、42条本身就是对程序瑕疵的一种救治方法,也就是用事后的证明、拉长救济期限的方法进行制度性的弥补。
我丝毫不否定上述补救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但是,这只是解决权利保障之周延性的技术问题,毕竟还没有形成法院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正面的、直接的否定性评价。假如对上述程序违法本身,在行政诉讼没有更进一步的司法评价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一种忽略不计。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也可以把上述制度性补救理解为是一种对程序违反的否定性评价,那么,这也仅仅只适用于上述几种情形,对其他非实质性的程序违反,怎么处理?
5.3 方法(III):确认违法
如前所述,非实质性、轻微的程序违法,也是一种违法。即使不撤销,也应该确认违法。所以,应该注意“若干解释”第57条、第58条补充进来的确认判决。[38]
从第57条第2款规定的精神看,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假如不能撤销,那么,也应该退而取其次,确认违法。这样才比较符合法治的精神,才能体现出行政审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之中的非实质性程序违法,又不能完全塞到与之最接近的第57条第2款(二)之中。因为不撤销,不是因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确切地讲,应该是“不具有撤销的价值和必要”。
假如我们牵强地把“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解释成也包括了“不具有撤销的价值和必要”,或者干脆就再修改司法解释,把后一种情况增补进去,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完美地解决上述问题?恐怕还“欠火候”。因为仅仅停留在确认违法的层面上似乎仍然不够,毕竟上述程序违法还存在着更正的可能。
那么,第58条是不是更合适、更能解决问题呢?上述不撤销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考虑到避免不必要地增加行政执法成本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之要求,从比例原则的角度讲,应该是符合第58条适用的前提的。所以,从这一条看,对非实质性、轻微程序违法,采取确认违法的判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58条向我们揭示的另外一个重要价值是,在“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之中暗含着某种程序瑕疵治愈的可能。但是,成问题的是,如果按照第58条操作,那么对程序违法的更正得放到判决之后。对于上述轻微的程序瑕疵,比如,缺少法律文书或者文书上有某些错误,实际上在审理的过程中就已然为双方当事人、特别是被告所知晓,是不是一定要拖到那时?这是不是显得太不(诉讼)经济?那么,有没有更加经济的方法呢?[39]
5.4 方法(IV):治愈
德国和法国法上的治愈理论(curing defects in administrative action),对于弥补我们上述确认违法的方法之不足,是极有参考、借鉴价值的。所谓治愈理论,是针对行政行为的瑕疵,让行政机关自己主动纠正其程序上的瑕疵或错误的一种制度。
5.4.1 能不能治愈?
但是,上述制度却遭到了学者的猛烈批评,认为治愈制度会实质性地阻碍行政行为的客体对行政机关的诉辩能力(substantialy hinder the ability of the subjects of administrative acts to defend their rights vis-à-vis the administration)。另一方面,恐怕也不能够有效地刺激行政机关提高行政决定质量。因为行政机关如果知道程序上的瑕疵会被法院容忍,法院还会让它在诉讼进行中救治而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特别是像缺少义务性听证也允许事后治愈,那么,回旋余地这么大的治愈会不会导致行政机关更加敷衍马虎、应付了事,进而引发更多的诉讼案件呢?不无疑问。[40]
对上述批评比较有力的反驳意见是,假如在诉讼过程中就能够通过给行政机关一个自行纠正瑕疵的机会来实现息讼,那么,干吗一定要拖到判决之后,再让行政机关纠正呢?[41] 在诉讼中的治愈,显然要比判决之后的改正要快捷,要节约诉讼成本。
而且,在我看来,治愈本身是在法院审查过程中发现了程序存在着瑕疵的情况下实施的,尽管是行政机关自己主动地去治疗,但实际上也形成了对行政机关不遵守程序的否定性评价。尽管不判决撤销,但是,假如法院改用确认违法的判决,效果依然不错。而且,有关的诉讼费用仍然必须由行政机关来承担。这种消极后果也会迫使行政机关在以后的执法中更加谨小慎微,而不太可能更加“忘乎所以”、“变本加厉”。
由于治愈一方面是在行政机关自愿接受的前提下实施的,另一方面,还因为诉讼仍然在进行之中,只是悬而未决,假如治愈的效果不能让原告满意,不能达到息讼,那么,诉讼将会重新启动,在这样的压力和情境之下,治愈往往会比较彻底。
如果从我国的法律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治愈制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因为是行政机关自愿主动去救治程序瑕疵,“不伤感情”,减少了双方以后可能发生的摩擦。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原本就有着一种解决纠纷的偏好,即行政机关同意变更或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来换取原告撤诉。如果在行政诉讼上引进治愈制度,能够与引进和解契约一样,[42] 将上述实践纳入更加规范的运转轨迹。
5.4.2 允许治愈的瑕疵有多大?
但是,从西方的经验看,对治愈的层面或程度的把握,却有着深浅之分,其背后的合理性也颇值得推敲和考量。
浅层面(程度)的治愈只是纠正那些对于行政裁量决定的结果不发生实质影响的程序和形式上的瑕疵。比如,在法国行政法上,形式瑕疵(defect of form)原则上不能由行政机关事后(ex post facto)进行治愈。但是,如果从形式瑕疵本身的属性上看,不会影响到行政决定的内容,那么,像这样的瑕疵可以治愈。像在决定的记录上没有签字,就可以通过事后补签的方法来治愈。[43]
像这样的治愈,其合理性显而易见,不太会诱发非议。因为,既然撼动不了原先的行政决定结果,为何不在诉讼过程中就接受治愈呢?治愈本身也达到了原告所预期的诉讼效果。
但是,从德国的经验看,似乎允许更进一步的治愈,也就是允许行政机关实质性地改变行政决定,来达到合法的要求。德国《行政程序法》(Law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Verwaltungserfahrensgesetz, VwVfG)S. 45(1)之规定,允许行政机关治愈下列程序和形式瑕疵:[44]
(1)没有所必需的申请(omission of a necessary application);
(2)没有对行政行为作出必要的理由说明(omission of a necessary statement of reason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ct);
(3)缺少义务性听证( omission of an obligatory hearing);
(4)没有按照要求共同作出委员会决定( omission of a committee's decision cooperation with which is obligatory);
(5)没有按照要求与其他机关合作(non-cooperation, although obligatory, with another agency)。
从上述的规定看,有些程序瑕疵对相对人权利都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比如,义务性听证,但是,仍然允许治愈,那么,最终形成的结果会不会还和原来的一样呢?恐怕不见得。成问题的是,德国法对这种可能并没有做进一步的限制,而是默许了上述两种结果的出现。但是,假设治愈之后,程序是正当了,但实体内容和结果却不能让原告满意,原告就仍然有可能要求继续诉讼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治愈本应具有的尽快息讼、节约诉讼成本等制度效益就不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整个诉讼会因为治愈节外生枝,时间拖得更长。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撤销,让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5.4.3. 容许治愈的时限
在德国,以往,程序瑕疵必须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治愈。其中的基本考虑是严格区分行政手续和司法程序,容许行政机关在包括诉愿在内的行政手续过程之中补正、治愈,但是,到达行政诉讼阶段则不容许,以强化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遵守行政程序的监督作用。[45]
但是,到了1996年的行政程序法修正案(S.45(2))时,却改弦更张,将上述允许治愈的时间延长到了行政审判结束之前。因此,在1997年的德国《行政法院法》(Administrative Court Act,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VwGO)的修正中也相应地增加了在诉讼中如何治愈的规定。包括法官可以给行政机关三个月的时间来治愈被诉行政行为中存在的瑕疵,但前提是不会因此延误审判。[46]
5.5 我的建议
所以,在我看来,单纯的治愈,对行政机关的镇慑效果欠佳,必须结合确认违法判决。两相呼应,才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不是说什么样的程序瑕疵都能够通过上述方法解决,甚至我也不否认在特定情况下,有些轻微的程序瑕疵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忽略不计。所以,能够进入上述诊疗的程序违法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程序瑕疵的治愈本身不会对行政裁量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或者说,程序瑕疵在诉讼中接受治愈,对行政决定无足轻重、无关宏旨。
所以,可以治愈的程序瑕疵,一般是对相对人权利保障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当然,也不排除例外情况下对实质性程序瑕疵的治愈可能。条件是,在诉讼过程中,经过审查,确信行政裁量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形成该决定的过程中却违反了某个实质性程序要求,比如,没有说明理由,因此,允许在诉讼过程中补充对理由的说明。
第二,程序瑕疵是能够,而且有必要治愈的。比如,法律文书内容错误,应该更正;行政决定正确,但是却没有说明理由的,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补充说明理由。
第三,假如诉讼能够治愈解决,那么,法院尽管没有必要将行政裁量决定撤销,但是,应该在判决之中确认行政机关程序违法,并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所以,建议在制度法上补充规定:
“对于可以治愈、被告也愿意纠正的程序瑕疵,法院可以中止诉讼,允许被告自己纠正。治愈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经过治愈之后,如果原告没有异议,法院可以作出确认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判决。“
6. 具体核心程序之个别分析
无偏见
无偏见(without bias)是行政程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普通法中,被认为是自然正义的两个最基本元素之一,(另一个是听取辩解或听证)。在程序上表现为自己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 iudex in sua causa)。
偏见会导致行政裁量决定无效(void)或者可撤销(voidable)。后一种结果得到了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的实证支持。[47]
在我国,无偏见的要求主要是通过回避制度体现出来。应当回避,但是没有回避,当然会对行政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一定是撤销。比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4条就规定,“…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进行的与案件有关的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回避决定的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
听取辩解(听证)
一般而言,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益处分之前,应该给他/她一个听证或者辩解的机会(audi alteram partem),让其参加到行政程序之中来。这是因为:
第一, 听证是和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和正当程序(due process)密切相关的。[48] 正当程序由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一个是听取另一方意见(hearing, audi alteram partem),另外一个是无偏见(unbiase, nemo judex in causa sua)。韦德(H. W. R. Wade)和福赛(C. Forsyth)甚至认为,听取双方意见(听证)最能够体现自然正义原则,因为它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正当程序问题,甚至可以把无偏见也包容进来,因为公正的听证本身就必须是无偏见的听证。现在之所以两者是分开的,是对传统二元论遵从的结果。[49]
第二, 听证有利于在事中就加强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能够有效地弥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射程不足。因为听证一般是在行政决定作出之前进行的,而且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或者知晓法律的亲朋好友参与,[50] 这对于及时制止错案的发生,提高申辩的质量,都大有裨益。
第三, 听证有助于积极吸纳相对人参与行政,形成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能够充分地体现良好行政的要求。
在我国,听证程序是由《行政处罚法》首次确立起来的,随后的《行政许可法》也肯定了这项制度。但是,就目前的推广程度看,还不如西方普及。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初创,较为谨慎,需要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可能是在制度设计上没有注意引进西方的非正式听证,程序过于繁琐,给行政机关过多地增加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负担,引起实践上、观念上的抵触。后者是我们今后要警惕和克服的。
但是,听证的适用毕竟还是会对行政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比如,治安管理上对于流动人口,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控制其行动自由的措施问题,就没有办法实施听证。否则,违法嫌疑人会乘机逃跑,受害人也会因此不满而不断上访、控告。因此,也没有必要事事都听证。
从近年来普通法的法院判例和理论发展来看,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下,[51] 可以不执行听证程序,只要没有违反“无偏见”之程序要求,仍然符合自然正义之要求。[52] 在英国,哪些是无须听证的决定(deciding without hearing)?一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授权法的规定;二是行政职能的种类(the type of function being performed);三是决定者的性质(the nature of decision-maker)。[53]
那么,违反听证的要求,会对行政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普通法的传统理论认为,违反自然正义规则的行为,就像越权行为一样,将导致行政决定无效。因为公正行事的义务,就像合理行事的义务一样,被当作默示的法律要求来执行。因此,不遵守之,就意味着行政行为是在法定权限之外做出的,是不合法的,进而是越权、无效的。[54] 因此,违反听证的行政行为,会实质性地损害正当程序理念和要求,自然也就是越权、无效的。[55]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41条规定“…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暂且不说上述两款在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上的表述不一致,至少可以说,在我国,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后果应该是行政行为无效、被撤销。其中的理由,不单纯是因为听证程序本身所蕴涵的法律价值需要保护,更主要的是,没有听证,意味着没有很好地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也就不可能全面地、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所以,从表面上看,行政行为被撤销是因为违反法定程序(没有听证),实质上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
如果因为没有给予公正的听证机会而导致行政决定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法院应该责令行政机关重新听证。听证还得由原机关组织。原机关原则上应该组织不同的成员来主持听证。如果不存在人员选择的可能性,那么,原机关应该以尽可能公正的方式组织听证。雷德法官(Lord Reid)指出,如果行政机关迅速实施了听证,而且重新对所有的问题进行了考虑,在给予当事人适当的机会陈述其意见之后,所做出的行政决定将是有效的。
但是,是不是只要违反了听证程序就一律导致行政行为被撤销呢?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新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比如,近年来,一些普通法国家的法院就认为,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听证,法院又觉得在该案中听不听证对于最终的结果来说都没有多大的影响,那么,法院也不会以程序违法撤销行政决定。[56] 这种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更加注重了救济的实质效果以及诉讼的经济原则。
说明理由
说明理由(a duty to give reasons)可以看作是听取辩解(听证)原则(audi alteram partem principle)的一个方面,是包含在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基于公正程序和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扼要地讲,这是因为,[57]
第一,说明理由能够增进行政裁量决定过程的理性与正当性,迫使行政机关必须小心斟酌相关事由,进而有效地遏制行政裁量的任意和专横。而且,能够增加行政的透明度,提升公众对行政决定的信任和接受。所以,它又被视为良好行政原则(principle of good administration)之一。
第二,理由说明的本身也架构出行政裁量的推理和思考过程,这就为以后类似的行政行为提供了一种指南,能够保持行政行为的前后一致性。
第三,向相对人阐述理由,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讼争,而且,也构成了相对人行使辩解权和诉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相对人不知道行政决定的理由,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辩驳,也无法断定凭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去申诉。所以,丹宁(Lord Denning)就说过,如果听证权要真成那么一回事,就必须包含着这样一种权利,当事人要有权知道针对他的案件。他必须知道有哪些证据?影响他的决定是怎么说的?他要有公正的机会去纠正、去辩驳。[58]
第四,也有利于法院事后有效地审查和评价行政决定的合法性。
但是在我国,因为缺少行政程序法的缘故,上述程序要求迄今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只存在于某些法律之中,比如,《行政处罚法》第31条之规定。[59] 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会对相对人产生不利益的行政行为,本不应该、但是仍然处于上述程序要求的射程之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行政法的一大缺憾!
那么,如果行政机关违反了说明理由之程序性规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这可以视违反的程度分别讨论。
(1)完全没有履行法定的说明理由义务
在行政审判上,假定行政机关仅仅只是没有履行法定的说明理由义务,并没有其他并存的违法问题(collateral unlawfulness),那么,是不是就凭上述程序违法就可以撤销行政行为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上述程序违反,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作出裁量决定时没有理由,可能是有理由,但是,没有说。当然,也可能是没有理由或者实际的理由说不出口。如果是后一种,当然需要撤销。但是,假如行政机关的确有理由,而且理由也是正当、合法的,只是没有说出来,那么,可不可以不撤销,而是在诉讼中治愈解决?至少从诉讼经济的角度看,不排除这种可能。
所以,从普通法的经验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判例倾向于并不必然因此导致行政决定无效。法院有时可以通过强制要求被告说明理由的方式来提供救济。当然,如果理由是不充分的、不合法的,那么就可以撤销。[60]
(2)形式上履行了,但给出的(部分)理由是不充分的,或者是错误的
我们只能大致地说,理由应该与行政行为有关,应该有说服力(intelligible),应该能够支持行政行为。说明的理由必须足以大略地告诉当事人“为什么输或者赢”(Reasons must be sufficiently detailed to ‘tell the parties in broad terms why they lost, as the case may be, won')。[61] 很可能是因为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率的缘故,说明的理由一般是简要的、要言不烦的,是对认定的事实、法律的适用及其之间的逻辑关联的高度概括。
所以,法院一般不直接审查、也没有必要审查理由的充分与否。如前所述,说明理由往往是揭示行政行为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阐述其中的关联,所以,顺理成章地能够转换为对事实错误(error of fact)、法律错误(error of law)以及不相关考虑(irrelevant consideration)、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s)等问题的审查。
当然,假定给出的理由是独立的(independent)、可以各自分开的(severable),其中有些是错误的,但主要的理由却是合法的,那么,一般也不会因此而撤销行政行为。[62]
7. 结论
上述对行政程序的效力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是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63] 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应该在考量个案呈现出的有关因素之后作出是否撤销的判断。如果不撤销,也不意味着程序违法是可以宽恕的,法院应该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如果程序瑕疵是可以治愈的,那么,在诉讼过程中,法院还应该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相应的治疗。
由于行政实践和行政程序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所以,要想更进一步对实践中层出不穷、形形种种的行政程序违法形态逐一进行分析,预先逐一给出相应的完美解决方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在个案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处理,必须有待于法官的判断、裁量和权衡,必须依赖于法官对其司法能动性以及宪政角色的感悟和发挥。
但这并不是说,上述研究是没有价值的,恰好相反,假如我们有着对行政程序效力的基本看法和原则,就能够有效地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像翘翘板那样,压下了这一头的行政裁量专横,却翘起了另一头的法官裁量专横。
--------------------------------------------------------------------------------
[1] 戴维斯认为,在裁量权改造之中,七个手段最为有用,即公开计划(open plans)、公开政策(open policy statements)、公开规则(open rules)、公开事实(open findings)、公开理由(open reasons)、公开先例(open precedents)以及公正的非正式程序(fair informal procedure)。其中,后四项都属于程序范畴。Cf. 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 Greenwood Press, 1980, p.98
[2] Cf de Smith, Woolf & Jowell,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5, pp.462-463. 在英国,也没有普通法上的一般义务,要求说明理由。但是,从法院的判例看,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技术可以推导出这种程序上的义务。Cf. P. P. Craig, op. Cit., pp.432-433.
[3] Cf. Hilary Delany,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Dublin. Round Hall Sweet & Maxwell, 2001, p.226, 227.
[4] 参见,刘宗德:“行政裁量之司法审查”,收录于其著:《行政法基本原理》,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1~142页。
[5] Cf.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p.526.
[6] Cf. Christopher Forsyth, “‘The Metaphysic of Nullity' Invalidity, Conceptual Reasoning and the Rule of Law”, Collected in Christopher Forsyth & Ivan Hare (eds.), The Golden Metwand and the Crooked Cord: Essays on Public Law in Honour of Sir William Wade Q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42, especially note 12.
[7]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
[8] 该条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9] 参见,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 —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之探索”,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10] 《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11] 当然,这种付诸阙如也可以理解成,司法解释是采取了“绝对公定力”之态度(?)。
[12] Cf. Christopher Forsyth, op. Cit., p.142, 144.
[13] 这种观点和大陆法的“完全公定力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完全公定力说”的真正价值在于,基于法的安定性之考虑,概无例外地推定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都具有公定力,针对行政行为效力的纷争,统统必须循着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
[14] Cf. H. W. R. Wade,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on: Void or Voidable? (Part I)”(1967) 88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510-511.
[15] Cf. H. W. R. Wade,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on: Void or Voidable? (Part I)”(1967) 88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525-526.
[16] Cf. Christopher Forsyth, op. Cit., pp.144-145.
[17]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承认这样的危险之事实存在。参见,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于《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参见,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 —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之探索”,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18] 《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19] 荷兰Utrecht University的Dr Tom Zwart教授在与我的交谈之中,表示不赞成上述做法。另外,他还向我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有关荷兰行政法的资料,在此致谢。
[20] “若干解释”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第4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1] Cf. Mark Aronson & Bruce Dyer,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IBC Information Service, 1996, pp.486-487. Cf. Peter Cane,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91.
[22] Cf. Michael Supperstone QC & James Goudie QC, Judicial Review, Butterworths, 1997, p.7.2. Cf. Philip John Bartlett,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Procedural and Formal Rules”(1975-1977)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64. 凯斯法官(Lord Keith)甚至在London and Clydesdal Estates Ltd v. Aberdeen District Council中认为,即使违反强制性(程序)规定,也不见得一定撤销。
[23] Cf. K. J. Keith, A Code of Procedure for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Legal Research Foundation School of Law Auckland, New Zealand, 1974, p.40.
[24] Cf. G. D. S. Taylor, Judicial Review: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Wellington. Butterworths, 1991, p.308.
[25] Cf. Philip John Bartlett,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Procedural and Formal Rules”(1975-1977)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50-55.
[26] Cf. Michael Supperstone QC & James Goudie QC, op. Cit., p.7.2.
[27] Cf. K. J. Keith, p.39.
[28] Cf. Philip John Bartlett,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Procedural and Formal Rules”(1975-1977)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51-52.
[29] Ibid., 52-53.
[30] Ibid., 53.
[31] Ibid., 54.
[32] Cf. Philip John Bartlett,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Procedural and Formal Rules”(1975-1977)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55-59.
[33] Cf. G. D. S. Taylor, op. Cit., pp.308-309.
[34] Cf. Philip John Bartlett,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Procedural and Formal Rules”(1975-1977)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66-67.
[3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36] Cf. Michael Supperstone QC & James Goudie QC, op Cit., p.7.3.
[37] Cf. Philip John Bartlett, “The Consequences of Non-Compliance With Procedural and Formal Rules”(1975-1977)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67-68.
[38] “若干解释”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其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39] 当然,我也不否认,第58条可能还有另外的考虑,对有些实体问题,特别是涉及利益调整的问题,需要放到确认判决之后,需要时间从容处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第58条仍然有其合理性。
[40] Cf. Bernd Goller & Alexander Schmid, “Reform of the German Administrative Courts Act”(1998) 4 European Public Law 32, 35, 36.
[41] Cf. Bernd Goller & Alexander Schmid, “Reform of the German Administrative Courts Act”(1998) 4 European Public Law 35.
[42] 关于对和解契约的介绍,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页,特别是注释。
[43] Cf.Zaim M. Nedjati & J. E. Trice,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Systems of Administrative Law,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41.
[44] Cf. Bernd Goller & Alexander Schmid, “Reform of German Administrative Courts Act”(1998) 4 European Public Law 34, note 18.
[45] 参见,吴庚:《行政法的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57页。
[46] Cf. Bernd Goller & Alexander Schmid, “Reform of the German Administrative Courts Act”(1998) 4 European Public Law 34.
[47] Cf. G. L. Peiris, “Natural Justice and Degrees of Invalidity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1983) Public Law 635.
[48] 在英国的学术发展史和法院判例之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价值尺度,即公正行事(acting fairly),也可以视为听证的理论基础。但正像韦德(H. W. R. Wade)和福赛(C. Forsyth)指出的,公正行事和自然正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可以相互替代,都是用来描述一个灵活的原则,其内涵可以随着权力的性质和案件的情形而变化。 Cf.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4, p.515.
[49] Cf.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op. Cit., p.494.
[50] 当然,在听证中,允不允许律师代理?允不允许知晓法律的亲朋好友出席帮助申辩?这不是当事人的绝对权利,而是由听证机关来裁量决定的。在裁量中一般要考虑以下因素:指控或制裁的严厉程度(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 or penalty)、是否可能出现法律上的争论点(whether any points of law are likely to arise)、当事人自己应付听证的能力、程序困难(procedural difficulties)、裁决的时间要求(the need for speed in reaching a decision)、关乎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公正的需要(the need for fairness a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fficers concerned)等。Cf. P. P. Craig, op. Cit., p.429.
[51] 在英国,基于公共健康或安全而采取的紧急行动,比如,将正在销售之中的变质猪肉收缴、销毁,或者命令将传染病人转院,一般是不要经过听证的。另外,在有些非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也不需要听证。比如,贸易部门派人对某公司的某些可疑问题进行调查,尽管这可能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损害,但是,事先的听证将不利于调查目的的实现。
[52] Cf. Peter Cane, 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61.
[53] Cf. P.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9, p.438.
[54] Cf.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op. Cit., p.516.
[55] Cf. P.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Sweet & Maxwell, 1999, pp.671-672.Cf. H. W. R. Wade,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on: Void or Voidable?”(Part II) (1968) 84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101-103.
[56] Cf.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op. Cit., p.549.
[57] Cf. de Smith, Woolf & Jowell, op. Cit., pp.459-460. Cf. Hilary Delany, op. Cit., pp.216-217. 当然,也有反对说明理由的,其论据是,说明理由的程序要求会抑制裁量权的行使,会过分加重行政机关的负担。但是,从欧盟法和澳大利亚的实践看,尽管都普遍要求说明理由,却没有出现上述问题。所以,上述反对理由缺少实证的支持。Cf. P. P. Craig, op. Cit., p.430.
[58] Cited from H. W. R. Wade & C. F. Forsyth, op. Cit., p.531.
[59] 该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60] Cf. Michael Supperstone QC & James Goudie QC, op. Cit., p.7.4, pp.7.5-7.6. Cf. de Smith, Woolf & Jowell, op. Cit., p.470.
[61] Cf. Hilary Delany, op. Cit., p.230.
[62] Cf. de Smith, Woolf & Jowell, op. Cit., p.469.
[63] 关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我还会另外撰文讨论的。
中国公法网